本文拟对《诗经》问世以后,历代对其所作的研究,择其大要,做一梳理,挂一漏万,难称周全,故谓之“极简史”。所谓的《诗经》学,或《诗经》研究,包括对《诗经》的编定、传播、注解、诠释等多方面,所涉及的领域可涵盖经学、文学、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农学、博物学、艺术学等多学科。
先秦时期,由于《诗经》本身尚在创作、搜集、编定的成形时期,故传统的《诗经》学——《诗经》研究,还未正式登场,还没开始真正进入研究阶段。这个时期,自然没有产生有关《诗经》研究的专门论著,有的只是对《诗经》产生过程的参与、点评和引申发挥,如孔子整理编定“诗三百”,发出有关诗教的观点,孟子提出方法论,荀子提出文化观等。其时,涉及《诗经》的话题虽尚不属专门的研究,但其相关的专题,却是与后代的研究多少有关,有的还很重要——《诗经》的基本概念——诗、诗三百、《诗经》;《诗经》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地域;《诗经》的作者;“诗三百”的采集(采诗、献诗)、整理和编定;孔子“删诗说”;“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先秦时代诗、乐、舞与《诗经》的诗乐合一;关于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概念及其争议;《诗经》的应用——先秦时代引诗、赋诗及其他;孔子诗说——“兴、观、群、怨”,“思无邪”,“温柔敦厚”,“不学诗,无以言”,“经世致用”等;孟子诗说——“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荀子诗说——“明道、征圣、宗经”等。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汉学)
两汉时代由于是《诗经》研究的开创和奠定时期,故而在《诗经》研究史上,汉代的《诗经》研究,便称为“诗经汉学”,简称“汉学”。
两汉时代,应该说是中国历代《诗经》研究的真正开创与奠基时期。为何这样说? 虽然,《诗三百》的产生时代在西周春秋时期,它的整理编定工作,孔子也参与了,《诗经》这个名称的定名,称【诗】为【经】,是在战国时启端——《庄子天运》有云:“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子 劝学》有云:“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真正将《诗三百》置于至高地位,是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被武帝采纳之时,此后,儒家的几部代表著作《诗》《书》《易》《礼》《乐》《春秋》等,从此被奉为了儒家的经典,于是,《诗三百》就成了《诗经》——自此以后,开始了历代对《诗经》的注“经”历史,也即,《诗经》的研究历史正式开启了。
两汉时代的《诗经》研究,总体上包括两大派,此即后世所谓汉代传诗的“四家诗”——“三家诗”和“毛诗”。“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还包括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故也称为“今文三家”(今文经学);“毛诗”是用战国时代的隶书书写(还包括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故也称为“古文毛诗”(古文经学)。
“三家诗”,指鲁诗、齐诗、韩诗三家——鲁诗,鲁国人申公所传;齐诗,齐国人辕固所传;韩诗,韩国人韩婴所传。
“毛诗”较“三家诗”晚出,相传为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所传。《毛诗》的代表著作是《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该著是“诗经汉学“的代表作,所作训诂解释,释词明确,渊源清晰。
由于“三家诗”和“毛诗”分别代表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因而在两汉时代,这两派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直接影响贯穿了整个时代。具体在对《诗经》的解说上,“三家诗”与“毛诗”的分歧,既表现在政治立场上,也表现在书写的文字、说诗的方法、解说的繁简、章节的编次、名物的训诂、字词的辨析,乃至对具体诗篇的不同理解等多方面。由于“三家诗”完全站在汉代官方政治立场上,它在两汉时代自然属于官学,而随着汉代统治的结束,它的生命也就告终了。“毛诗”则与汉代政治距离较远,属于民间传授之学,且又不断提高了训诂和义疏的质量,因而它比“三家诗”的生命力显得旺盛,此后便一直延续下去了。
这里,应提到一位在汉代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儒——郑玄,他为《毛诗》所作的“传笺”——《毛诗传笺》一书,在整个中国《诗经》研究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打破了师法之拘,结束了两汉的今、古经学之争,书中的解诗,兼融了“三家诗”和“毛诗”之说,以宗毛为主,吸取“三家诗“,并在《毛传》基础上作补充修订,提出了不少属于自家的说法,显示了其自身的特色。
两汉时代在《诗经》研究方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毛诗序》。《毛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大序(又称《关雎序》)系针对全部《诗经》而写的总论全部《诗经》的序言(兼及《关雎》一诗),小序则是为《关雎》以外其他三百零四篇诗所作的简短诗意解说。《毛诗序》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说法甚多,至今争议不决,分别有:孔子;子夏;卫宏;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毛公、卫宏合作;等等。对《毛诗序》为何而作,其文字的来源和所作序的内容是否切合原诗内涵,历来争议不决,难以定论。但是,不管如何,笔者认为,《毛诗序》本身是一篇极有诗学价值的文字,不但其小序部分值得参考(自然不可照单全取,必须结合作品本身与历史时代,有所取舍),且其大序,尤值得重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早期阶段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的诗歌专论,它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总结了先秦时代儒家的诗歌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属于儒家诗教的开创性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主张,属于一篇具有开山意义的纲领性理论文字。
这里,不妨全文录下《诗大序》文字(《关雎》部分略)——“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毫无疑问,从上引文字可以见出,《诗大序》在内容上,是一篇儒家纲领性的礼教宣传文字,其封建政治色彩不容否认,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篇文字,确是高度阐发了先秦时代儒家的诗歌理论,代表了这一时代文学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最高水准。为何这样说? 我们看它的具体文字阐述。概括地看,这篇文字的理论要点,包括以下四部分:一,精辟地阐述了诗、乐、舞三者的起源,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特征,其中尤其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开创性地提出了“诗言志”这一纲领性的主旨口号,标明了诗歌创作的目的与功用,由此,这个口号成了后世历代中国传统诗歌创作和理论的旗帜,其本身切中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本质特征——言志抒情。二,概括地点明了诗歌与时代及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密切关系,所谓“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变风、变雅”等,即是其具体体现。三,突出了儒家诗教的作用,强调了诗歌的政教功用,且明确指出,诗歌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作用,它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话本身虽然包涵了浓厚的儒家礼教色彩,但客观地说,它确实较为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实际功用。四,对“诗六义”的概括——风、雅、颂;赋、比、兴,既判明了诗的分类,也阐述了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这对当时和后代的诗歌创作及理论,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两汉时代由于是《诗经》研究的开创和奠定时期,故而在《诗经》研究史上,汉代的《诗经》研究,便称为“诗经汉学”,简称“汉学”。
魏晋至唐《诗经》研究
这个历史阶段也还是出现了《诗经》研究的不同学派及其代表学者,它们形成了争论或对峙状态。魏晋时代是郑学、王学之争,南北朝时代是南学、北学之争。
相对于两汉时代,魏晋至唐这个历史阶段,《诗经》研究处于低潮期,基本上没有形成专门的学术流派,问世的著作也相对较少,这与这个历史时代不同于两汉大一统社会“独尊儒术”有一定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乱世”,南北常年处于战乱和朝代更迭状态,即便隋唐统一后,儒家思想也还是不如两汉时代那样处于独尊地位。
不过,这个历史阶段也还是出现了《诗经》研究的不同学派及其代表学者,它们形成了争论或对峙状态。比较有代表性的,魏晋时代是郑学、王学之争,南北朝时代是南学、北学之争。其时,汉代郑玄的《毛诗传笺》标举毛诗,融合三家诗,成为当时的权威注本,形成了“郑学”,这引得魏人王肃的攻击,认为这是打着“毛诗”牌子,却引用“三家诗”,破坏了“毛诗”古文经学的家法,由此,王肃要申毛难郑。不过,王、郑两家之争,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后来郑玄还是凭自己的地位,以及《毛诗传笺》本身的影响,使其书得以流传后世。南北朝时代,南学,承魏晋兼采王学;北学,承汉代推崇郑玄。随着隋朝统一南北后,所谓的南学北学,也就结束了对峙——北学归入南学而趋统一。这个统一,实际是由朝廷授命唐代学者孔颖达,负责主持撰定“五经正义“(《毛诗正义》系其一)而得以完成。《毛诗正义》是魏晋至唐时期《诗经》研究的一部重要代表著作,它广泛吸收了唐初以前历代的《诗经》研究成果,“融其群言,包罗古义”,为《毛诗故训传》和郑玄《毛诗传笺》作疏解,集唐前汉学之大成,全部保留了《毛传》《郑笺》的注文,并在这些注文基础上作疏解(后世简称其为《孔疏》)。《孔疏》坚持“疏不破注”原则,综合吸取汉魏以来诸家训诂之见解,融汇了汉魏六朝《诗经》研究的成果,全书贯穿了说解、文字、音训的三统一,使之达到了当时《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是继《毛诗故训传》(《毛传》)和《毛诗传笺》(《郑笺》)之后,历代《诗经》研究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经》学著作。
必须注意的是,魏晋至唐这一历史阶段中,《诗经》研究不仅限于学者在经学范畴内对《诗经》作注释和说解,而且出现了文学家对《诗经》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艺术手法作阐述和评价,这当中包括刘勰、钟嵘等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的多篇论述中,涉及了对《诗经》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的评论和阐述,比较代表性的篇章有《宗经》《辨骚》《时序》《情采》《比兴》《夸饰》《物色》等,其中分别谈到了《诗经》的教化作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关于赋比兴、《诗经》的修辞手法、《诗经》对后世的影响等。钟嵘的《诗品》在品评诗人及其作品高下时,自然涉及到了诗歌源头之一的《诗经》,而他的《诗品·序》中,更是直接阐述了他对《诗经》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认识和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宋元时期《诗经》研究(宋学)
这个时期《诗经》研究的新风气——倡导怀疑,喜好辨伪,重视义理,不信诗序,探求新义。改造传统儒学、时兴自由研究、看重实证思辨,已形成学风。
宋元时期的《诗经》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在宋代。元代整个朝代在异族人统治下,汉族的儒家经典自然受到压制,大约除了朱熹的《诗集传》在当时有些影响,其他几乎无啥可说了,因而出现的涉及《诗经》的注解,都是朱熹《诗集传》的延申发挥。这里,拟集中阐述宋代的《诗经》研究。这个时期可称《诗经》史上的高峰期,相对于汉代的“诗经汉学”,宋代可称“诗经宋学”,特别是南宋问世的朱熹《诗集传》,是宋学的代表,在整个中国《诗经》学史上,堪称里程碑式标志。
宋代的社会风气,或者说宋代的经学论坛,普遍是疑经、改经,对先人的诸多经典,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持怀疑态度,考辨成风。这就牵涉到了这个时期《诗经》研究的新风气——倡导怀疑,喜好辨伪,重视义理,不信诗序,探求新义。也就是说,这个历史阶段,改造传统儒学、时兴自由研究、看重实证思辨,已形成学风。其时涌现的一批《诗经》研究著作,代表性的有:欧阳修《毛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诗序辨说》、程大昌《诗论》、王柏《诗疑》等。宋代这些注《诗》学者,对《诗序》发起猛烈攻击,力主废《序》,由此,他们与当时的汉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的大家,在《诗经》研究上推出了《毛诗本义》,该书重点在本义说解,对前代的毛、郑所说,多有指正,认为他们在不少方面训释不当,这在当时属于开了风气之先,毕竟无论毛还是郑,都是前代《诗经》研究大家,他们传世的《诗经》注本——《毛传》《郑笺》,历来被奉为权威,而欧阳修居然敢于对他们大胆评议,且自创新说,为此,欧阳修的研究自然对宋代的《诗经》学起了较大影响,之后的苏辙、郑樵,乃至朱熹,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郑樵是“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诗序》,提倡声歌之说,重视名物考证,他的《诗辨妄》指出了《诗序》诸多谬误,其辨妄对象,直击毛、郑——指责他们的说解为“村野妄人所作”。可惜,郑樵这本《诗辨妄》已失传,今可见者,乃顾颉刚所辑之残本。
朱熹毫无疑问是“诗经宋学”的权威代表人物,他的《诗集传》是“诗经宋学”集大成的代表著作。可以说,《诗经》研究到了宋代,是朱熹真正建立起了可与“汉学”相对峙、相抗衡的“宋学”——“诗经宋学”至此开始确立起了它的学术体系,它以朱熹理学思想为基础,汇集了宋人众多的训诂和考证成果,又顾及了《诗经》的文学特点,使得这部注释简明的《诗集传》,成了当时和后世数百年的权威注本。综合朱熹的《诗经》研究和他的代表作《诗集传》,我们可以看到,它显然具有以下四方面特色:其一,反对《诗序》,指出《诗序》的种种谬误,他因此专写了《诗序辨说》,用查核史料、对照诗篇内容的做法,驳斥《诗序》,尤其针对三百零五篇的《小序》。其二,在反对《诗序》的基础上,他广采众说,充分吸取了前代各家之说,并融入自家的看法,建立了与汉学不一的宋学。其三,对“诗六义”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诠释,比毛、郑所释相对更接近了诗本义——“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不仅如此,朱熹还在他的《诗集传》的具体诗篇注释中,标明每首各运用了赋比兴的何种手法——或单独,或综合(赋而比;比而兴;兴而比;等等),这对于读者欣赏和理解诗篇的艺术特色,很有启发帮助。其四,总体上看,朱熹《诗集传》的注释、诠解,力求接近诗本义,努力做到简明得体,且不限于从经学角度作解说,还尽可能顾及了用文学眼光剖析诗歌的内在蕴含与艺术特色,这无疑增进了读者对《诗经》文学价值的认识。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朱熹的《诗集传》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体系,“诗经宋学”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确不可低估,但朱熹毕竟是个正统的封建卫道士,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封建统治研究《诗经》、注释《诗经》的,他的研究初衷,绝非为文学而文学、为诗歌而诗歌,而是力求不能有害于封建礼教的温柔敦厚,不能违背封建的纲常伦理,目的在于宣扬封建教化、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明清时期《诗经》研究(清学——新汉学)
元明两代,在《诗经》研究方面,如出一辙,都呈低谷状,很少有具影响的研究著作。而清代则完全不同了,它是《诗经》学史上第三座崛起的高峰。
明清两代的《诗经》研究,有个非常鲜明的差异,即明代与清代相比,明代显然呈低谷状,而清代绝对是高潮。明代的《诗经》研究几乎沿袭元代,除朱熹《诗集传》的余绪影响外,学术界较少出现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诗经》研究学者和论著。可以提及且有价值的,大约是如下二部: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独居一格,诗史结合,不遵从传统解说,考证有精核之处,体现了突破传统、力求创新的努力;陈第《毛诗古音考》,推倒宋人的“叶音说”,开创了《诗经》古音韵学的研究。明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研究学者和著作罕少的状况,和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很有关系——因科举考试要求考《四书》,于是,重《四书》轻《五经》在当时便成为社会风气,致使《诗经》学在明代自然趋于了衰落。可以说,元明两代,在《诗经》研究方面,如出一辙,都呈低谷状,很少有具影响的研究著作(少数例外)。而清代则完全不同了,它是《诗经》学史上第三座崛起的高峰,是继汉学、宋学之后,崛起的第三座高峰——清学,即“诗经清学”(或谓“新汉学”)。
清代的《诗经》研究继承了汉代学派的朴实之风,讲究考据,“无征不信”,一反宋学的空谈义理、不务实际和明代的科举取士、不重经学,这实际是为了摆脱宋明理学的桎梏,旨在复兴汉学,故谓清代的《诗经》研究为——“新汉学“。整个清代,由于统治者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政治视线,便大力提倡经学,于是乎,大批知识精英将毕生精力付诸经学研究,使得经学由此开始兴旺发达,名家辈出,著作如林,清代的《诗经》学也就自然而然成就空前、蔚为壮观了。
清代《诗经》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辑佚、校勘和小学三个方面,这是它特别有别于汉学和宋学的显著特点——汉学注重注释、疏解、正义,宋学在汉学之后注重义理,而清代的清学,则偏重辑佚、校勘、小学,体现了治学功底和精细功夫。具体来说,辑佚方面,主要是对三家诗的辑佚,代表学者为陈寿祺、陈乔枞、王先谦;校勘方面,阮元的《毛诗校勘记》(《十三经校勘记》之一)堪称代表作;小学方面,研究《诗经》音韵、考据学的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研究《诗经》文字、名物考证的陈启源、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等,都是清代的杰出学者,他们代表了清代《诗经》研究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大体来看,清代的《诗经》研究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宋学衰落,汉学复兴,顾炎武开创考据学,创立音韵学,黄宗羲将经学与史学结合,开始学术史研究,王夫之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第二阶段清中期,进入清代经学研究繁荣期,考据学盛行,产生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学派”,以古文经学(所谓新汉学)为主,对《诗经》展开全方位的考证研究,其范畴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辨伪、辑佚、校勘等,其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整个《诗经》研究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可与之相比。这个时期,产生的《诗经》研究代表作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诗传疏》等,它们代表了清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此外,陈寿祺、陈乔枞父子辑录三家诗,魏源著《诗古微》,也值得一说。第三阶段清末,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所替,今文经学开始繁荣,出现了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这是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此外,这个时期还涌现了所谓不今不古的独立思考派,即在汉学与宋学以外,产生的第三派,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有: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等,他们的研究,开了清末《诗经》研究的新风。
(作者注:本文撰写,参考了多种古代和今人的相关论著,限于篇幅,不专门列出书目,特此说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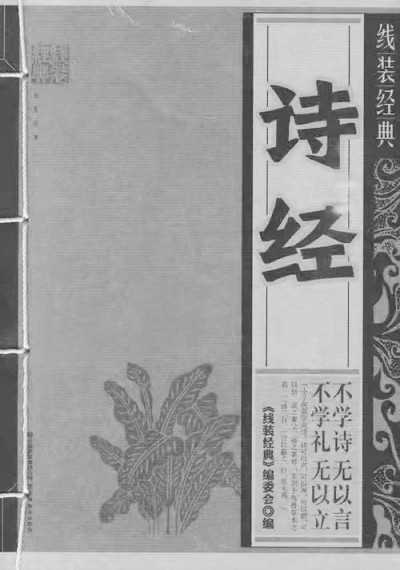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