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荷马史诗》英译者、英国18世纪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更多以睿智而精妙的格言著称于世,如“浅学误人”“智者裹足不前,愚者铤而走险”以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宽恕他人,神明自得”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蒲柏提倡“宽恕”之道,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未能践行此道。像他的友人斯威夫特一样,蒲柏的讽刺对象,上至时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英王乔治二世,下至文坛诸友——从莎剧名家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到小品文圣手艾迪生(Joseph Addison),乃至格拉布街潦倒文人——无所不包。借用伍尔夫在《奥兰多》一书中的评价:“蒲柏先生睚眦必报,世上无人可比”,由此也引发对手疯狂报复。据说后来蒲柏在自家庄园遛狗时都要随身携带手枪。
对于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达官显贵(及其帮闲文人),蒲柏下笔之际毫不留情,同样,对于附庸风雅、无事生非的宫廷贵妇,他亦极尽嘲讽之能事——其言辞之刻毒,用心之险恶,甚至远超他对同侪的攻讦谩骂。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家通过新批评式的“细读”,从蒲柏诗作字里行间发现若干“罪证”,证明在18世纪英国文坛,厌女症是一种集体症候,而蒲柏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上述文论家一致认为,在蒲柏诗文中,最能集中体现厌女这一时代症候的作品当推《夺发记》(The RapeoftheLock,1712)。
戏仿英雄史诗《夺发记》取材于发生在1711年的真实事件:贵族青年罗伯特·彼得(诗中“男爵”)在宴会上公然剪下名门闺秀阿拉贝拉·弗莫尔小姐(诗中“贝琳达”)的一绺秀发,两家因此反目。友人请蒲柏作诗化解矛盾纠纷,蒲柏慨然应允,并圆满完成任务:在史诗结尾处,青年男女尽释前嫌,终成佳偶,实现所谓“诗学正义”(而现实中的一笑泯恩仇则未能达成)。
《夺发记》诗题中的“强夺”(rape)一词在18世纪通常意指“强行夺取他人财产”,但亦可喻指带有暴力的性侵犯(“强奸”)——如莎士比亚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Lucrece)。对于蒲柏而言,将男爵违背女方意志偷剪秀发之举指为“强奸”无非是小题大作、滑稽搞笑(mock epic),但对年轻女子贝琳达来说,此举不仅是羞辱性的冒犯,更是赤裸裸的性侵。当时的读者极有可能对贝琳达“被夺发”后歇斯底里的过激反应(“她恐怖的尖叫撕裂了恐惧的天空”)大加嘲弄——而这或许正是诗人蒲柏所预期的效果。
蒲柏日后坦承,选择《夺发记》为题是他有意为之,“由于标题……类似小说,许多女性可能因此而误买误读”——在蒲柏看来,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易受书本封面包装所蒙骗。她们从来不会青睐寓意深刻的严肃文学作品,相反更中意格调低下的小说。蒲柏在诗中描述贝琳达闺房内居然有一本关于“蔷薇十字会”(RoseCross) 的故事书,明显带有鄙夷不屑的意味。
蒲柏的厌女症在《夺发记》开篇“序言”(“致阿拉贝拉书信”)部分便展现无余。在信中,他假装向这位女士解释“诗中几个难以索解的术语”,事实上却是故意侮辱她的智商:“我知道,在女士面前说些难听的话是多么令人讨厌;但是一个诗人最关心的,就是要让大家,尤其是从性别角度,理解他的作品……所以,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言下之意,即男女智力有高下之别:即便是阿拉贝拉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年轻女子,也需要经过成年男性苦口婆心的开导。随后,蒲柏又向这位贵妇作出保证:诗中偶有言辞不恭,但无伤大雅——“除了美艳过人,其他方面您与书中人物毫无共通之处”,并且断言,以夫人的文学才华和品位,一定不难识破诗中的讥讽其实是一种“自我解嘲”。
像荷马史诗开篇交战双方的排比铺陈,蒲柏在《夺发记》开头部分极力渲染贝琳达在赴宴之前精心梳妆打扮的场景。根据蒲柏描绘,贝琳达容貌举止宛似女神,她的闺房犹如一座“圣殿”,梳妆台上不仅陈列阿拉伯香料和东方的瓷器,更有来自帝国殖民地各处的奇珍异宝,以及若干本《圣经》——《圣经》并不是用来向他人炫耀的资本,真正想研读的人也不需要那么多本——可见贝琳达只是把《圣经》看作是一种身份的点缀和装饰。在蒲柏看来,这也体现出上流社会女性的共同特征,即爱慕虚荣。
对于贝琳达这样的贵族女性来说,宴饮、舞会之类的社交可能是她一天当中(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唯有通过社交,她才能在婚姻市场有所斩获,收获美满姻缘——前提是她必须拥有少女的身份(贞洁)和傲人的姿色。贝琳达的侍女爱丽尔(Ariel)以及“气精”(Sylphs)、“水精”(Nymphs)等众多精灵最主要的职能,一是守护她的贞操,一是装扮她的容貌,二者同样是她人生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因为在婚姻市场,女性一旦失贞,其身价立刻贬值,这也是贝琳达与男爵“闹翻”的根本原因——她担心自己此后在上流社会再无容身之地:“哦,我宁愿被人厌恶地抛弃在某个爱情荒岛或遥远的北方土地上……在那里,没人会在意我的容貌,就像沙漠中的玫瑰花那样——自生自灭。”
作为一名未婚女性,贝琳达在公开场合遭遇“夺发”,堪称是奇耻大辱。随着一绺秀发飘散而去的不仅是她的人格尊严,更是美满婚姻及其幸福生活。她一方面责备自己不该对男爵掉以轻心(“今晨命运女神已给我足够的提醒”),一方面对男爵的轻率之举充满怨愤,“哦,你真残忍!剪去几根隐蔽的毛发并不算心狠,偏要夺走如此暴露的卷发太过残忍。”——此处可见强烈的性暗示:照蒲柏的观点,贝琳达宁愿被强奸(强奸只是私下的羞辱),也不愿被当众夺发。如此一来,她不仅在私下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玷污,仿佛日后霍桑小说中猩红的“A”字烙印在她的胸口:她的“缺陷”(失发即失贞)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犹如中国瓷器上的一道裂缝”。
需要指出的是,在夺发事件中,贝琳达明明是受害者,但在患有厌女症的蒲柏笔下,受害者与施害者却轻巧被易位。男爵在社交场合公然施暴,令女方颜面大失,招致物议沸腾,而诗人蒲柏却像宴席上的长舌妇一样,反过来指责贝琳达“生性浮夸”,甚至进而将美貌归结为女性的“原罪”——“假如一个女人犯错了,看看她那娇俏的脸庞吧,你肯定会原谅一切”。在蒲柏看来,生性浮夸的贝琳达仅仅因为容貌昳丽就被视为德行过人而大受追捧,恰恰说明在两任乔治国王(以及摄政王)统治下,英国社会价值观及道德风尚每下愈况。
与此同时,诗人更以叙述者的口吻指控贝琳达故作冷艳,忸怩作态,以致环绕在她周围的男性“难以把持”:她美若天仙,对于在场男性而言,她的一颦一笑,都是致命的诱惑——因此,归根结底,假模假式的贝琳达被夺发完全是咎由自取。很显然,蒲柏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于两性的“双重标准”: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保持贞洁与纯真,以维护其人格尊严(并捍卫纯正血统);但另一方面又将拒绝男性调情的女人贬称为假正经(“只能像个贫困的老处女,孤独终老”),理应受到命运惩罚。
像《伊利亚特》中愤怒的阿喀琉斯一样,满腔悲愤的贝琳达(“柔软的酥胸竟能蕴藏如此强烈的愤怒”亦隐含嘲讽之意)在“地精”(Gnomes)协助下,向冥府的司脾灵女王(Queen of Spleen)求助,希冀通过发动一场“性别大战”向男爵复仇并挽回颜面。在蒲柏时代,司脾灵(脾脏,意指“愤怒”)一词是包括焦虑、抑郁和癔症在内的诸多神秘疾病的总称,其主要症状如昏厥、头痛、恶心等,往往成为女性(尤其是成年妇女)的“第二性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蒲柏笔下司脾灵女王的洞穴(Cave)堪称是女性神经官能症的渊薮:这里的女性无论年长年少,无不遭受各种奇怪病痛(如“相思病”)的折磨和困扰。
女王身边有两位侍女:一位名为“性恶”(Ill-Nature),“似一位老处女/身着黑白条纹衣,脸上满是皱纹”;另一位名为“做作”(Affectation),“相貌令人作呕/脸颊上泛着年方十八的红晕”。“做作”拙劣地卖弄风情,故作娇弱,动辄“变得满面愁容/宛似病态美人”。接着,洞穴中所有女人皆“因司脾灵发作而变形”——至此,女性完全被物化:有的变作饱满的茶壶,有的变作唉声叹气的罐子,还有的变作高谈阔论的鹅肉馅饼。在史诗的高潮部分,蒲柏形容“……姑娘们变成瓶子,大声叫唤着瓶塞”——其中的性意味不言而喻:女性本身既无知又空虚,唯有寄望于男性施恩才能臻于圆满。
值得注意的是,《夺发记》中的浪荡男爵只是因为“恶作剧”(男爵将这绺头发视作一种奖品——象征着贝琳达以及所有女性在两性战争中既是战俘又是战利品)受到轻微的嘲讽,相反,通篇几乎所有女性无不受到严厉谴责。与贝琳达一同参加宴会的克拉丽莎(Clarissa)助纣为虐——她一向假作正经,满口道德教谕,此时乃不失时机地为男爵“递上剪刀”——“甚至在他开口之前,她就已经将剪刀拱手奉上”。而贝琳达本人,蒲柏暗示,如果她懂得自我贬抑,就理应向世人隐瞒她的美貌,而非急不可耐地前往汉普顿宫赴宴(“妇女为了好名声,最好不要迈出闺门”)。至于宴席上的贵妇名媛,在目睹贝琳达卷发遭劫后,无不失声尖叫,仿佛在哀叹“她们最心爱的伙伴——丈夫和哈巴狗——不幸逝去”。
在蒲柏笔下,女人无论年龄大小,无不生性贪婪轻佻——宴席上贝琳达的眼眸“游移不定,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来回闪烁”,照蒲柏的推断,很显然,“她可以随时离开一个男人,只是为了从另一个那里获取更多愉悦”。所谓女人心,蒲柏断言,无异于“移动的玩具店”——她们人生唯一的乐趣就是贪图享受、追慕虚荣——“不要以为,当女子吐出最后一口气息,/所有的虚荣便会即刻消失:/哪怕死后,她仍会考虑身后的虚荣。”
正如评论家韦斯特福尔(Cassandra Westfall)在《蒲柏<夺发记>中的女性负面形象》(“The Negative Images of Womenin Pope’s The Rape ofthe Lock”)一文中所说,厌女症在蒲柏所处的时代并非偶然现象。小说家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是狡黠女性的化身:“一切希望在世界上得点好处的女人,都懂得如何保存她们贞淑的名声”,最擅长在成功男士中间周旋并伺机俘获猎物。剧作家康格里夫在《哀悼的新娘》中讥讽:“女人一旦发怒,胜过地狱烈火”。散文作家艾迪生给女人下的定义是“一种喜爱华丽服装的动物”。评论家爱德华·扬(Edward Young)也曾引用蒲柏格言,表达对女性的歧视和憎恶:“娱乐是妇女霸业之所在,/生来就擅长安抚和款待。/她们故作天真,却不乏精明,/何必费力找寻真知? /你一度无意说出的话千真万确;/‘大多数妇女毫无性格可言’。”
根据研究者一致的看法,蒲柏的厌女症一方面跟他的家庭出身及个人际遇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的情场失意。众所周知,蒲柏不仅因儿时患脊椎病而致身体畸形,成年后身长不过一米四,弓腰驼背,无法直立行走,而且终日饱受肠胃病、偏头痛以及失眠等病症折磨,因此只能长困于“司脾灵洞穴”之中——他曾自承洞穴中诸般病痛都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此外,身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在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英格兰既不能拥有名下私产,也不能担任政府公职,甚至没有资格居住在伦敦方圆十英里之内——像他所嘲讽的女性一样,他只配享有二等公民地位。恰如《蒲柏诗文集》编选者威廉姆斯(Au⁃brey Williams)在“序言”中所说,蒲柏在《爱洛伊斯致阿伯拉尔》中感喟女子有“千般哀愁”,在《夺发记》中哀叹女子为暴力胁 迫而“失去纯真”(loss of inno⁃cence)——“谁说玻璃脆弱、不能持久? 人间的美貌或荣耀消逝更快”——未尝不是诗人的顾影自怜和自我感慨。
尽管身形丑陋且疾病缠身,但蒲柏自恃才气在情场却从不怯阵。他曾向文友勃朗特小姐(Teresa Blount)求爱,遭对方婉拒。后来又向沙龙女主霍华德夫人(La⁃dy Howard)备述仰慕之情,可惜仍未获垂青。蒲柏的文坛对手宣称“(他)最优秀的诗作都源于情场失意”不无夸张,但基本属实——尤其是他与18世纪著名书信作家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一段长达数十年由爱生恨的情感纠葛,为他本人(及其对手)的讽刺诗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向蒙塔古夫人求婚失败后,蒲柏恼羞成怒,在《群愚史诗》(The Dunciad)中指名道姓,斥责夫人靠“卖弄风情”混迹文坛:她的游记书信大多出自文学情郎之手。此论一出,打击面甚广。小说名家菲尔丁随后奋勇加入战团,双方大打出手,成为18世纪英国文坛一大“景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中曾提及蒲柏另外一首长诗《论妇女性格》(“Of the Char⁃acters of Women”,1735)——二人对饮时,顽皮的奥兰多故意将一块方糖扔进蒲柏茶杯,茶水溅出,令后者大为不快,于是摇头晃脑责骂女人“不守法度”——其中有臭名昭著的格言警句:“有一个事实你之前从未留意,/大多数妇女毫无性格可言。”针对蒲柏谬论,蒙塔古夫人以她一贯的机智反唇相讥:“如果蒲柏的身体和他的思想一样强健,/对女性将是何等致命的诱惑;/然而命运的安排实在妙不可言,/上天增强他的头脑,同时毁了他的相貌。”——借用中国孔老夫子话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呜呼哀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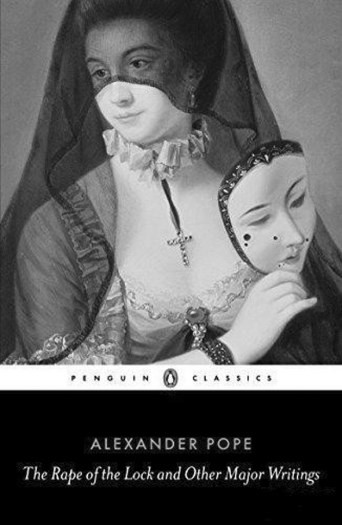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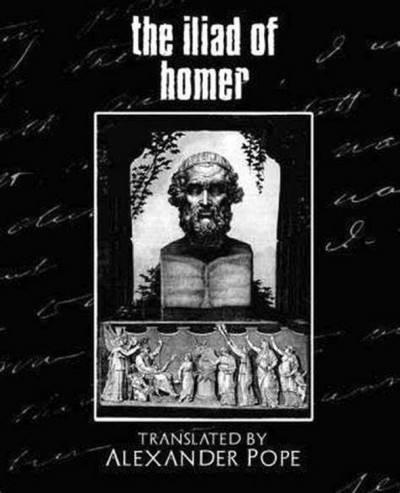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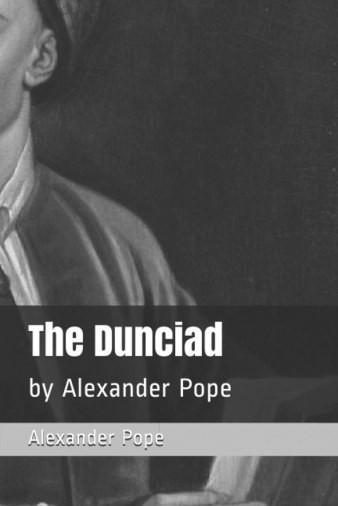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