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先生为我们这一级学生开“民间文学”课,是在1989年下半年,距今有三十多个年头了。也是在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这位老师。
说传说,一点儿没有夸张。刚入学时,就有高年级的同学跟我们讲中文系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老师的故事,薛宝琨是其中之一。一是因为他名气大,二是因为他有特点。流传的薛先生的故事之一,是说他在课堂上讲课时,提到中文系时,总是说“贵系”。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以为说的是旧时代的“桂系”军阀。既说“贵系”,显然,薛先生当时就不是中文系的了;同时,谁都听得出来,他既说“贵系”,也显然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在里边。不过,薛先生和中文系自有渊源,他以前曾在中文系工作过多年,而且讲的又是民间文学,与文学关系密切,所以中文系请他还在“鄙系”开课。彼时,薛先生在范曾主政的东方艺术系任教。
薛先生讲课,虽带着讲稿来,但讲时并不怎么看。在黑板上写下这堂课的主题,就开讲。往往一节课讲下来,黑板上就一个词,几个字。他梳着大背头,眼角很长,嘴角也很长。在我的印象中,他许多时候是站在讲台的左侧,重心落在右脚上,左腿伸向左前方,比稍息的步幅还要大一点儿;背着双手,头向左上方扬着,并不怎么看教室里听课的我们,而是眼睛望着左上方,好像在天花板上还有人在听他的课。
——果然,第一次上课,就亲耳听到他说“贵系”如何如何。
有些老师讲起课来或者读作品时,往往情绪饱满,或者说情绪激动,有时还会随着作品中的人物或喜或悲;还有不少老师在评论作家时,也比较情绪化,喜欢的,热情赞扬,讨厌的,怒声贬斥。薛先生不是这样的。他说话不快不慢,情绪也很稳定,没有什么过喜过悲的表达,总之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审视的态度;他讲课没有口头语,没有多余的零碎的话。总之,从语言表达到台风身段,都很有风度。
在20世纪80年代,能出书的学者还很少,而薛先生那时已经出了不止一本书。1979年,薛宝琨参加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承担了其中重要章节。此后,薛先生又出版《曲艺概论》(合著)、《相声艺术论》(合著)。为了学这门课,我从图书馆借过《民间文学概论》和《曲艺概论》。也是在这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薛宝琨和汪景寿、李万鹏几位大学老师在北京“邂逅”,在侯宝林的发起下,组成相声史论研究小组,按薛宝琨的说法,由侯宝林“直接参与指导”。他们的成果之一,就是1981年出版了《相声艺术论集》,1982年出版了《相声溯源》。
《相声溯源》这本书对于相声有多么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侯宝林认为,“相声这种民族民间艺术,集结、吸纳、整合、参悟了所有的中国文化”。“民间笑话和喜剧艺术的讽刺精神、优伶艺人卓立舞台见机而作即兴发挥的滑稽意识,文人学士在语言文字游戏方面的幽默智巧,都显现了中国文化‘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都蕴涵着中庸中和中正的思辨哲学。”所以,研究相声,意义重大。相声这门为广大人民热爱的艺术,究竟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这不仅关系对其本身的认识,也关系对其艺术规律的认知。今天的相声艺术不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它有着久远的源头。只有了解相声艺术的历史渊源,才能正确认识它的发展过程和形式特点,也才能由此探讨更普遍的艺术规律,推动这门艺术的繁荣发展。相声可溯之源虽然很长,但可证之史却很短。此前,虽然有罗常培、吴晓铃、杨荫深、林庚等学者对此做过探讨,但大都是散论和单篇文章,没有从总体上对这一重要课题做出较全面的研究。侯宝林从1949年开始,就有为相声治史立论的理念。仅由此一点,就可看出,侯宝林对于相声的贡献是整体性的,是学术性的,也是历史性的,远超出一般演员的贡献。而《相声溯源》的出版,正是侯宝林这一理念的初步实现,也是相声真正有史,相声研究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标志。
《相声溯源》虽是薛先生与侯宝林、汪景寿、李万鹏合作的著作,但薛先生肯定在其中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这从多年后,中华书局版《相声溯源》(增订本)(2011年)的再版前言能感觉到。侯先生名望高,但写作并非他长项,而且他社会工作繁多,不大可能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和写作中投入很多;汪、李二位,如果是承担了较多的写作工作,在前言中,薛先生会提到的;书的署名,顺序也是侯、薛、汪、李。这更可说明,此书的最主要的写作,是由薛先生承担的。
1984年,薛宝琨出版了《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一书,前一年,他还与侯宝林合作写出了《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艺术》,此书涵盖面很广,几乎对所有的俗文艺体裁都有较深入的论述,建立起薛先生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是在八十年代,中宣部策划,人民出版社组稿,出版了一套“祖国丛书”,其中,由薛宝琨撰写《中国的相声》一书。《笑的艺术》《中国的相声》连续两年获1986年、1987年天津鲁迅文艺评论奖,《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获1983年天津哲学社会科学专著三等奖,《中国的相声》还得过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在薛先生给我们上课的这一年,即198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
总之,这些著作,使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名学者。这样一来,他在课堂上的一些言语和做派,也容易使人产生些许误解。
“民间文学”这门课在中文系开了好几年了,一直是选修课,两个学分,也就是一周上一次,连着上两节。曾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薛先生曾在这门课上请过侯宝林来讲,也请过天津的一些相声名家。可惜,轮到我们上的时候,这些眼福耳福都没落着。
薛老师这门课的结课考试,是让同学们写一篇短论文。我自己写的什么题目,现在也忘记了,就记得最后薛老师给我的成绩是77分。
我到北京工作后,又因为工作关系,采访过薛老师。
1995年1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新创了两个周刊——《文化周刊》和《家庭周刊》。这是那几年报纸杂志化浪潮中两朵中央级的“浪花”。《文化周刊》是每周三出版,主编是沈卫星。编《文化周刊》第一版的,是杭天勇,兰州大学刚毕业,著名歌星杭天琪的堂弟,当时光明日报社围棋第一高手,业余四段。他那会儿锐气正盛,天天憋着要整些大稿子,要轰动轰动。这第一版是综合报道,头条要大选题,报道的分量也要相对厚重,一周一篇,压力不小。那一年,正好是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办,他就找我,想围绕天津做些文章。天津在近代史上,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但近些年,相比北京、上海,发展要慢许多,不妨围绕个中历史文化原因,做个报道。为了这个报道,我当然要采访一些天津的学者、作家,要请他们发言才比较合适,也能说到点儿上。在此过程中,就想到了薛先生。因为薛先生研究俗文学,天津在这方面有得说。
“打破天津文化弱势”发表在光明日报1995年6月14日第9版。“弱势”这个词,以前几乎没有在中央大报上出现过,这一下用出来,比较醒目。报道大概4000字,但历史、文化内容比较多,采访的人也比较有代表性,比如王辉、薛宝琨、冯骥才、滕云,还有朱光磊、张国刚等等。报道总体上不是一个常见的宣传的调子,而是比较纵深的报道,并且带有反思性,提出了问题。其中,借学者之口对天津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提出一定批评。批评最尖锐的,当数薛宝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薛先生讲完,我出于职业习惯,特地问他:“您说的这些话比较尖锐,我就这样原话报道,没问题吧?写成稿后,您要不要过目,再看一下?”薛先生说:“没问题,就这样登,你不用给我再看了。”
作为中央大报,冷不丁登出这么一大版带有批评性的报道,当然给天津市的震动不小。据天津的朋友讲,市里有关部门曾托人打听这篇报道的“背景”,天津高层专门还就这篇报道开了会。
薛宝琨是1961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就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当编辑,后来又到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在广播说唱团,他写歌词、相声、鼓词,也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不少曲艺圈的人,和侯宝林等人建立了友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广播事业局被砸烂,薛宝琨在劫难逃,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改造。后来,又迁到河南淮阳。在此期间他挨过批斗。据说,那几年他心灰意冷,就想在河南安家落户,种地为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薛宝琨和侯宝林坐在田间干活,那时侯宝林是“反动权威”,薛宝琨是“黑五类”,都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正经历着“人生最晦暗的时候”。在1966年以前,薛宝琨跟侯宝林的相处是彼此礼貌客气,互相尊重。1966年以后,两人一块儿倒了霉,一块儿下干校,就成了患难之交,无话不谈。当时并没有人向他们传达“林彪事件”,但是薛宝琨跟侯宝林说:“你可能要回去了,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侯宝林不信。薛宝琨说:“您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看我说的灵验不灵验。”果然,不到一星期,侯宝林就被宣布允许回家探亲,回去以后就再没有返回乡间劳动。一年以后,薛宝琨也回到了北京,回到广播说唱团。1973年国家政策有了调整,社会氛围也有变化。不过,薛先生已经不想继续在电台工作,于是,他回到天津,落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薛宝琨对侯宝林的研究,是在几十年的时间中逐步深化的。薛宝琨是这样定义侯宝林这个“大师”的,他说:“侯宝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相声大师,是举国闻名、世界瞩目的杰出艺术家。他继承并发扬了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改变并提高了相声的艺术格调。在相声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他起到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作用。”但薛宝琨并不是像一些学者一样,一旦研究某个作家,就无限夸大这个作家的成就。薛宝琨在充分肯定侯宝林的历史贡献之后,接着说,“侯宝林是这样一位大师:他不是作家,几乎没写过多少作品,但许多作品经他之手却立见新意、顿时生辉;他也不是语言学家,几乎在这方面并无专著,但是,语言一上他的口却变幻无穷、风趣盎然;他更不是评论家,几乎从不对艺术现象品头论足,但他却以他自己的行动回答了相声应该怎样和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他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他热爱这种‘俗’的形式,却又赋予它‘雅’的生命——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这些论述,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学术的严肃和学者的分寸。
《中国的相声》是薛先生独著的一部相声史,用薛宝琨自己的话说,是试图以贯通古今的“史话”方式,将近现代和当代相声发展的历史脉络,以不同层面的重点人物为代表,采取以点带面、史论结合、论由史出的办法,从焦点的括叙和评论中勾勒相声的历史概貌,揭示艺术发展的规律。他不无自负地说,此书“或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相声史论结合之作”。
薛宝琨虽然研究的是热闹的相声和曲艺,但他保持着学者的严谨和良知,有着深沉的历史感,不媚俗。前些年,马季去世时,媒体上对马季以“大师”称之,流行一时。对此,薛宝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他心目中的相声大师只有四位: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而马季算不上大师。
他说:“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达到经典的程度。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它延续或者承继了清代的话本小说这一脉,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化蜡扦》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他写传奇故事,写历史往事,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用相声讽刺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第三位是侯宝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儿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马三立,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对底层民众熟悉。”薛先生的论断,可以说清音独响,让公众有个清醒的认识。薛先生说,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任何大师都是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沉淀,“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是在他去世十年以后”。
薛宝琨在研究曲艺特别是相声的时候,注意挖掘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特别关注与分析不同演员和创作者的美学特点,对这些加以概括,并加以理论的总结。他出手的文章论著,都是资料翔实,有理论深度,而且文笔优美畅达。他有深厚的美学理论素养,有深厚的文史知识体系,评论客观中肯,高人一筹。他直言那些名家各自的优缺点,不徇私谊。谈优点,不溢美;谈缺点,中肯而又“婉而多善”。所以,被评论的、被批评的那些即使是很有名的明星,也都服他的气。他以“文而不瘟,雅俗共赏”概括苏文茂的相声风格;以“绚丽也平实”评论刘文亨的艺术特点;他评论魏文亮,说他深知“相声味儿”,懂得相声的奥秘不止于语言的“婉而多讽”,还在于它的奇思妙想,魏文亮擅长的模拟“因童趣而更加离形得似”。薛先生的相声评论和研究,不仅使研究者受益,也使相声演员受益,使众多相声爱好者受益。大家因他的工作而更加了解相声、热爱相声,观赏者也学会了欣赏相声,提高了欣赏水平。薛先生认为:马三立是津门相声的魂魄,马三立的表演本真、自然、朴巧,心平气和绝无造作;马三立的风格虽可用一“俗”字代表,但不是伪俗、低俗、庸俗,而是真俗、大俗、美俗,是大俗入雅。薛先生从刘宝瑞“迟急顿挫”的节奏里,看出有书路(评书)的起承转合,从刘宝瑞的“顶刨撞盖”的语势里,看出气氛的浓淡张弛,他甚至从刘宝瑞“铺垫系抖”的包袱里,看到人生和生命的“成住坏空”。
这是怎样的一种欣赏和共鸣啊? 可以说,薛宝琨不仅是侯宝林先生的知音,也是所有相声演员的知音,说他是相声在学者中最大的知音,恐怕也不为过。
大概十年前,我回天津,还见过一次薛先生。我当时想约薛先生写文章,和我的研究生老师张圣康说起来,张老师就帮着联系,又一起和我去了一趟薛先生家。
张老师和薛先生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薛先生虽然晚两级,但他们关系一直不错。那次见面,聊的时间也不长,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那时,薛先生的听力已经很不好,一般说话,他听不大清楚,所以和他交流也不多。只是他和张老师聊一些闲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薛老师。
2016年2月28日上午,薛宝琨在天津市黄河道医院逝世。
薛宝琨是天津人。1935年生,与圣康老师同庚,都属猪。1948年,薛宝琨报考商业职校,1950年,薛宝琨在知识书店当实习生,站了一年柜台,转年复学,到1954年在天津医药公司采购供应站当会计。1956年,薛宝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反右”之后,他钻研外语,想搞翻译。我查网上的材料,知道薛宝琨是1956年入党,但因替别人打抱不平,便以“庇护右派”和“走白专道路”之名取消了预备期。1979年北大为他恢复了党籍。薛先生有天津人的智慧。据说,他曾提出“三小主义”,即,在小城市生活,找个小单位,做个小差使。这也使得他在“文革”中遭到批判。
有人统计过,薛宝琨出版过十几本书,除了前面所举,还有《中国人的软幽默》《怎样欣赏戏曲艺术》《中国说唱艺术史论》《薛宝琨说唱艺术论集》等。《中国幽默艺术论》获1993年华北五省市文艺理论专著一等奖。《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中也获一等奖,此书曾在台湾出版并一版再版。1992年,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志”丛书,其中《艺文典·典艺志》,就是请薛宝琨撰写。薛先生还应中国曲协“《当代中国》丛书”之邀,撰写《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201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薛先生主编的《相声大词典》。
薛先生有老派文人的道德操守。从公德说,他作为学者,正直,讲真话。比如,那次他对天津人文化性格的直言;比如,几十年来,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在书中对他所熟悉的众多曲艺界人士、包括许多相声名家的评论,他都实事求是,立足作品,立足创作实绩,把他们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中,给予一个恰当的评价。他曾公开说:“我一个学者不能说违心的话,虽然违心之说能得到好处,但是那样就不是薛宝琨了。”从私德说,也有一件事,让大家钦佩。因为薛先生的夫人长年卧病在床,所以薛先生开会时从不在会议上用餐,而是赶回家亲自照料妻子的饮食起居,二十多年如一日。反观时风,还有近年不断爆出的高校教师的各式“新闻”,怎不让人感慨。
受薛先生感染,南开有不少学生,后来都从事与曲艺有关的工作。其中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是薛先生的得意门生鲍震培。2005年5月,全国第十五届书市在天津举办,《中华读书报》做了一个专刊。我专门请鲍震培给我们写了一篇“说唱艺术天津魂”,为报纸增辉不少。鲍震培近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相声病了,得治”(2018年8月18日),很犀利,很中肯,影响很大。这篇文章的风骨和专业水平,让我又想到薛先生。
我与薛先生交往很有限,所知也很有限。但他毕竟教过我,是我的老师,写一篇文章,简要地记述他的事迹,表达怀念,也是应该的。
薛先生曾说:“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必将是美好的回忆。’——是的,我们这一代确实浪费过许多光阴,但生命和人性却并未曾有过一丝毁灭。我们曾经不幸过,但我们今天却是万幸的。我们经历的或许有过太多的痛苦,但我们回味它时却在不断荡起的淡淡哀愁中发现了无可重复和永存无限的快乐。”——这段话现在读来,仍不免让人怅然。
(本文摘自《南开风语人》,祝晓风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4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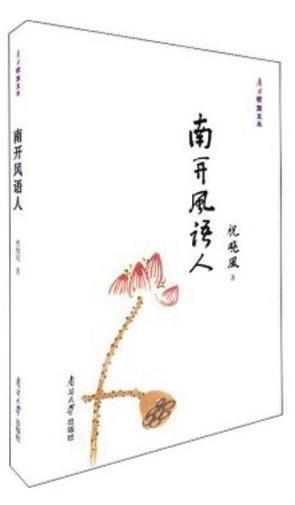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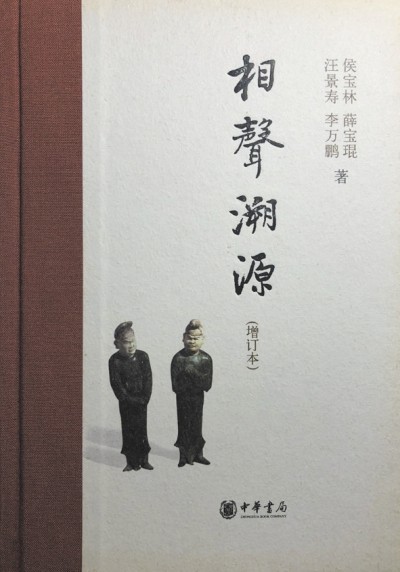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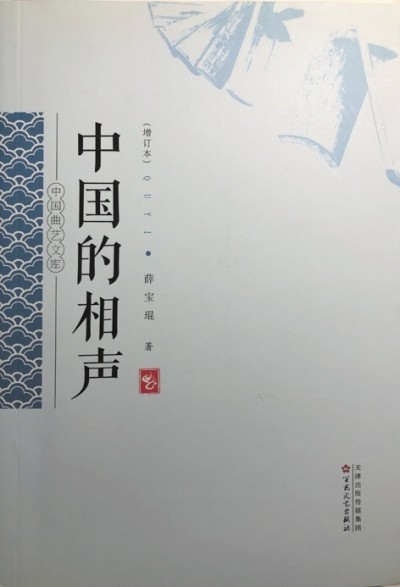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