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复平(Mark Halperin)《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Out of Cloister: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960-1279,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收入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了。这部书基于宋代“寺院碑记”,分析了唐宋之际文人的佛教观出现了哪些变化,考察宋代知识精英对佛教的态度,由此呈现了佛教在宋人精神生活中的真实情形。
作者认为,佛教在宋代并没有被宋代理学边缘化,而是融入到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孩提时代,他们就开始接触佛教,会经常听到亲人们在唱诵佛经,或者是和父母一起去寺院烧香。在求学阶段,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佛寺里准备科举考试,在远赴他乡参加科举考试期间可能会寄宿在佛寺里,并向僧人卜问前程。有时候,科举考试也会被安排在寺院进行。当他们到地方上任,作为地方官,他们需要向寺庙征税,并要维持寺院及其周边的秩序,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还要为寺院选任新的住持。在桥路建设或是赈灾扶贫的工作中,他们也可能要求助于寺院。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僧人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丧葬事宜就离不开僧人的帮助。对于那些被贬或退休的官员,佛寺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地方,如黄庭坚等人和僧人交游就颇为频密。
依据佛教和世俗社会中不同群体或阶层的关系,可以划分出皇室佛教、民众佛教、士大夫佛教等不同类型。同皇室佛教利用佛教维护统治秩序,民众基于功德福报考虑而信仰佛教不同的是,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具有一定超越性的,“即超越自身利益而关心天下福祉,进而关注真理本身”(本书“译后记”)。这使得宋代文人的佛教观,并不能与佛教信仰等量齐观。他们对佛教的态度,表现了士人阶层对“天下”“苍生”和世俗社会的看法,表达了某种社会理想、政治抱负。
从文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互动角度来看,佛教是“融入”宋代文人生活之中的。但这种融入,又是有边界的。例如,以苏轼为代表的护教文人(本书第二章),一方面反对禅宗中摈弃“方便”的激进观念,讲求在真谛和俗谛之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又非常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关注教义而更关注佛教与世俗联结的地方。宋代的护教之论关注的是儒佛相通性的问题,是对真理本身的探究,形上,但不“出世”。
仿韩愈《谏迎佛骨表》上奏排佛的王禹偁(本书第三章),其排佛情绪同样不能与宗教信仰划上等号。他本人为佛教寺院写下的多篇碑记作品,恰恰是在揭示佛教的世俗教化作用。其前辈韩愈之所以秉持强烈的反佛态度,更多地是因为安禄山叛乱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和政府的财政,认为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寺院、日益增多的僧众,大大耗费了国家的资源。韩愈从稳定社会秩序角度提出的崇儒抑佛,考虑更多的还是世俗社会的利益。(李天石认为,韩愈被贬,《谏迎佛骨表》的反佛立场只是诱因,真正原因是他对皇帝权威的质疑。见李天石:《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论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宋代士人对佛教的非议主要是从文化衰落、财政依附角度展开的(本书第四章),他们将寺院碑记作为针砭时弊的平台,反对朝廷对佛教活动给予过多的关注和支持(如苏舜钦《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曾巩《鹅湖院佛殿记》)。当然,宋代文人对佛教的非议还包括批评那些不能践行自身责任的僧人,在他们看来,僧人们和尘世中的俗人(特别是文人)一样,也是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腐化的世界中。但即使反佛情绪激烈者,与寺院、僧人的联系同样没有中断过。比如欧阳修,他力倡传统礼仪,为此曾耗费大量时间去建立家族的祠堂,还延请道士以作照料(刘子健(James T.C.Liu):《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Ouyang Hsiu:An Eleventh Century Neo Confucianist),第165页),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还是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同上书,第170页)。
宋代文人的寺院记忆同他们的文人身份并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讲,文人的感受反映了佛寺如何发挥了学校、图书馆、驿站和守墓人的共同功能的。因此,无论士大夫是否喜爱佛教,寺院都和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第五章)文人与寺院的关系,折射出佛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文人们能够以一种更虔诚的眼光对待佛教,以一种专注的态度来学习佛经。这是佛教“融入”宋代文人生活的一个例子,但这种“融入”,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泾渭分明。从这意义上说,宋代文人的佛教观,是从教义之外、信仰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角度去看待佛教,是超脱的视角,或者可以说:佛教不是融入了宋代文人,而是游离于宋代文人信仰体系之外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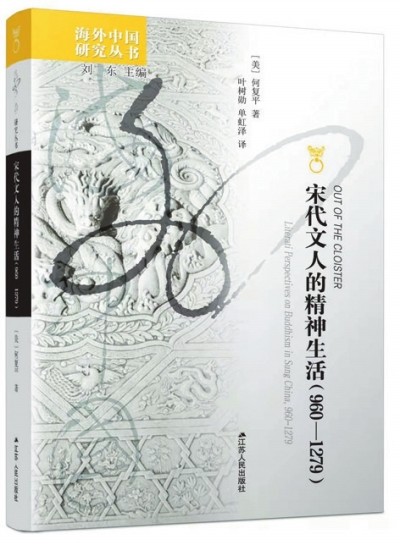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