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想编《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这本书? 这本书从酝酿出版,为什么先后折腾了三十年? 这本书有什么用处,还有什么不足? 大家知道,鲁迅最初是通过翻译活动走向文坛的,最早的成果是跟二弟周作人共同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这本书得到朋友资助,在日本东京分上、下两册出版,在上海市找了一个绸缎庄寄售。上册印了1000本,卖了20本;下册印了500本,也只卖了20本。后来这绸缎庄着火,存书和纸版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本书被冷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还不习惯于阅读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作品,不知为什么文章刚刚开头就很快结了尾。中国人看惯了章回体,动不动要看八十回,或一百二十回才过瘾;看戏也要看连台本。40年前我在山东泰山开会,住在泰安宾馆,那宾馆外面是一片空地。那时农民家有收音机的人少,电视机则几乎没有。每天傍晚,人们就带个小板凳围坐在那空地上,在电线杆上悬挂的大喇叭底下听刘兰芳讲评书,像赶集一样。这是当时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读者和听众的文学欣赏习惯。
中国读者是通过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才开始接触现代短篇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概念不清,又缺乏科学分类,但实际上存在着文言小说跟白话小说两个传统。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油印讲义到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才被梳理出一个粗略的历史轮廓。所以鲁迅1923年10月7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
简单地说,先秦时期,文史不分,小说文体并未独立形成。文言小说,有作为中国神话宝库的《山海经》,有东晋史学家干宝撰写的《搜神记》(其中杂入了他人之作)。文学价值最高也最符合小说特征的是唐代的传奇体小说。像元稹的《莺莺传》,后被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西厢记》。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出现,说书艺人创作了大量的白话小说,主要是短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话本小说,其代表作见于《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到了明清两代,长篇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金瓶梅》是奠基之作。后来出现了章回小说《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但在创作领域诗文还是正宗。
历史上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场合。几乎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时,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发表了一次讲演,题目叫做《论短篇小说》,后来由傅斯年记录,经胡适修订发表。这次讲演就是为了厘清现代短篇小说的概念。胡适说,不是篇幅长就称之为长篇小说,篇幅短就称之为短篇小说。长短篇小说的区别不单纯取决于篇幅和字数。西方的短篇小说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选取生活素材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也就好比截取一棵大树的横断面。锯开大树看“年轮”,可以了解这棵树的寿命。第二个特征是文字简洁,恰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凡是可扩充为章回小说的短篇则不是真正的短篇。我认为,胡适所强调的这两点,第一点是根本,第二点可以视为对一切文体作品的共同要求。中国古代小说往往重视故事的完整,情节曲折,叙事奇巧,首尾相应,高潮迭起,悬念不断,如一条游龙,蜿蜒起伏,上下翻腾。这原本是由说书的需求决定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没有情节的起伏跌宕,听众就会坐不住,更不会下次掏钱再来听书了。
西方短篇小说则不同。胡适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法国作家都德创作的《最后一课》(一名《割地》)。这篇小说虽以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为题材,但并没有正面描写这场战争,而是运用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选择了韩麦尔先生所讲的最后一堂法语课。因为法国的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德国之后,法国人面临着不能学习母语的民族悲剧。作者通过一个小学生小弗朗士的叙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成立后,这篇小说长期被选进语文教材,影响并感动过几代人。当然,当下也有人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就是法国掠夺的,居民说德语的居多,但这是历史学界争议的问题。如今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仍属法国版图,学校多进行德语与法语的双语教学。
胡适在这篇讲演中,特别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的趋势是由长趋短,由繁入简。简而言之,抒情诗,独幕剧,短篇小说这三种体裁代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即使是写短篇,也不能为讲故事而忽略了对人物灵魂的揭示。
也还是当年4月19日,周作人同样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发表演讲,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周作人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写小说是一种下等行为。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视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由于新小说可以培养国民新型的道德和人格,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所以“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就是上等。
但是,虽然有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文学的小说却一本也没有”“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因此,周作人希望中国的小说家能借鉴日本小说的创作经验,这经验用五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创造的模拟”。周作人所说的“模拟”就是我们所说的“借鉴”,“创造的模拟”就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实现跨越。中国的新小说不仅要具有新的形式,同时也必须表达新的思想,这就需要从头做起。我认为周作人这种新小说观,鲁迅也是认同的。如果说,胡适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倡导者,那么鲁迅就是这种理论在创作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大家都承认鲁迅是文学家,而为鲁迅奠定文学家地位的则是他的小说。鲁迅创作的小说并不多,结集出版的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这三种,一共收录的作品33篇。我以为,仅凭《阿Q正传》这一篇就可以使鲁迅在“文学家”这个称谓之前再加上“伟大的”这个定语。阿Q这个精神典型很快大踏步地进入了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的画廊,所以鲁迅也就成为了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狂人日记》不是不优秀,但作品的内容是颠覆中国的旧道德,旧伦理,跟外国的一般读者难免产生文化隔膜。
创作小说,首先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丰富的人生阅历,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但同时还必须汲取中外文化滋养,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明确说过,他创作小说之前并没有读过“小说作法”之类的理论书籍,而“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众所周知,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过医。他塑造《狂人日记》中那个“迫害狂”的形象,就仰仗了一些神经内科方面的知识。至于他以前究竟读过哪百来篇外国小说,我原先觉得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离开了人证、物证、旁证,谁有本领开列出这百来篇外国小说的篇目呢? 从1989年起,我开始研究鲁迅藏书,并发表了一些短文。1990年代初,我又申报了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叫《鲁迅藏书研究》。我的同事、师姐姚锡佩在查找鲁迅收藏的剪报时,发现了一册装订好的日译外国短篇小说,共八篇。这就是鲁迅留日期间阅读日译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这一发现增强了我探寻鲁迅1918年之前所接触的百来篇外国小说的浓厚兴趣。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是三十年了。所以,我说《他山之石》的出版,是实现了我三十年来的一个夙愿。
这本书从酝酿到出版为什么会折腾三十年?
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剪报册共装订了十篇俄国文学作品,我们称之为《小说译丛》。涉及的作家有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普希金这四个人。然而鲁迅当年并没有阅读俄文原著的能力,他所接触这些小说都是日文转译的,其中少数的篇名日文与俄文一致,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外套》,都是写当时俄国小人物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的译名跟俄文原作对不上号。这在翻译活动中本是常见现象。比如鲁迅的《二心集》,原意是跟旧中国的旧政权两条心,但俄国译者曾翻译为《两颗心》,似乎是在谈情说爱。鲁迅的杂文《三闲集》,书名原本是讽刺创造社的成仿吾认为他是“有闲阶级”,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但俄文译者曾被翻译为《三个游手好闲的人》。日本明治时代对于外国文学一方面是如饥似渴地引进,另一方面在翻译时又太不拘小节,有增有删有改写,甚至把作者的名字和国籍都搞错了。这种翻译风格被称为“豪杰译”。日本译者这种“豪杰”做法,就让我们吃尽了苦头。比如剪报中有一篇屠格涅夫的《妖妇传》,顾名思义是一个妖里妖气女人的传记,但连俄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没听说过屠格涅夫有这篇作品。要读屠格涅夫的原著,首先要精通俄文。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学过俄文,但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而中断了,远没达到阅读俄文小说的水平。另外,一般单位也没有俄文版的《屠格涅夫全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梁展告诉我,《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版中国以前只有翻译家戈宝权收集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图书馆馆藏本也有残缺。找全屠格涅夫的俄文原著更加困难。一是看不懂,二是找不到,想继续研究就会卡壳。后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竹内良雄教授到中国访学,我拜托他去查。他查遍了日本的大图书馆,也只搞清楚了这十篇俄国小说日译文的原载刊物。彻底查明这十篇小说篇名的是东北师范大学孟庆枢教授。他是我的老朋友,精通日文,又精通俄文,多年在日本讲学。他发现,《妖妇传》的准确译名应该是《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宿命论者》原来只是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当中的一节,果戈理的《昔人》应翻译为《旧式地主》,屠格涅夫的《森林》应译为《波列西耶之行》。在俄文中,“波列西耶”的意思是“森林连绵的洼地”。我们原想请一些翻译名家来翻译这十篇俄国小说,但目前一般翻译费比稿费还低,译者难找。有的名家跟出版社签的是终生版权的合同,无法转让或重复授权。因此,改译编写起来也十分不易。《域外小说集》也是鲁迅早期阅读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这部译文鲁迅亲自翻译了三篇:安特烈夫的《谩》和《默》,迦尔洵的《四日》。这鲁迅当然读过。其余13篇都是鲁迅二弟周作人的译文,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同吃同住,共同从事文学运动。《域外小说集》出版时,鲁迅审改了文字,又亲撰了《序言》《略例》,他当然也读过这批外国小说。胡适虽然高度赞赏这批译文,认为文词朴讷,超过了桐城派的翻译家林琴南。但桐城派的文字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即内容合理,材料确切,文词精美。然而这种文风在五四时期沦为了末流。周氏兄弟受业师章太炎影响,有复古之风,文词古奥,今天的读者直接阅读《域外小说集》的译文困难超过一般古文。所以我们又请学者认真将周氏兄弟的文言译文改写成现代白话。这也得花费不小功夫。所以,如果没有姜异新博士的合作,这本书再过三十年我也编不出来。姜博士不仅为本书撰写了一篇提纲挈领的长篇序言,而且组织力量完成了本书的编译工作。从这个意义上,她应该列名于第一主编。
《他山之石》的阅读价值与不足
如果从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报道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算起,鲁迅研究已经有了112年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相对成熟的综合性学科,也可简称为“鲁迅学”。这门学科的史料已经基本齐备,今后很难再有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发现。对鲁迅评价也基本正确,很难产生颠覆性的看法并能在鲁研界占据主流。对鲁迅作品阐释当然空间无限广阔,但鲁迅对自己的很多代表作已有自评,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也很难超越鲁迅本人的自我认知。所以,鲁迅研究学科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致使有的学者知难而退。有个别学者则通过过度阐释或故意曲解的方式哗众取宠,吸引大众眼球。这好比人的正常体能是有一个极限的。据说世界上有个活得最长的人,是英国的弗姆卡恩,活到了290岁,这很不可信。人到百年,就已经成为寿星了。世界男子百米短跑的最高纪录是9秒58,是牙买加名将博尔特2009年创造的。中国名将苏炳添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跑出了9秒83的好成绩,也震惊了体坛。要把男子百米短跑的速度再提高哪怕是零点零几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提高鲁迅研究的水平同样艰难。
《他山之石》的出版,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读者不应该仅仅关注鲁迅哪篇小说受到了哪位作家的具体影响,比如《狂人日记》的篇名取自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药》的结尾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这样的例证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通过阅读这本书,进一步研究鲁迅在创作中国现代小说时在文体上进行的大胆探索,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为什么形式都很不一样? 特别是《故事新编》,为什么又采取了古今穿越的手法? 鲁迅对这些外国小说精神上的继承和发扬更值得关注。鲁迅讲得很明白,他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寻求的是反抗和叫喊的声音。他从俄国文学作品中明白的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所以,我们从鲁迅的阅读和翻译的文化取向中应该学习的首先是鲁迅的平民立场,以及对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
这本书当然还留下的不少遗憾。这种遗憾首先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些翻译家造成的。他们的“豪杰译”没有使当年的鲁迅从中品尝到那些俄文作品原著中的原汁原味,当下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当然也无法充分感受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所以,只能以这本书为媒介,今后去阅读这些作品更优秀的完整译文,乃至于直接从外文原著中去汲取更加丰富的滋养。根据二流、三流的译文去欣赏西方的一流小说,那感受肯定会差得很远。所以有人说,文学作品是无法翻译的。对此,作为编者,我们应该向诸位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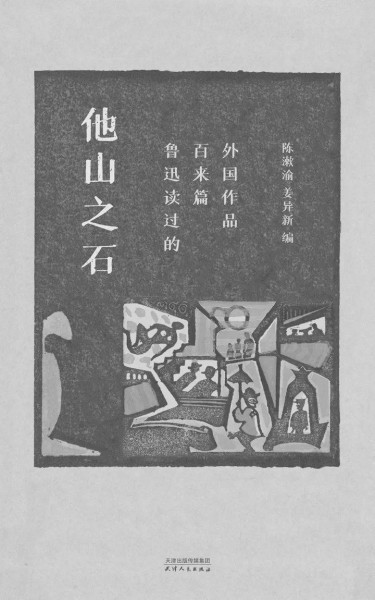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