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荒野,翻译《恶之花》,不觉已近一年。偶尔望一眼“窗外”,仍是“薄暮”——“这迷人的傍晚……”无论是看见眼前的现实落入诗中,或诗中“薄暮”再现于眼前,同样值得欣慰——我们难道不该从“恶之花”丛中捧出“拾荒者的酒”“孤独者的酒”“恋人的酒”……并为此干杯,敬一敬那长存的酒魂、诗魂,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放在今天又是怎样的光景?
的确,对我而言,“翻译”是一种深度阅读,是陪伴作者的一段艰辛旅程,它有助于我们忍受苦难、孤独——曾经有过这样的灵魂,比我们承担了更多的绝望、孤苦,我们难道不该因此释然,并重拾作为人类的一点尊严,重获些许生的勇气与信心么?
正如“薄暮”时分,我又听见肖邦钢琴曲,从遥远的波兰华沙传来——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每每听闻这样的琴声,受伤、绝望的灵魂,瞬间深得安慰,并坚信世纪流转,真正穿透尘世喧嚣与历史风尘的,惟有高贵的灵魂——他们身前蒙受的屈辱、承受的苦难,有如薪柴之于火苗,给后人带来绵绵不绝的光明与温暖。就像当年万般无奈的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跟后世是有关联的。”果然一语成谶。
而作为后世的我们,能否担当得起这份隔世厚望与沉甸甸的友情?
今年恰逢夏尔 ·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诞辰200周年,恭喜北京大学法语系的董强先生曾倾尽心血翻译的克洛德·皮舒瓦撰写的洋洋巨作《波德莱尔传》得以再版重生,关于波德莱尔的生平、逸事尽在其中,这里无须赘言。只是作为一名《恶之花》的新译者,我私下里赞同董强先生的导师米兰·昆德拉的观点:认为诗人的日记、书信、文章都不是作品,并质疑生平与作品的关系。正如《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所言:“对‘自我’稍有认知的人都会明白:从事创作的‘自我’,并非我们在日常的社交、习俗及恶行中体现出的那个‘自我’。要理解这个创作的‘自我’,我们惟有探索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接近它。这是一次心灵的朝圣,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我想,如果将《恶之花》的创作过程比作这样一次朝圣,同样恰如其分。
我现在相信,了解波德莱尔“本人”是一回事,了解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是另一回事。难怪通灵诗人兰波说:“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或许可以理解为“我”是生活中的“我”,而这“另一个”,即是作为“诗人”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尽可以研究波德莱尔的生平、逸事,但不宜将其诗歌与当时的某位情人、朋友,或某一段生活一一对应;因为那样发现和找到的,只是波德莱尔的“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而非“另一个”;而诗人的灵魂,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在生命之上“遨游”——“诗人”灵魂出窍,在现实中无处安放,只有寄托于某人某事;尽管“某人某事”触发了诗人灵感,却不可等同于诗歌的源泉与归属。
如此看来,我发现《恶之花》本身,更像是一部具体而微的“诗人自传”:从“出生”到“死亡”(如《致读者》《祝福》《伊卡洛斯的哀叹》),从现实生命中的各种“处境”(如《信天翁》)与“心境”(如《忧郁》之一到之四、《虚无的滋味》、《雾和雨》),以及他与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与自身的关系,连同对“自我”“民族”与“祖国”的理解(《我喜欢裸体时代的回忆》),对平民(如《致红发女乞丐》)及革命者(《西西娜》)的情感,尤其是对于“诗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刽子手》),一应俱全。——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何事最难为?”泰勒斯回答:“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中的箴言,显然也铭刻在波德莱尔心头——从《恶之花》的“缘起”看来,从一出娘胎(《祝福》),到埋进黄土(《墓地》),葬身深渊海底(《伊卡洛斯的哀叹》),无论是在天空“遨游”(《遨游》),或躺在“妓女”身边(《入夜,我依偎着……》),无论是被封在酒瓶里(《酒魂》),或漫步在街头(《巴黎即景》诸篇)……上天入地,“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认识自我”,并寻找知音——或许“自我”就是“诗人”苦苦寻觅的知音,亦未可知;只可惜他同时也是“自我刽子手”(L' Héautontimo⁃rouménos),如厨师烹煮并吃自己的心(《幽灵·黑暗》),注定陷入黑暗与绝境。而绝处逢生,或许只在后世,在我们。呵呵,说句玩笑话:读《恶之花》你就惨了;或因为你惨了,所以要读《恶之花》,这两者有何区别? 不如“认了”。而世纪流转,人类世代,总有“该隐的种”(《亚伯与该隐》)为万人唾弃,“无可救药”的灵魂,他们至今手持“撒旦恩赐的火把”——对“恶”的认知,认识自我,探求真理,并以此作为“惟一的光荣与慰藉”(《无可救药》)。
重读《恶之花》,第一印象即是“诗人”的出生及“母亲”的发誓诅咒。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从降生之日,便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宿命”。通灵诗人兰波曾在给导师的书信中说:“如果青铜觉醒,发现自己是一把铜号,这不是它的错。”换句话说,有如“青铜”意识到自己是一把“铜号”,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一名“诗人”,皆天性使然,无法改变,“这不是他的错”;这种“觉醒”在兰波大约七岁完成(见《七岁诗人》)。而波德莱尔似乎更早,如《恶之花》开宗明义:“当诗人奉了天神的崇高旨意,/降临在这苦闷的人世间(《祝福》)”,可见这种对于宿命的认知,与身俱来,先知先觉。然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与此同时,“诗人”已预感到自己天生的不幸及悲惨命运,以至于“惊恐的母亲,朝着悲悯的上帝。/亵渎、诅咒,捏紧双拳”:
——啊,我宁愿诞下一团毒蛇,也不要生养这嘲笑世界的孽种,真该诅咒那一夜的及时行乐,害得我的肚子从此罪孽深重。
尽管日后,“诗人”“与清风嬉戏,和流云谈心,/在受难的苦路上歌咏、沉醉”;然而,“他所爱之人都对他存有戒心……/在他身上试验着他们的暴虐残忍……”这便是“诗人”悲惨的出生,“厄运”的开始——生于人世间,“诗人”灵魂的状态及在现实中的处境又如何? 好比“信天翁”,被船员钉在甲板上,百般戏弄、嘲讽:“一个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嘴巴,/另一个蹒跚跛足,模仿着飞天的残疾”,而它巨大的雪翅如双桨拖在两侧,“冲天羽却妨碍它在地上走动”。而沦落人世间,“诗人”又如“病缪斯”在精神上深陷沼泽(《病缪斯》),在生活中苦苦挣扎,为稻粱谋(《谋生的缪斯》),并在遭遇“厄运”之时:“远离显赫的坟墓,/向一座孤坟走去……”(《厄运》)。
如此“出生”与“境遇”,自然将“诗人”逼上绝境,而成为异类,“陌生人”。在散文诗《巴黎的忧郁》中,开篇即是《陌生人》的自问自答——
告诉我,你这神秘的陌生人,说说你最爱谁呢? 父亲还是母亲? 姐妹还是兄弟?
——哦……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那朋友呢?
——您说出的这个词儿,我至今一无所知。
——祖国呢?
——我还不知它坐落在何处……
对于这样无解的“世纪疑问”,我们不妨从《恶之花》中寻找答案:从现实生命中看,波德莱尔六岁丧父,而“精神之父”似乎也随之而去。对于“父亲”,波德莱尔一向讳莫如深,却在《恶之花》中,泄露了天机:在《地狱中的唐璜》中:“斯卡雷纳尔嬉笑着讨要工钱,/唐路易伸出颤抖的手指,/要让河岸飘荡的亡魂都来看看/那嘲笑自己满头白发的逆子”——
这位唐路易正是唐璜的父亲;“诗人”自比唐璜,而这下地狱的“逆子”(le fils auda⁃cieux)同时也是“勇敢、放肆的孩子”,无惧众亡魂的目光,公然嘲笑自己“满头白发的”父亲。而在另一处,这“逆子”的心机隐藏得更深,也更加凶险:在《远行》(七)中,当我们将登船,驶向幽冥之海,听见那歌声,迷人而悲哀——“请来这里,你们这些想品尝/蒌陀果美味的人们! 这里有/你们心中渴求的神奇果实;/在这永无尽头的绵绵午后,/尽情采撷,并沉醉于芳馨甜蜜!”——“从这熟悉的口音,我们猜到了那位幽灵;/是我们的皮拉得斯,在向我们张开双臂。”——皮拉得斯(Py⁃lades)是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儿子俄瑞斯忒斯的堂兄兼密友;阿伽门农遇害,凶手正是俄瑞斯忒斯母亲的情夫。俄瑞斯忒斯最终选择了复仇,与皮拉得斯一同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而这惊天的秘密,就藏在“迷人而悲哀的”歌声中。由此让人自然联想到波德莱尔的“个人隐私”:六岁丧父,母亲改嫁,与继父水火不相融;而本着“就诗论诗”的一贯立场,我更愿意将这份“隐私”,看作是一种精神上更深远的“隐秘”——
在拉丁文诗歌《弗兰西斯卡颂歌》(“Franciscae meae Laudes”)之后,波德莱尔附加了这样一段文字:“读者难道不是和我看法一致么? ——拉丁语,这最终衰落的语言,一个强壮者崇高的叹息,已然转变为精神生活,并准备好恰如其分地表达对于现代诗歌世界的理解和对激情的感受。神秘是这块磁铁的另一极,卡图勒之流,全凭本能的粗鲁诗人,只知道感性这一极。”无论作为作者或读者,但愿我们不要成为法国诗人“卡图勒之流”。由此,我想,真正的“诗人”(波德莱尔)与读者,就好像司芬克斯与俄底浦斯,前者出谜语,后者猜谜,而不是相反。难怪司芬克斯常出现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并成为象征中的象征,一如“神秘”或将成为开启《恶之花》及现代主义的一把钥匙。
再看“诗人”和他的母亲。我曾在拙作《在荒野“遇见”兰波》中,同样以“就诗论诗”的方法,探讨了兰波与“母亲”的关系,及兰波在现实中及精神上的截然不同的“两位母亲”;同样,波德莱尔也有“两位母亲”:现实中令人绝望的母亲(用兰波在《七岁诗人》中的话说:“她有一双会撒谎的蓝眼睛”),与自己心灵深处,无比依恋的“母亲”——她有许多化身,如《秋歌》诗云:
可依旧爱我吧,爱人芳心!当一回慈母,哪怕对一个恶棍、逆子;做一回姐妹或情人,赐我片刻温馨,即便如秋光倏忽,残阳易逝。
这里,爱人、母亲、姐妹是一体,包含人类母性共有的柔情蜜意。而更绝望,也更强烈的对“母爱”的渴求,写在献给女仆的诗中:
您曾嫉妒的那心胸博大的女仆,如今已长眠于草坪下的泥土,我们自然要去供奉鲜花。死者,可怜的死者,悲苦无涯……
望着她空洞的眼睑珠泪滚滚,我该如何回应如此虔诚的灵魂?
在此,漂泊无依的游子心,将自己对母爱的渴求,寄托于对已故的保姆玛丽埃特(Mar⁃iette)的深切思念中,甚至将她视为第二位母亲(une seconde mère);而随着她的离世,“长眠于草坪下的泥土”,诗人将自己心中的母亲,也一同安葬掩埋。这首诗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经典评论:“这位被认为不合人情、带有无聊的贵族气的诗人,实际上是一位最温柔亲切、最有人情味、最具平民性的诗人。”
而有关波德莱尔的平民精神,译者以为,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地好好书写并深入研究探寻。可惜篇幅所限,这里只能一带而过。请看《致红发女乞丐》《致一位马拉巴莱少女》《西西娜》,还有《途中的波西米亚人》……在这些诗歌中,不知为何,译者处处看见作者的影子,尤其写到“红发女乞丐”为了生存,出门乞讨,“在十字街头,讨些残羹冷炙”——“你低眉偷看那值/二十九苏的宝石,/可是,对不起,/这我也不能送你”——
这里“不能送你”“那值/二十九苏的宝石”的真正原因,显然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买不起! 这位所谓“贵族气”的诗人,就这样偷偷炫耀自己的贫寒,一如“诗人”在开篇的《祝福》中就勇敢宣称:“我知道真正的高贵源自苦难”(Je sais que la douleur est la no⁃blesse unique)。
再看《致一位马拉巴莱少女》,作者在这位在异国他乡做女仆的印度裔少女身上,寄予了怎样的敬仰与深情:
在这热带的蓝色国度,上帝将你造就,你的任务就是给主人点烟斗,将清水和馨香灌入瓶中,在床边驱赶飞来飞去的蚊虫,而当晨风让梧桐树漫语轻歌,你就去集市上买香蕉和菠萝。一整天,想去哪里,你都赤着脚,轻轻哼着不为人知的古老曲调;当傍晚披着猩红色的斗篷降临大地,你就舒展身体,轻轻倚靠着凉席,任梦境飘渺,蜂鸟成群,一如你温婉、绚丽,繁花似锦。
原来“对于沉思的艺术家”,温柔于斯,高贵于斯,魂牵梦系的美人、美神也正在这里——一位在世俗眼里,给主人点烟斗、赶蚊子、赤脚出门,买香蕉、菠萝的女仆身上。——回头一想,那些谴责波德莱尔不道德的道德卫士们,他们满脑子的高官厚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提起来令人作呕。
而对于真正的革命女性,“温柔女战士,/一颗杀手心,一样充满仁慈……”波德莱尔又寄予了怎样的仰慕之情! ——原来“这位被认为不合人情、带有无聊的贵族气的诗”,心中敬仰的,分明是那些乞丐、“杀手”,行将就木的耄耋老人(《七长老》《小老妖婆》),还有那世代流浪漂泊、贫困无依的《途中的波西米亚人》……可见在波德莱尔心中,什么人最值得崇敬、仰望,什么人可鄙可恶。而与此相反,无论在现实或文学作品中,我们常看见一些貌似最具平民精神的于连式的人物,他们怀揣着拿破仑的肖像,时时处处不忘标榜自己的“平民精神”,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为跻身于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哪怕头破血流。呵呵,这样的人,满眼皆是。
对于“诗人”而言,母爱的缺失,造成大地冰冷、黑暗,海洋苦涩;而“冰冷”(froid)、黑暗(ténèbre)与“苦涩”(amer),不仅是《恶之花》中频频出现的形容词,也是诗人的心灵底色。而在《恶之花》中的“恶之花”部分——《毁灭》《遇害的女人》《莱斯波斯》《下地狱的女人》《血泉》《寓意》《贝娅特丽斯》《吸血鬼变形》《库忒拉岛之行》《爱神与颅骨》,皆为这“两姐妹”的化身;而所有《反抗》部分,包括“彼得”“该隐”“撒旦”都是“兄弟”…… 而从如此“父母”,这样的“姐妹弟兄”的“镜子”里,我们不难看见“诗人的灵魂”——正如法国作家奥莱维利(Barbey d’Aurevilly,1808-1889)在评论《恶之花》时断言:“但丁走进地狱,波德莱尔走出地狱……《恶之花》出版后,这位使罪恶绽放鲜花的诗人只有两条路:要么朝自己脑袋开一枪,要么成为一名基督徒。”我想,这是我所看见的,对“诗人”的波德莱尔最精确的描述。
然而最终,“诗人”既没有“朝自己脑袋开一枪”,也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也不一定),而他之所以选择活下去(尽管曾经自杀过一次),我想,应该是靠“朋友”——“朋友”?“这个词儿,我至今一无所知”“陌生人”说。而“一无所知”,并不意味放弃“寻找知音”。
“朋友”只有在孤独中找寻。如波德莱尔曾经对朋友说:“我也写诗! 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将它们示人的地步! 诗歌是一朵罕见的花,必须在高傲、孤独的宗教中,自己去呼吸它们的芬芳,去采撷它。大自然创造出诗人,不是为了让他们去做演员!”而放眼望去,现如今,成堆的诗人“抱团取暖”,相互吹捧,结果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也分不清这伙人究竟是诗人还是演员。我想,真正诗人在现实中往往孤立无援,却在精神上寻找隔世知音。如南宋诗人文天祥感叹:“读史识其他,抚卷为凄凉。我生何不辰,异世忽相望。”而这种异世知音,如“灯塔”相互照亮。试看《灯塔》中的艺术家:鲁本斯、雷欧纳多·达芬奇、伦勃朗、米开朗琪罗、毕劼、瓦托、戈雅、德拉克洛瓦……,或如“镜子幽深”,相互映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恶之花》诸多重要意象(诸如“地狱”“坟墓”“尸体”“蛆虫”“撒旦”)中,“镜子”占有独特位置,如“海是你的镜子”(《人与海》);“这可怜而悲伤的镜子,曾粼粼闪烁……”(《天鹅》);“你为何那么不知羞耻,/不站到镜前,看看自己红颜已逝……”(《你要将整个世界带进密室》);“我就是那面不详的镜子……”(《自我刽子手》);“一位忠诚、喜乐的天使,/她将使死火复燃,镜子复明(《恋人之死》)”;“藻井华丽,/明镜深深……”(《遨游》);“只因我拥有能使万物生辉的明镜……”(《美神》);“黑暗与光明对垒,/惟有一颗心,成为明镜”(《无可救药》)。而“镜子”何为? ——认识自我。
还有许多隐藏的“镜子”,如“一具腐尸”、一位“犹太丑女”……在此不一一列举。而更为幽深的“镜子”,或如荣格所说的“集体意识”及自我的“神话原型”——兰波认为:“诗人是盗火者。”他找到普罗米修斯;而同样沉浸于古希腊神话,“喜欢裸体时代的回忆”的波德莱尔似乎更多一份悲凉,少一份英雄情怀,他找到“伊卡洛斯”,就是那位希腊神话中挥动着蜡翅膀,与父亲一同逃出牢笼,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
我徒劳地探寻着空间宇宙中心与终极;经不住未知火眼的凝视,
感觉我的翅膀已焚毁折断;
我无从享有这崇高的荣誉:
对于美的挚爱已将我点燃,
将我的名字投入深渊,
那里将是我永恒的墓地。
“诗人”最终折断翅膀,坠入深渊,却没有伊卡洛斯那样的幸运: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深渊。这便是《伊卡洛斯的哀叹》。原来“诗人”并不奢望名垂青史,却在绝望之中,寻求更深的绝望,并由此产生对“死亡”与“荒淫”这“两姐妹”的深深依恋,并不知不觉,陷入难以自拔的“醉生梦死”……这种可怕的状态,我想,才是真正“波德莱尔式的”:以生命为代价,认识自我,点燃自我,用“火焰书写的黑色传奇”。
眼看新译《恶之花》即将完成,心里诚惶诚恐,一些诗中的画面常常浮上心头:残忍的“诗人”手持“撒旦恩赐的火把”逆流而上:当世人正苦苦寻求真善美一体,他却从拆毁了传统的美学大厦,从“恶”中发掘真美;当世人纷纷逃离都市,“诗人”却逆流而上,在都市“薄暮”徘徊……
最后,作为译者,请允许我在此略谈翻译《恶之花》的点滴体会:首先,译者认为,翻译即是给母语注入新鲜血液,其中包含新的语言、新的诗意、新的观念。因此,切忌用母语中的陈词滥调、旧形式与旧观念来“套”新诗,尤其是《恶之花》,它本身自带至今依然新鲜、强大的力量,拒绝一切旧的枷锁与精神桎梏。比如《吸血鬼变形》中,这女人“如炭火上的蛇”,“开启草莓红唇”,原文是de sa bouche de fraise,意思明确,译成“樱桃小口”或欠妥当。明明是“草莓红唇”,为何要套用陈旧的俗语和美学观念呢?
再者,我相信所有《恶之花》的译者,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即《恶之花》通篇如唐诗宋词一般浑然天成,从头至尾,对称、押韵,如《太阳》一诗中所言:
Je vais m’exercer seul à ma fan-tasque escrime,
Flairant dans tous les coins les hasards de la rime.
我将独自习练神奇的剑术,从各个角落寻求偶然的韵律字符。
波德莱尔的朋友勒瓦瓦瑟尔也曾在诗中提及:“我们狂热地喜欢押韵,波德莱尔/喜欢用怪韵,而不爱用顺韵”,而透过《恶之花》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为了节奏、韵律,波德莱尔付出了近乎疯狂的努力。
作为译者,我从心底抱定这样的信念:法语能实现的,汉语必能实现;波德莱尔能做到的,译者应尽力尝试。反之,不押韵还是波德莱尔么? 不照原诗原韵,终究是一种遗憾。而所有这些,只针对自己而言,无关他人,谨以此译文,表达对诗人波德莱尔,以及未来读者的深深敬意——
读者,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单数,仅此一人,我也许认识,但更有可能是个“陌生人”,他(或她)独具慧眼,精通法语、汉语,字里行间,触及诗歌与人生真谛。在这位读者面前,我这个老大不小的学生,惟有毕恭毕敬呈献自己不成熟、不完美的作业。而在此,顺便“剧透”一下自己在长期的翻译中找到的一种“偷懒”的方法:让读者参与翻译。因为在原诗中,有很多“关键词”一语双关,或一词多义,涉及神话典故、历史传奇。这种时候,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附上“原文”,添加注释,让聪慧的读者一目了然,心领神会。
最后,作为新译者,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恶之花》已经有多个译本,为什么还要翻译? 在此,请允许我顾左右而言他:妻子正在家里欣赏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我收拾书包出门,说:“我去演奏我的波德莱尔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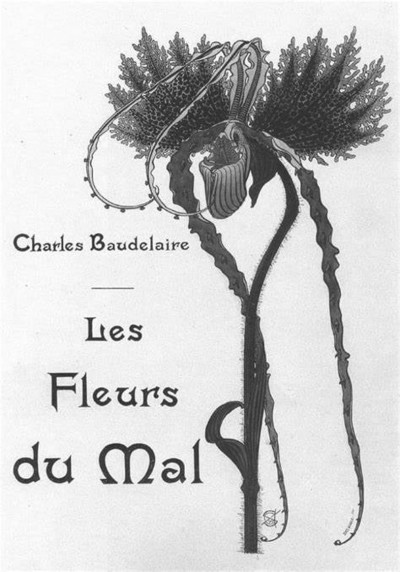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