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医学,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多是冰冷高效的医院、迭代频繁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令人眼花缭乱的药片胶囊……它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如此平常,以致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医学自创始之初便是这等枯燥、无情、理性、机械、“唯科学论”的模样,既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又少有对人性的尊重。
但若置身医学史发展的全程,我们则会惊讶地发现,人类医学远非仅仅聚焦在药物史、诊疗史这等单调严肃的领域,在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作为一门容括自然科学、天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集成而存在发展。如中国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诸多医学著作、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以及西方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托勒密的星占医疗学以及盖伦医学思想等均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按照大的阶段划分,世界医学的发展在17世纪前均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巫相通)、元素说以及体系化传统医学时期。而如今我们所熟识的现代医学,实际上是从17世纪科学革命开始才渐具雏形。在当时“机械论”大行其道的主流氛围下,医学也未能逃脱这场革命,而逐步发展成以“还原论”生物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医学体系。虽然之后伴随诊疗设备和技术的接续革新以及医学教育的扩大与规范化,现代医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说,医学还从未攻克过如此多的疾病、挽救过如此多的生命,但亦因其自身之傲慢与偏见引发出了更多问题:对患者心灵需求的忽视、对身心健康的错误定义、医者人文情怀的缺失,以及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漠视,等等。正如英国著名医学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所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下,医学界开始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之前居主导的“还原论”生物模式也开始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医学人文学(Medi⁃cal Humanities)这一学科。该学科迄今未有明确定义,但规定了研究范围是除医学技术领域之外的所有相关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学科,是多维度、多层面探讨当代社会文化中健康与疾病、生殖与死亡、病痛与治疗等的学科群。因此,其研究者的构成既有医学专业人员,又包括诸多社会科学学者,从而使这一交叉学科兼具科学之理性与人文之关怀。
从我国来讲,医学人文及相关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基本都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都经历了从译介国外经典著作到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能够适应和指导中国现实社会的阶段。《医学与文明》(第一辑)便是以医学相关事物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刊物,由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主办,宗旨为“着眼社会发展,注重人文关怀,打通学科壁垒,加强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并且坚持“求真务实、创新发展、中国情怀和世界视野”。
该书涵盖广阔,体现在地域分布广、时间跨度大、视角新颖以及写作形式的多样上。地域上,既有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如李新宽《近代早期英国消费与健康关系的多重矛盾》、谷操和闵凡祥《中世纪西欧对麻风病的双重态度》等,又有以我国为对象者如马得汶《“三原并两重”:关于藏医当前发展的若干思考》,以及中西比较研究如张茜《真实与虚化:论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中英报道之歧异》。时间跨度方面,上至托勒密(约90年—168年)的《星占四书》,又经过中世纪的西欧、18世纪的美国(张琪《1793年费城黄热病期间的种族歧视与非裔美国人群体身份的形成》)、19世纪的英国(王广坤《试论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的转型》),直至对当下疫情的探讨。研究视角上,既有医学社会史(郝树豪《亨利·西格里斯的医学社会史思想探析》)、医学人类学(李如东《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感悟——王建新教授访谈录》)、医学教育(聂文《近代早期英国的健康教育》)等常规领域,又有从经济学(马泽民《黑死病对中世纪英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法学(高建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具有所有权吗——评〈手的失窃案:肉体的法制史〉》)、医疗占星学(高阳译《星占四书·第一书》)等新颖视角切入者。
2019年,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宣告成立,并由韩启德院士担任首任系主任。如韩启德院士所说,科技(医学)与人文要相向而行,“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医学与文明》亦贯穿这样的态度,不论是社会学视角、人类学视角、历史学视角甚至传播学视角,均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而尤其可贵的是,《医学与文明》认识到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归根结底还是要为现实中的大健康事业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依据,而不能仅是纸上空谈。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超老龄化的前夕,经济结构也面临重大转型,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健康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医学与文明》(第一辑)中的一些讨论就颇具现实指导意义。一是医学教育。十九大着重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这势必需要更多的医学专业人员。尽管国家已推出不少鼓励政策,医护人员依然供不应求。本书中《试论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的转型》《近代早期英国的健康教育》,就为我们带来了英国医学教育、健康教育的他山之石。另外,《试论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的转型》还着重谈到了民营医院的兴起、技术变革带来的医院制度的变革,以及技术主义、商业主义与医院中新管理主义模式的形成等,对我国当下鼓励兴办民营医院的政策亦有参考价值。
二是民族医药的发展与我国边缘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前者如马得汶《“三原并两重”:关于藏医当前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青藏高原Y藏医院的医学人类学调查》以医学人类学的方法深入民族医院进行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一线医生和医院管理人员,并以此为基础跨学科地将文化、地理环境、民族和心理因素等纳入健康的考量范畴,真正地从现实入手来有效推动民族医学的发展。后者如《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感悟——王建新教授访谈录》是对著名民族及人类学学者王建新教授的访谈,对加强对边缘人群的医疗保障颇具启发意义。
本辑的“文献选译”收录了高阳翻译的托勒密《星占四书》以及刘娟翻译的米兰的兰弗朗克《放血入门书》,这着实令笔者有些意外。星占学当中的医学知识是国外医学史与科学史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但在中国,该领域却一直处在冷门边缘的地位。古代略显“迷信”的放血术亦处于这种境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选取颇具国际视野,不免感慨该刊编辑对于世界医学史研究状况的多方位掌握,以及在选录文章时的深思熟虑。
学科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个人命运,兴衰皆有其因缘,或者说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2020年开始的全球疫情令更多人停止对于无止尽之欲望与享乐的追求,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医学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医学史、医学人文思想的相关研究亦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主流舞台并发展壮大。《医学与文明》可谓应运而生,必将在今后大放光彩并启发更多研究者参与到这个探索生命真相、为众生身心健康而奉献的伟大事业中。如该刊主编李化成教授所说:“我们希望在这个稚嫩的平台上,看到富有时代气息、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我们更希望,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本刊文章传播的不仅仅是医学与文明相关的知识本身,更是智慧与良善,以及面对疾病及更多困难时的勇气与希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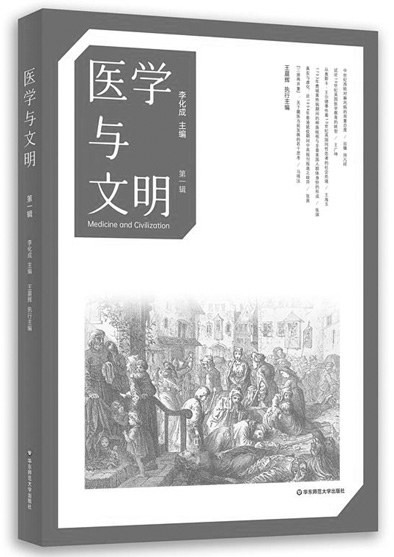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