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的标题是徐俊《翠微却顾集》的副题,我选不出一个比这个更合适的题目来作文,所以就“借用”(网络语“盗用”)一下。按照我和徐俊兄的交情,他应当不会怪我,下面行文也不用敬称,我想也不会得罪他的。
我知道徐俊要编这样一本书,是2019年4月末,当时孟彦弘、朱玉麒张罗着给凤凰出版社编一套随笔类的小丛书,名为“凤凰枝文丛”,约稿名单中有徐俊,但他考虑之后谢绝了,因为文章主要都是写中华书局的。现在翻阅这本2021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翠微却顾集》,的确如此,里面几乎百分之九十八的内容是和中华书局有关的,有些文章上来就是“局里”,放到其他出版社,的确对不上号。
这本以中华书局为叙事中心的书,看似随笔,其实作者是想说说中华书局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联系。翻开还透着墨香的新书,一连串的名字映入眼帘:顾颉刚、汪篯、邓广铭、周一良、陈寅恪、何兹全、田余庆、启功、张政烺、郑天挺、蔡美彪、向达、周勋初、项楚、赵昌平、陈尚君等等,还有中华书局的王仲闻、宋云彬、赵守俨、程毅中、傅璇琮等,仅仅看这个名单,就知道这本书与中国现代文史学术的关系了。但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学术史,而是选取一个个“有着典型意义的事件”,阐发其中的学术史价值。我读罢此书,想谈谈感触最深的三个方面。
一编辑与学者
1954年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出版方向确定为以古籍整理和文史哲著作为主,成立不久的古籍出版社也并入中华。在金灿然等书局领导的主导下,很快与文史哲各方面的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开展各项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
徐俊书中相当一些篇幅,都是在讲述中华书局的编辑与学者之间交往的佳话,特别表彰编辑对于学者在完成其名山事业时的种种帮助。比如开篇讲不应被忘却的王仲闻,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他在1959年接手唐圭璋《全宋词》时,受托加以修订,曾写下约千条修订加工记录,近十万言,以致原编者建议署名改作“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但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名字长期没有在出版物上出现。
周振甫帮钱锺书责编其学术巨著《管锥编》,是又一个学林传颂的佳话。周振甫是1948年钱锺书在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时的责任编辑,所以在《管锥编》完成后,钱先生首先给周看。周随后在1977年10月24日写了《建议接受出版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次日即决定接受出版。周先生在责编钱氏这部鸿篇巨制时,先后写有详细的审读报告,有数万言之多。钱氏逐条做了批注,有的接受,有的修改,有的不取,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管锥编》的样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谈艺录》补订本时,周振甫再次责编,又写了十数条意见,钱氏也逐条做了批注。徐俊还特别从中华保存的档案中,全文抄出这两部书的审读报告和具体讨论文字及钱氏批注,让读者全面了解周振甫实为《管锥编》《谈艺录》两大名著的第一功臣,钱氏在《管锥编》序中称赞其“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诚哉斯言! 周振甫先生晚年又花了很大气力责编了钱锺书之父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三册,这固然有周原是钱基博在无锡国专的学生,但也有与钱锺书的友情在内。编辑与学者之间的友谊,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徐俊在回忆周振甫的文章最后说道:“令我深有所感的是,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126页)
为了帮助学者完成学术大业,中华书局的领导还数次利用“上方宝剑”,调人入京,来协助工作。徐俊书中利用中华所存档案,记录了为帮助顾颉刚完成《尚书》整理、研究、今译等工作,从1959年夏开始运作调动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处工作的刘起釪来中华书局。此事经过三年多的周折,最后在1962年11月终于成功。这个结果,不仅解了顾颉刚的燃眉之急,而且也成就了刘起釪的《尚书》研究事业。
在与学术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华书局充分尊重学者的意见。比如书中提到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点校问题,虽然有争议,但中华点校本最后尊重邓广铭、周一良的意见而改订。又如书中详细介绍了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稿本的整理及拟出版的“前世今生”。此书1945年即由商务印书馆校勘补订,准备排印,但因事未果。1954年科学出版社成立,又考虑出版,请王先谦门人瞿蜕园整理并标点。瞿氏戴罪立功心切,全力以赴,写了数千条版本校对浮签和近十万字的校勘记。科学出版社送陈垣审订,以为原书值得一印,但要尊重王氏原文,不轻易增删。科学出版社写好了万把字的《刊行说明》,就等付印。1958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制定,《新旧唐书合注》纳入“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转入中华书局处理。中华随即约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汪篯和科学院历史所贺昌群三位外审。周一良对《刊行说明》和瞿氏校记都有不同看法;而汪篯则写了近万字的否定意见。此外,唐长孺对全书出版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中华书局内部也让赵守俨做了审读,最终决定尊重专家意见,把稿子退回科学社。虽然此书题目与当时中华急于求成的“二十四史”集注本相合,而且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准备出版,但专家的意见高于一切,所以1959年10月即叫停。笔者过去听闻王氏此书在科图尘封,在《唐研究》第3卷上发表过谢保成先生的介绍,今读徐俊此文,才真正了解到此书经过了如此多的行家之手。
中华的编辑与学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启功先生在1971年借调到中华,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直到1980年代初返回北师大。他常说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个家”,就是因为中华人待他像家人一样,而他也为中华题写了大量书签,常常横竖简繁多写几条以备用。作为书法家,他还给许多中华的编辑写了“墨宝”,几乎是有求必应。
中华书局一贯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学者完成拟出版的专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约请三十余位著名学者出版个人学术论文集,表示“只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不拘文体,不拘性质,不论考据、义理、札记,均可收入。对收入的文章,作者如愿意修改,可以;不作修改,也可以”(49页)。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是非常开放和宽容的了。徐俊书中完整揭示了中华书局为出版陈寅恪先生论文集而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对于上面的沟通,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要知道这个议题开始时,陈先生的《论再生缘》在香港被人翻印,引起一些麻烦(北大历史系资料室有此印本,我看过文中所说的序)。虽然由于中间人没有传递消息,最后此事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中华书局在接到陈先生确定把文集交给上海方面出版后,立刻给相关方面回函,并整理好完整的往来书信档案,都可见中华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对于学者的认真负责。书中收录了中华书局为出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时的往来通信,可以看到中华安排人按照周先生的提示,找人去上海帮忙抄录作者的旧稿,由中华支付费用,“出版社把对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完全当作分内之事”(51页)。
可以说,在“文革”开始前,中华书局为一批作者赶出了论集,既坚实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地位,也为中国学术垒筑了基石。试想,如果没有这些论著的出版,到“文革”结束后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的学术会与日本、甚至港台的学术差距要更加远。
“文革”以后,中华书局秉承五十年代以来的学风,仍然为学者编辑出版学术专著和论集,比如张政烺的各种古文字、易学专著,以及《张政烺文集》;郑天挺的文集、日记、讲义,以及后人编的郑先生纪念文集、学行录;项楚《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到《项楚学术文集》八种11册;如此等等(其实还有许多没有在本书中谈到的学人论著)。另一方面,中华书局对于选题其实十分谨慎,对于书稿把关严格,编校仔细,所以出版的著作质量上乘。因此,学人也逐渐以在中华出书为荣,若不在中华出书,就好像在学术圈子里“未入流”的感觉。
正是因为中华书局对于学者如此这般的厚爱与帮助,所以当中华约请学者来做事时,大家也是有求必应,责无旁贷。上述学者帮助中华审稿的事例,即可见一斑,而最大规模的学术界与中华书局的合作,要属“二十四史”的点校和修订工作了。
二“二十四史”点校本和修订本
自2005年以来,徐俊一直大力推动“二十四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可谓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本书中大概一半篇幅都和“二十四史”的点校本和修订本有关,通过中华团队的档案整理工作,徐俊也是首次把“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成书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同时也用访谈形式,把“二十四史”修订本的工作过程和陆续出版的成果,做了透彻的说明。
1958年成立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在其主导下,接续《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开始了“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的工作,中华也全力投入其中。据徐俊介绍,当时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前四史”的主要点校是中华的编辑和外聘编辑完成的。《史记》及三家注是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基础上加工、复校而成,赶在1959年9月国庆节前出版;《三国志》由陈乃乾完成,同年12月出版;《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而成;《后汉书》由宋云彬点校完成;后两部书迟到1965年“文革”前夕才出版。
为了推进“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1963年中华书局报请中央宣传部,调外地学者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罗继祖、王永兴等来京,入住中华翠微路大院,集中工作到1966年,取得较大成绩,特别是“南王北唐”主持的南北朝各史的点勘工作。1967年曾短暂恢复校史,但成效不大。1971-1978年之间,又抽调一批学者到中华书局王府井办公地点,集中校勘,周总理指示由顾颉刚总其成,其中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改由上海方面负责,京沪两地,都取得重大进步,“二十四史”各部点校本也陆续出版。
对于“二十四史”点校本阶段的工作,本书有多篇文章涉及。如《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活灵活现地把宋云彬的贡献描绘出来,让我们看到这位“右派”分子为了立功,甚至冒进的可歌可泣故事。文章更多地讲述了从点校本到修订本是如何过渡的,包括对郑天挺、何兹全、田余庆、蔡美彪、刘浦江的回忆文章和修订本出版后的访谈。
不言而喻,“二十四史”点校本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徐俊说:《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不但奠定了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学,也引领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方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179页),“‘二十四史’点校的成绩和贡献,并不限于古籍整理,而是对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二十四史’点校本惠及每一位历史学家,意义重大”(175页)。我在古籍整理与历史学研究中度过了四十年的光阴,对他的话深表认同。
不过,“二十四史”毕竟主要产生在“大跃进”和“文革”年代,整理条件非常艰苦,因此也有不少问题。按照徐俊的总结,主要是整理标准和体例不统一,底本选择不一,所用版本有限,检索途径贫乏,以及印刷技术的限制。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下,2005年徐俊等中华书局领导开始推动“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为此,徐俊带领团队,清理了有关“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作档案,走访了在世的参加点校的成员或其弟子,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总则、制度和流程,要“以程序保证质量”。在尊重原整理者、原参与单位、原点校校勘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修订本的负责人及其团队,“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457页)。到目前为止,修订本《史记》《魏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等11种已经出版,成绩可观。过去我们对于“二十四史”点校本有一种不假思索的认可,引用时从来不考虑其得失,不像我们用《全唐文》中的篇什,总是要去看看《文苑英华》、个人文集等,所以在“二十四史”修订本开始阶段,一些人是有所疑虑的,觉得不会超过六七十年代那批整理者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徐俊给出的各史修订本的统计数字,知道增补多少,修订多少,维持原貌多少,可知这次修订本虽然样貌与点校本保持一致,但内涵的确是旧貌换新颜了。
关于“二十四史”修订的更高一层意义,徐俊说道:“一部重要史书的整理,其意义不只在其书本身,还在于优势学科的建设和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二十四史’修订获得学术界积极响应的原因。”(134-135页)我的同事刘浦江教授主持的《辽史》修订,就以后续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参加整理的年轻人后来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如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苗润博《〈辽史〉探源》、邱靖嘉《〈金史〉纂修考》、陈晓伟点校《金史详校》等,可见其影响深远。
三 中华书局与学者型编辑
徐俊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他的书名虽然是取自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但暗含着对中华书局(曾在翠微路)的眷顾。而书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中华人要成为一位学者型的编辑。
记得2000年后中华书局在海淀一家书店召集的某次座谈会上,有位学人发言,对中华的编辑像做学问一样责编书颇有微词,说编辑对作者的书吹毛求疵,非挑出一堆错来不可。我当时听了,不知若何。此时正是中华很多骨干编辑因为中华领导的更换,方向改变而纷纷离去的时候,徐俊也在这年年底离开中华去了社科院文学所。现在读了徐俊的书,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学者型编辑”的责志。
书中说到,金灿然执掌中华书局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华书局学术品格和独特个性形成的时期。金灿然当时罗致了一批其他单位不要的学者来当编辑,包括前面提到的王仲闻、宋云彬,还有孙人和、马宗霍、杨伯峻、马非百、傅振伦等人。今日却顾,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而是著述名家,他们做编辑,自然是以一个学者的素养来做工作的,这恐怕就是“学者型编辑”生成的缘由。
在追忆周振甫的文章中,徐俊特别强调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编辑的代表”,他还同时提到杨伯峻、王文锦、赵守俨等,他们既默默无闻地做着编辑工作,又都有专精绝学。从1983年开始,徐俊加入中华书局编辑队伍,“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动力,仍宛然在身。前辈的指引,同事的砥砺,自己的努力,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获益”(120页)。他说进入中华的年轻人,“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339页)。他以其很少流露的文学笔法,描写这些前辈学人:“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而这种职业品格,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文化企业来说,无论她走多远,都是不可或缺的。”(126页)
徐俊还以傅璇琮为例,说到“编辑工作的清苦,编辑而具有学术追求,编辑加学者,更加劳力劳心。但是,他们的学术追求,他们的编辑实绩,成就了中华的事业,也成就了他们自身”(151页)。他特别强调傅先生的编辑职业对他学术的影响,行文中随意说到,傅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许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子,因为他是《万历十五年》的责编。过去我读《唐代科举与文学》,只觉得很好看,真过瘾,没想有些笔法或许真的有所借鉴。
由于有这样一批学者型编辑,有这样一个学术传统,确定了中华的性格。对此,徐俊总结道:“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一直坚持对古籍文献的深度整理,坚持为学术界提供古籍基本书的出版方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读者所用的理念。”(130页)在回忆赵昌平文中,表扬昌平先生“既不从声流俗,又不固步自封,在今天的出版界是非常难得的品格”(171页)。这些话语,显然是徐俊对中华书局的学术定位,对年轻编辑的期望。
这本书中涉及到徐俊本人的篇幅并不多,但也可以看出他在编辑中如何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学者型编辑。1987年接受编辑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后与《全唐诗外编》修订本合为《全唐诗补编》),他也像前辈王仲闻、周振甫那样,逐句核对每首诗的存佚、真伪,先后增删达五百多首,并与尚君先生反复磋商,共同完成了一部上乘的《全唐诗补编》。与此同时,徐俊也在开始自己着手系统校录敦煌写本中的诗歌,也就是他所说的找机会让自己去打一口深井,来触类旁通地去熟悉各种文献。2000年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出版,不仅提供给学界精校的全部敦煌写本诗歌,而且还在五万字的前言中,谈到写本和刻本的区别,以及把诗歌放到原来流传的状态中去考察等观点,可以说开创了敦煌写本文献整理的新时代。这本《辑考》和他编辑的《补编》,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华书局学者型编辑的全貌。
笔者与徐俊年龄相仿,旨趣相投,一见成交,日久弥坚。他书中提到我对他的《辑考》有所帮助,而他在已经担任繁重领导工作的日子里,还抽出时间给我的序跋集——《学理与学谊》当责任编辑。书出版后,第一时间撰写书评,揭示“序跋的意义”,对我所说的“学理”和“学谊”做了准确的概括和提升。正是徐俊身上有着学者的素质和编辑的责任,所以能够和我这样不善交友的人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学者型编辑的一个方面。
徐俊2003年回到中华进入领导班子,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一把手),几乎放弃学术研究,全心工作。我们在谈工作时称他为“徐总”。作为职业出版人,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本书出版于他退休的前夜,这是对自己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晚辈的交待,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上圆满的句号。
从此以后,希望徐俊兄可以开启新的学术人生,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回到学术自身,回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所从事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工作”(157页)。我们相信,作为学者一面的他,一定会在学术领域开辟出一片“苍苍横翠微”的新天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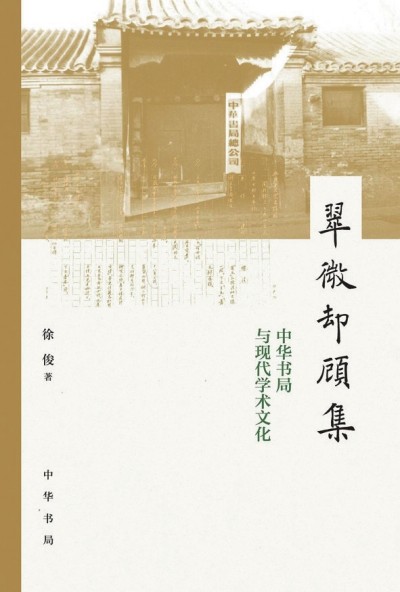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