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之谜”说起
吾师江晓原尝言,这些年求解“李约瑟难题”者多如过江之鲫,看得人们严重审美疲劳。本书初看似未脱此窠臼,安上科学革命名头,或有新意存焉? 序中开门见山,要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原版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西方,为何近代科学没在中国出现),在科学史家看来,即便不全是也很接近于伪问题。前提就成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领先”,也不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改问“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西方”有意义得多,起点还高于李约瑟。
作者又找到了好的着力点:近代欧洲特有的“国家竞争体系下的激烈军备竞赛”使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本书亮点颇多,值得关注。
不过封底推荐者无一是史学家或科学史家,作者自身是医科和经济学的“科班出身”,写历史书殆近于“越界狩猎”。本书不乏真知灼见,但那些有趣有益的内容如果被读者忽略过去,那就近于买椟还珠了。所以笔者决定先谈“椟”再捧出“珠”。
本书似有如下默认预设:1、科学是技术的基础,要解释近现代西方的技术优势就得解释科学革命。2、科学是公共产品,只有国家扶持、创造出科学的民族氛围,形成全民风气和大众运动,科学的“市场”才会出现,民间才会开始“自发”产生科学家(p.146;这太经济学了)。
该两预设可能都有问题。关于科学和技术相互平行可以独立发展,可参阅后文推荐书目;而“国家扶持……最后民间出科学家”公式,则很难从古典希腊到牛顿时代的历史得到支持。
其次是作者用生产力佐证中国古代科技,如以古希腊服装生产力落后于中国为例证。但古代民族各有所长,没哪国在金字塔、方尖碑和木乃伊方面生产力超过古埃及。拿中国贵人绫罗绸缎去比古希腊衣着,这样的生产力比较,缺乏说服力。
最后,更早占有古希腊遗产的东罗马、伊斯兰社会未发生科学革命,不证明这些遗产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只证明它们不是充分条件。其实本书解释科学革命的目标应改换(甚至不必出现在书名中),方能让那些有价值的内容更加突显出来。
揭示“去道德化”与西方崛起的关联
用战争解释科学革命可不可行? 这且待下文讨论。但首先,本书用战争解释西方崛起,是可行的。其次,放弃解释科学革命的目标,其实损失不大。本书仅序、导论和第六章涉及科学革命,叙事重点原就是“中世纪/近代欧洲军事史及与西方技术产业崛起的关联”;专列一章讲文艺复兴“道德沦丧”及国家赞助,详述梅毒、意大利城邦战争,尽管忽视了同时期远为猛烈、影响科学史直接得多的黑死病与百年战争,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但引入“道德”维度,很有新意。如果不执着于解释科学革命,本书更多亮点渐次显现。最值得一提的洞见就是“去道德化”与西方崛起的关联。
西方道德之路有破有立,书中两方面皆有,但破得更明显。第二、第四两章,揭示得较为深刻得当:“去道德化”对象主要是外人:异教徒与“蛮族土著”。基督教欧洲源于古典地中海世界,对“非我族类”的“零道德”态度在希腊罗马时期已现端倪。文艺复兴以来,进而把原本基督教框架下不道德的事,转变为新型国家框架下“道德”的事,这是盛唐崩溃后的中国一直不愿意做的。盛唐政治本身虽谈不上多道德,但完全舍弃儒家道德另起炉灶搞一套全新的道德体系,显然与中国大一统传统观念不兼容。因而古代中国的公德摇摆于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而欧洲跳出了这个循环。
私德方面却是欧洲大幅摇摆不定:古代中国理学最盛时也不像维多利亚时代,假道学笼罩一切;而16~17世纪之交晚明物欲横流的程度或许还不及早先意大利,大致仍在“张弛有度”范围内(参阅《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公德“立”的方面,与作者花大笔墨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密切相关。十字军的打砸抢烧与奸淫掳掠,其宗教背景为大航海时代“上帝、黄金、荣誉”三位一体的人生信念做了铺垫(p.181);进而又在民族国家时代化为“国家荣誉感与公民责任感”,招来两次世界大战之祸(p.490)。这“新公德”的实质与希腊罗马古典公德区别甚微,复古多于创新。
自抗战、特别是抗美援朝以来,现代中国贯彻新公德,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又如作者提到晚清军工受传统道德束缚未能加入全球军火市场,致使经营困难(p.461~462),这种事也再不会发生了。对此如何评价,却是难于下笔之处。
能不能用战争解释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论题是块硬骨头,主体是17世纪完成的天文学/物理学/数学革命。化学革命要追溯到希腊化以来的炼金术传统,发生更晚(将拉瓦锡的工作与牛顿理论建构联系,虽便于强调弹道与火药,但学理依据不足)。要啃它就得提到科恩经典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含2012年中译本补遗),它整理了70多年来围绕科学革命实质与原因展开的约60种阐释。
譬如造纸术印刷术带来“低成本信息传播”是否构成科学革命的前提? 该书“科学从抄写走向印刷”颇有启发性。科学革命时期学术交流主要靠书信;从公元前后罗马的书店出版业、俄克喜林库斯“垃圾堆”莎草纸文献出土看,廉价纸和印刷机也作用有限。须另辟蹊径,如古老的书展:“在科隆、莱比锡,尤其是在法兰克福……1564~1649年交易的图书达到7.5万种,总计约6千万至1亿册……学者们通过浏览法兰克福书展的书目跟上最新的思想潮流。”(《剑桥科学史》卷三)如此巨量“知识经济”浪潮中的成千万上亿册书,一方面便利了传播科学革命,另一方面碰巧有几条奇思怪想在遥远的未来有益战争和工业,都是可能的。
贝尔纳曾受赫森命题启发,也是读科恩会有的收获:前人试过给伽利略等人的研究安实用背景,军事(尤其火器和弹道)还正是赫森命题三大领域之一。
但总的来说,所有“外因论”解释都有隔靴搔痒之憾,战争决定论亦然。用现代方法演绎伽利略或牛顿研究的极小部分并配解说,不能证明他们真出于那个外因而研究;后者也没解决“提出的”问题。基于物理学的弹道学、基于天文学的海上经度测定,科学革命两大空头支票,革命完成后多年仍未兑现。在17世纪的炮兵看来,科学家的弹道纯属扯淡;18世纪解决经度测定也未使用早先的设想。
外因论在理工科毕业生(与“工业党”有交集)中颇时髦。《白银资本》《大分流》将西方崛起归因于美洲白银或煤炭分布,却回避科学革命论题;因为一涉及该论题,必动摇读者信心:原来各文明都有区别于其它文明,得自早期地理地缘环境的文化传统或曰基因;相同外部条件不能保证什么。
科学恰是这样的传统或曰基因之一。若美洲、中、印或非洲某小国集群也有那种战争环境却没有希腊科学和哲学传统,或缺少欧洲中世纪以来遍布各国的大学体制,明清鼎革为证:那结局顶多是又一次秦汉或唐、元式大一统,而非科学革命。
严肃讨论科学革命的规定动作有:科学革命实际进程;革命对象;中世纪以来的大学(科学革命人才多出于此);天文学(核心科学与革命主战场);希腊的数学与数理科学:几何、算术(数论)、天文、和声——合称四艺,光学、静力学、数学地理学,古人皆视之广义数学(下文提到数学皆取广义)。
古代科学整体复兴、中世纪大学及课程预先存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大学盛行及与神学、数学的冲突与张力,都是科学革命基本条件。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及宗教改革/反改革以来竞相开办大量新学校,使数学无须证明自己有用、真能解决弹道问题——那不过是个别学者可有可无的自抬身价。他们背靠的是大学。论有用性,对弹道的有用性也不及对占星术或神学重要——后两者背后有丰厚职业报酬,占星术是行医必需。
在大学教师看来,几何学促进哲学,还有助理解神学真理;算术(数论)对天文表很重要,保证天球和谐运动的可公度性(排除无理数才能保证精确重复);天文学能预言未来,是理解宇宙的关键……所有机械技艺(建筑、军事、冶金、农学)都未进入中世纪大学,文艺复兴也只扩充了历史、诗歌——大学,至少艺学院,根本就反对实用性。
教师有创新知识并讲授的自由,但不这样做可能更好——两者同等关键。作为欧洲意识形态一部分,科学在大学里总被认为有用。古代科学(尤其四艺)的角色更像四书五经。赵宋以降儒家经典千年未兑现三代之治,科举照考不误——能提供官场话语、文书能力足矣。欧洲大学与社会对科学有用性的要求不高于此。
扩展阅读和启发意义
想解释“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很可能实为有害的自选动作。科学、技术、产业的中心并不必然重合,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关联很薄(流体静力学/真空泵与大气压实验/早期真空蒸汽机)。其他地方如中国,以拿来主义态度借科学革命成果完成工业化完全可能,事实上也做到了。无人计划优先有益战争的欧洲科学:首要功用在占星术、炼金术与神学方面。罗伯特·S·韦斯特曼的长篇著作《哥白尼问题》也注意到战争与科学的关系,却是通过占星术这中介,战争只是占星术繁荣诸因之一。
这里为好奇科学革命的读者推荐:“科学史译丛”“科学源流译丛”《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剑桥科学史》第二、三、五卷,以及不久将要出版的《产业、技术与科学中心转移论纲》。
西方兴起或复兴时优势不止于自行其是,更在于既有局部小国林立(希腊、意大利、欧陆)加速知识演化,又有另一局部长期和平(亚历山大里亚、不列颠、北美)加工前者血与火换来的成果。看过《权力的游戏》的不难心领神会:假如那儿也发生科学革命,维斯特洛大陆的分裂战乱与“坐视诸王国灰飞烟灭、我自研究”的学城,显然缺一不可。
最后强调一下本书的启发意义: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对西方故事——不能只听西方自我美化的一面之词,双方的故事都需要重新讲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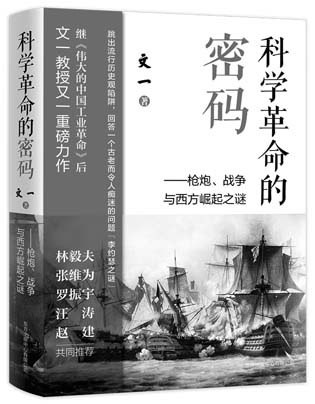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