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从具体的某一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窥见弥散其中的时代风貌;时代的力量在作者脑海中烙下钢印,作者又以文字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为时代发声。《时代与肖像》所收系列散文原是王尧发表于2020年《雨花》杂志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共计十二篇,记录了其从少年至青年时代故乡的人事风物的记忆碎片。
既然是“肖像”,则免不了对人的刻画。与过去着重于书写知识分子的散文随笔有所不同,这一次,王尧更多地着墨于成长过程中身边曾出现过的普通人。他们的形象与身份各异,或是亲人、老友,或是少年时代的玩伴、同学,或是曾经教授过自己知识的老师,或是自己做老师时带过课的学生,甚至少年时互生情愫的“初恋”,当然,更多的是记不清名字的匆匆过客。
写人通常离不开外貌描写。然而,虽说是“肖像”,王尧却很少去描绘一个人物的具体外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外在形象仅仅是通往内心世界的甬道,对于人物内在深度与广度的挖掘才是目的。因此他往往只用寥寥数语点出一两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奶奶的一丝不苟的发髻,李先生落光的门牙,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身上的雪花膏的香味,表姐时而白皙时而黑红的面颊……这些细节如同厚重的汉语词典首页的偏旁部首索引,指引读者跟随着王尧的提示,去翻阅、去探寻关于这些人物的更丰厚的内容。
关于外公的这一篇章,其“索引”是这样一句话——“我的腿迈不出去”,它也被用作该篇文字的标题。于是,阅读之初我们便可以推测到,疾病、生与死,是这篇文章将要探讨的话题。亲情是散文随笔中一个泛滥的主题,谈亲情必谈生死,谈生死必谈疾病,而后便陷入了无节制的情感泛滥,而王尧在文中对于情感的处理则恰恰相反,其本人在文章中的存在往往是隐秘的,情感无疑是节制的,哪怕是写到外公的疾病时。王尧更多是将人物放在了时代的背景之下,令读者去阅读这个被时代塑造了的人,去发现他的本真,文中的老人并非以“王尧的外公”这样的形象存在,他是独立的、鲜明的,是站立着的。在后来的篇章中,王尧又写到了奶奶,那个森严的富贵家族中走出来的“闻家二小姐”,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热爱俄罗斯文学的憨厚表姐等等。这些亲人大都故去了,而王尧写他们时,情感始终是节制的。这并非是他对故人们欠缺情感,相反,他是将文字铸成了一层反射着阳光的薄冰,怀着类似情感和相同经历的读者因内心的炙热融化冰层,就能感知到底下拳拳涌动着的暖流,甚至触摸到温润柔软的河床。这样隐秘而深沉的情感,就像他所描写的那场为缅怀外公而举办的简朴仪式:“我想起他因为生病戒烟,在他的坟头点了两支香烟。另一支给外婆,外婆怀我妈妈时有了烟瘾。我们撒了许多纸钱,坟头烟雾弥漫。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但我知道墓地之外是绿的麦苗,黄的菜花,像蝴蝶一样的蚕豆花。我看到外公,也看到外婆。外公说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没有一个字写悲伤,没有一个字写怀念,但悲伤与怀念都在其间,更多的,还有希望。《时代与肖像》十二篇,由写亲人开始,由近及远铺陈开去——最开始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血亲,尔后出现的是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和师友,再往后是青年时代的学生,还有或远或近的乡邻,关系不咸不淡甚至叫不上名字的“熟人”。他们被极简的肖像笔法刻录下外表,又在具有典型性的经历和事件中鲜活起来。
在创作《时代与肖像》系列散文的同时,王尧也在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非虚构”的《时代与肖像》同“虚构”的《民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们不难看出《民谣》中的那个少年带着作者本人的影子,《时代与肖像》中记叙的诸多人物也在《民谣》之中有着彼此的映照。这二者的关系,好比作者从真实记忆的母亲河中提取出水和土,在虚构的世界里铸成精美的瓷器。
凡过去的时间皆成为历史,时间无形无际,我们该如何去描述它?《时代与肖像》十二篇文章提供了一则方法,记忆是历史的承载者,从记忆中打捞出细枝末节,以还原过去的时代;人物是历史的锻造者,去观察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就能看见“历史的光影破碎地洒落在他们身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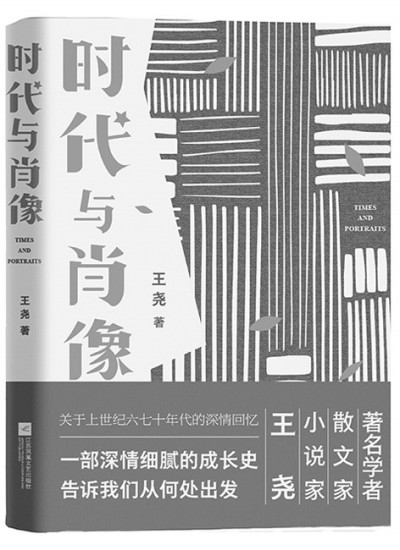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