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构思这篇书评时,去旁听了一次王晴佳教授面向川大师生的在线讲座。讲座围绕海洋史及全球史研究展开,期间王晴佳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历史的“单数”与“复数”。他以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es)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 记》(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例证自古典时代以降西方两大治史传统:多元的和单一的历史,即“复数”的历史与“单数”的历史。王老师指出,虽然长久以来“一部历史”(“A History”)的历史叙事占据主流地位,在19世纪民族史观滥觞之际影响更深;但多元的历史叙事现如今正在不断复兴。
乍看之下,“复数”的历史这个表述并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但它恰恰是构成了世界史(全球史)研究的核心:即多元的历史。这种多元性,也为《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沙盘》一书作者塔利姆·安萨利(Tarmim Ansary,1948-)所捕捉到。但安萨利在书中呈现出的人类文明历程,并非单纯连缀“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文明”——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欧洲和美洲,而是始终立足自身的全球史观,直面各种文明融合与交流,以此构筑自己对人类数千年交往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的独特解读,即探讨到底是“什么撬动了世界沙盘”?
在安萨利看来,每种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全球尺度的主体叙事”(第145页),因此“任何人所认知的‘全世界’”,其实源于不同的人群(他们既可以是不同种族、民族,也可以是不同地域、时代)从自身群体出发看待世界历史。他因此将不同文明,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欧洲和美洲,称为“世界历史单子”(world historical monads)。安萨利的“历史单子”借自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s)概念,取其既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又通过知觉来反应整个宇宙之意,并且每个单子都不一样。而在文明内部,他又利用星座的文化建构属性将各类人群及其观念置于寰宇之下,称之为“社会星群”(social constellations),并认为一切个人及其观念组成的集合中的各种要素,可以新增,也可以消失,但“若是脱离了文化,便不复存在”;而又因有文化的存在,即便单一的个体离开,群体依然能够影响历史与现实。书中一个重要例子是印度,作为几乎贯穿本书的各个章节的文明之一,代表的恰恰是与中国那种逐步形成“国家主导、自我中心的单一体系”相对的“历史单子”。
印度之于中国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政治环境中:即便是出现较为强盛的政权,如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约公元前187年)、笈多王朝(约320-约540年),甚至到17世纪末之前的莫卧儿王朝,都未能统一南亚次大陆。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并未影响印度在不同时期实现文化、贸易、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繁荣。安萨利一方面将个中原因归结为政权林立并未对以村庄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印度社会构成太大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正是印度文化中多元共存的特征使得印度人不在乎政治的分裂,“因为他们能从印度教这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中寻得团结”(第153页)。虽然曾经一度出现过的单一自洽的叙事,即佛教,但终究还是让位于兼容并包的叙事(印度教)。而这种包容性也让截然不同、甚至全新的“社会星群”进入印度,前有伊斯兰文化,后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前一个问题上,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既存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但一定程度文化混合的趋势又有迹可循,从而形成了一个至今“仍为两个互不相融叙事所占据的”印度;而后者在1857年实现对印度征服之后的历史,安萨利虽未触及,但我们依然能够明确了解,在当下这个由机器和信息主宰、全球图景已然形成的世界,印度依然拥有它的影响力。
但如果单纯使用“历史单子”抑或“社会星群”加以叙述,那么本书可能就带给人一种人类历史仿佛只关乎观念与叙事变化的错觉。事实上安萨利开篇就将工具、语言、贸易视为普遍存在的构成人类文明存续的客观条件,并始终强调“5M”(即通信、数学、军事、金钱和管理)的重要性,从而赋予“历史单子”“社会星群”客观实在性。
除此之外,安萨利还强调环境与信仰的重要性。不同群体所聚集的环境,决定着这个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方式,继而注定了不同环境中人们的互动。而信仰体系(不仅仅是宗教)则帮助人类适应环境,但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的集体经历也不尽相同,由此发展出各自具体的信仰体系。人类社会的早期互动源于不同环境下生存方式的差异,它既可以表现为以物易物的互利共生,但往往也注定会因为贸易、资源乃至信仰产生摩擦和冲突。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甚至远距离的群体间的 联 系 也 开 始 出 现:以1095-1272年十字军历次东征为例,形成于截然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交汇的地理界线长达数千英里,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围绕资源和贸易线路,甚至仅仅是某一城镇控制权的争夺必然带来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伴随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两大文明的双向交流——这种交流并非对等,甚至可以明显发现东方对西方的输入远大于反向输入,正是这种包含了技术、规则和思想的全面西输,帮助欧洲单子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1500年之后开始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而在公元11-13世纪,它就已经开始超越伊斯兰文明。
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当整个地球开始连接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反映到人类社会之中,除了原来的不同环境下的直接互动之外,还出现了间接的,被安萨利称为“涟漪效应”的联系。他对英国白银外流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清朝内部的社会动荡的简要回顾,实际上是对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对于“西方的兴起”与“东方的衰弱”在“结构和运动周期上相互依存”判断的重申,但安萨利不仅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是欧洲文明兴起后在中国引发的“涟漪效应”,还提出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解释世界的主体叙事面对西方冲击不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濒于解体,而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这个历史单子开始面临巨大变动。
通篇读来,安萨利的这本全球文明史既有别于中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强烈的“参与感”,也不同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可以避免让世界史成为受控的“带有视角的游戏”(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立场。他的这种观察视野和写作倾向无疑与其“曾作为‘局内人’”经历“两种文化、两套叙事”有关:安萨利出生于喀布尔,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则为美国人。他在一个“亲属关系极为密切的传统阿富汗大家庭”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期,16岁随母亲到美国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从此远离他曾经的阿富汗家园。而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又夹在接受正统伊斯兰教义的弟弟与适应彻底世俗化的美式生活的姐姐之间“跨越地球的裂痕”之间。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差异,让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体会到困惑和巨大冲击。直到1980年前往南非和土耳其的旅行才让视“世俗的西方文明为家园”的安萨利重新拥抱伊斯兰文明,而2001年的9·11事件又令他在愿意为阿富汗发声的同时,又能面对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坦然以“两种文化同时都能接受的方式生活在两种文化中间”。尽管《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沙盘》一书并不是一本专门探讨文化冲突的作品,但正是安萨利的身份成就了这本视角独特的全球史读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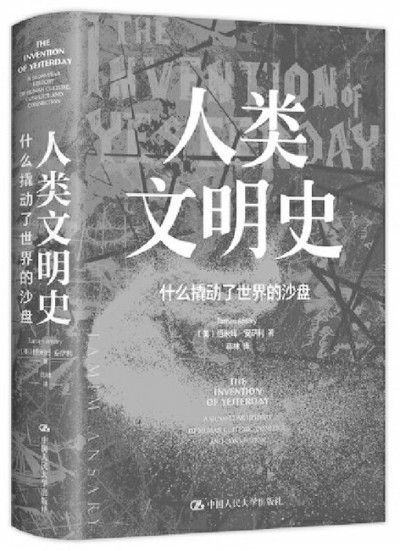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