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开始的? 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又是何时衰落的以及为什么衰落的?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为此提供的各种解释充满了书架,其核心不外乎试图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正是这两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的历史命运,成为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
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历史观(包括强调“路径依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这种历史观如今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如此流行和“不证自明”,以至于需要我们对西方近代史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从微到著去重新审视和批判,才能发现它的破绽。
历史观,无论正确与否,对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正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世界,才造成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企业家和政治家对当今世界的变化迷惑不解,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在思想和行动上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爱恨交加。而那些误以为自己不受任何历史观影响的精英集团,实际上都是某种历史观的奴隶,并每天都在以西方灌输的历史观理解和创造着自己国家的历史。
但是,经过西方上百年打造形成的这一流行历史观,却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真实发展史严重不符。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还有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后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腊“民主”和古罗马“法制”一直是西方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而衡量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最佳标准,不外乎人们衣食住行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水平——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文明体系的生产力和服务于这个生产力的深层制度,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活水平就不应该低于而是应该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因为按照西方中心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比同时代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才能折射出比中国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优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通常都比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
18世纪启蒙思想先驱,卓越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欧洲近代史上最才华横溢的既精通古希腊又通晓18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师伏尔泰,在论述煤炭、炼铁和中国古代的其他科技成就时说道:“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读书写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是很少染色的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却是由细得不可思议、轻得不可比拟的蚕丝,通过木制织机细密织成,再用五颜六色的有机染料层层上色,经过千针万线裁缝而成的绫罗绸缎。如果那个时代有什么精密工艺能够形象地体现公元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运算之精妙的话,非中国丝绸的制作过程莫属。
丝绸产业精细的工艺流程与分工环节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丝绸制造业不是任何古希腊城邦小农经济轻易能够拓展与承担的产业。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创造运河体系和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现代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只有高度发达的大一统市场经济与信用体系才可能流通纸币。而欧洲国家要等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到了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也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商品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没有任何商品(除了黄金)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即便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算起,直到大约1800年工业革命爆发时(也就是直到中国清朝开始由盛而衰的时期)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换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在那个欧洲开始发生巨变的300年(1500—1800)间,全球货币的流向仍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盗取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了中国,为的是购买中国的商品。比如17世纪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游荡,最后都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相比之下,号称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匮乏程度,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从古希腊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初期,中西方在生产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异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由此可见,流行历史观强调的古希腊包容性民主自由传统和日耳曼部落的法律文化,并没有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为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直到工业革命爆发前夕的整个西方世界带来超越东方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繁荣。
为什么?
因为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
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比如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和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与之相对,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predict⁃able and calculable)的法律结局,尽管对某些个案的裁决可能会与实质正义者所根据的宗教与伦理原则或者政治权宜相冲突。由于形式正义减少了个人对统治者的恩惠与权力的依赖,它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而形式正义恰好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的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是存在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法规是运用理性制定的,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因此在韦伯看来,脱胎于古罗马法律传统的这种程序正义,提供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因而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并影响了好几代西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他们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论,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哪怕那些长期研究东方古代历史文化的西方专家也不能免疫。
他们描述的这种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差异如果存在的话,真的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原因吗?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即便是文艺复兴以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虽然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因此,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国家,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靠军队来捍卫法律和社会秩序。
其次,韦伯的先辈——18世纪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早就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任意不公时精辟地指出过:“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韦伯正是这样一位善于以斯多葛派心情来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社会学家。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坚决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包括他所处的欧洲启蒙时代),其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次又一次问道,东方的编年史作者又会如何看待欧洲的封建体系? 它看起来难道比我们描述的东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吗? 伏尔泰说,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这样的统治方式只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而中华文明已经生生不息延续了好几千年。
不过,这些西方启蒙思想家也对中国人在逻辑学、几何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方面与17—18世纪同时代西方相比的严重落后,都一直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和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个别人,中国朝野普遍都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
是什么因素导致近代中国对形式化的数学不感兴趣? 流行历史观认为,这也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
其实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的何止中国人。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以前也对演绎数学普遍不感兴趣,但是却在专制暴君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的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俄国人直到18世纪以前也普遍对演绎数学和科学不感兴趣,但是却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日本人直到1868年决定直接面对并参与到欧洲列强“打砸抢掠”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之前,对科学与演绎数学也像中国人一样不感兴趣,但是却在明治维新以后在作为绝对君主的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这东西感兴趣了。同理,中国人一旦意识到民族存亡实质上是国家间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竞争,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才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连16世纪的宗教改革大师,路德和加尔文都蔑视和嘲笑数学和科学。罗素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
但是,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由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这种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就产生了国家力量对这类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虽然早期的繁荣仍仅局限于精英阶层)。
比如达·芬奇在年轻时写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一封求职信,便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各个城邦国家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巨大兴趣与需求。在这封求职信中,达·芬奇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基于火炮这种新型战争模式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这反映了达·芬奇所处的时代,国家力量对人力资本的最大需求并不是艺术才能,而是军事才能和与此相关的数学知识。
因此,达·芬奇的求职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西方流行历史观所描述的、独立于东方文明影响的、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自身传统的历史运动,并不是一个所谓宗教改革与思想解放下艺术家个性自由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运动。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这么高大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他们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起来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军工产品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也像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和诗人画家的涌现一样。
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
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是各个欧洲王室在延续几百年亡国灭种的热兵器战争压力下,相互竞争的结果。这个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了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同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在竞争中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是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的。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大国争雄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制度;从此以后,法国才在科学领域方面崭露头角。而法国从此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接任路易十四的路易十五国王,又在18世纪为培育军队将领专门拨款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统一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提供了杰出军事人才。
古希腊的数学知识对于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来自阿拉伯文明的外来品。它既没有为古希腊自身,也没有为(古希腊灭亡之后)全面继承了古希腊文明遗产长达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330—1453)带来科学革命。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之所以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与维持这种战争的巨大财政压力,刺激了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钢铁般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
火药对于欧洲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转型具有极端重要性。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
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多数战争,都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荡涤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战争意志又缺乏海战经验和现代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付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相互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韦伯自己的祖国(德国)在19世纪实现统一之前的兵荒马乱与贫穷积弱,和统一之后才产生的经济奇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和加入欧洲列强的打砸抢行列以后才产生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在结束清末与民国的兵荒马乱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的工业化奇迹,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了韦伯把欧洲繁荣归因于古罗马日耳曼部落的法治传统的理论,以及他更加可疑地把近代欧洲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下东方国家的衰败,归因为基督教比儒教更富有理性经商精神和勤俭节约美德的宗教决定论。
而且,韦伯主义者这一“西方民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才是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流行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公认其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君主制先进和包容,其人民远比英格兰人勤劳,其金融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远比英国完善的荷兰共和国。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经采纳了更为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远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习模仿来的。在17世纪英国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使得君主制的英国超越共和制的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与能工巧匠。但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荷兰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100年才开始复制了这场早已普及欧洲大地的制造业革命,远远落在法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之后。为什么?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俄国(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提出这一系列问题,是希望对流行历史观提出正当的质疑,以便于我们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对李约瑟之问的最终解答,也会自然而然地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韦伯之谜。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正如尼采所说:“我们需要历史,为了生活和行动。……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
(本文摘自《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文一著,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第一版,定价:79.8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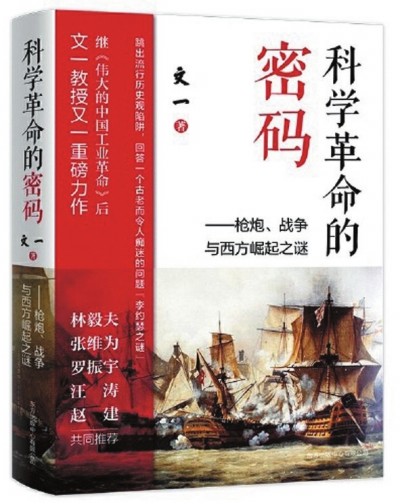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