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国教授点校的《王安石文集》最近在中华书局出版,连日拜读书稿,除了有先睹之快,更感受到这是一部功力深厚、有益学林的扎实之作。
作为网罗六艺、糠秕百家的一代人豪,王安石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其文集也曾有过不止一种的整理本。最初有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临川先生文集》,后又有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公集》。这两种时代较早的整理本免不了因筚路蓝缕而有欠周备。前者使用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明代何迁本为底本,没有参校宋代龙舒本;后者据龙舒本点校,但参校本少,失收篇目多,而且还是用简体字排印的版本。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一种简体横排的《王安石全集》,虽是据《王文公文集》标点,但连校勘记也不出,只是供大众阅读的便捷版本,并非规范意义上的古籍整理作品。诗文集的笺注本则有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清代张宗松清绮斋本标点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以及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2002)、《王荆公文集笺注》(2005),高克勤《王荆文公诗笺注》(2010)等,但也都未能尽善。
凡此种种不由得使人感慨,如王安石这样的名贤大家,其别集竟无精良上乘的整理本出版,仿佛《西清诗话》中所言的王文公集“迄无善本”的情形于兹复见。直至2016年王水照先生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出版,才一改这样的局面。《全集》整理工作汇集了众多王安石研究的专家,更有王水照先生主持,质量上乘,深受好评。于此或许不免有人担忧,力作在前,剩下的多是王安石研究中积疑已久的难题,刘教授的《王安石文集》是否还能有所突破呢? 拜读书稿之后,这样的疑虑一扫而空。无论是在标点校勘,还是在王集版本厘析、作品辨伪辑佚等方面,刘教授均有发覆创新,让人为这部后出转精的力作发出一声因难见巧的赞叹。
首先,从各种王集版本的梳理和选择上,刘成国教授便花费了一番精力,最终选定以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的明嘉靖何迁本《临川先生集》为底本。以往整理使用的何迁本多是据《四部丛刊》的影印本,但刘教授仔细对比了明刻本与《四部丛刊》本,发现后者虽易见易得,但并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覆刻何刻本(何刻本亦非覆刻詹大和临川本),且《四部丛刊》初印本存在误字,再印本又做了一些描润回改,和明刻原本不可同日而语,故毅然为“去伪存真”而“舍近求远”。校本则有南宋龙舒本、王珏本、明代嘉靖五年刻本、嘉靖应云鸑本等十一种之多。其中仅王珏本就参校了国图藏宋刻元明递修本、北师大藏残宋本、国图藏黄廷鉴校本三种。诗集的部分还参校了元大德本《王荆文公诗笺注》、朝鲜活字本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等。此外又选取南宋刻本《皇朝文鉴》《圣宋文选》等十余种文集、笔记。真可谓是广搜博讨,蔚然大观。
其次,在点校方面新整理本《王安石文集》更是精益求精,对以往整理本之失亦多有匡补。譬如集中卷十六《送郓州知府宋谏议》诗“庙谟资石画,兵略倚珠钤”句,复旦《全集》版作“庙谈资石画”,下出校记曰:“‘庙谈’,宋刻本、龙舒本作‘府谟’。”而刘教授对比互勘,发现明代何迁本是作“庙谟”,《四部丛刊初编》所收的何迁本初印误作“庙谈”,后印本曾描润回改。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古代作“谈”字的刻本,《全集》本是受《四部丛刊》初印版之误。而且“庙谟”一词出自《后汉书》,指为朝廷谋算,与下句“兵略”相对,“庙谈”语不经见。故而此次新整理本作:“庙谟资石画”,下出校记曰:“‘庙’,宋刻本、龙舒本作‘府’。”
又如卷九十一《王平甫墓志》“年止于四十七”下校记,刘成国教授言:
原有“以熙宁七年”五字,据递修本、嘉靖五年本删。龙舒本亦有此五字。黄校曰:“‘四十七’下明刊多‘以熙宁七年’五字。”则黄所见宋本并无此五字。按,神宗熙宁八年(1075)四月王安国尚在世,撰《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其卒在熙宁十年八月十七日。详细考证,可见拙文《新出土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与王安国卒年新证》。
刘教授关于王安国卒年一文我之前曾有拜读,乃是据洛阳新出土的《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王安国熙宁八年撰)以及王安石《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曾巩《祭王平甫文》等史料考订安国卒年在熙宁十年。新出土文献和传世史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扎实可信,原本的考证已可定谳,此次新整理本又曾加国图藏宋刻元明递修本《临川集》上的黄廷鉴校语按断,堪称摭实周详,巨细靡遗。
这样考实祛疑的例子在书稿中俯拾即是,如二十一卷《寄余温卿》诗“独过嵇山锻树阴”,《全集》版作:“独过稽山锻树阴”,下出校记:“‘稽’,《全宋诗》校改作‘嵇’。”此次新整理本作:“独过嵇山锻树阴”,下出校记曰:“底本作‘稽’,今据元大德本改。按,嵇山,在今安徽宿县西南,相传嵇康曾居此锻铁。稽山,即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与嵇康无涉。”
再次,新整理本在对王安石作品的辑佚和辨伪上成果斐然。本次辑得的集外文87篇、诗词81首,尤其是最后的“存疑与辨伪”部分,一共辨证了多达51篇作品的真伪问题。每篇作品下不仅详明出处与各本异同,还广罗相关史料与古人论说。如文献不足,事有两可,则审慎存疑;如有罅隙乖违,蛛丝逗露,则批亢捣虚,一语中的。譬如《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一文,《永乐大典》属王安石名下,复旦《全集》版作佚文收录,下注曰:“《皇朝文鉴》、《文章辨体汇选》皆属元绛。”然作者究竟为王为元,未能按断。刘教授则辨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韩琦再判大名府在熙宁三、四年间,其时王安石已拜相,不掌内外制,而元绛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文当属元作。”仅一语而断明,可见考史之精。
此外,如辨《回皇亲谢及第启》言:“启曰‘某限列谏垣’,然王安石生平未曾任台谏之职。此启非王安石之作。”辨《(景定)健康志》所载熙宁八年十一月王安石《乞废玄武湖为田疏》言:“此文绝非王安石所作。熙宁八年十一月王安石已复相。”或以历官、或以年岁,一语而断,但实则背后皆有复杂的考证。如《回皇亲谢及第启》刘成国教授曾遍考宋代史料,推断出此文皇亲可能是宗室赵叔盎,而作者则是张璪。元丰二年四月,张璪以知制诰之职赴秘阁考试宗室;五月,兼知谏院。正合文中“限列谏垣,莫趋宫屏”之言。《乞废玄武湖为田疏》除了与王安石判江宁时间不合外,文中“车驾巡狩”之语也颇突兀,神宗朝从未巡狩或议及巡狩江宁,刘教授研判此文作于徽宗、钦宗之际或高宗朝。诸多考证最后写入按语中者却往往仅是直指肯綮的关键一语,这种举重若轻的简明扼要实在让人想起荆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句子来。
以上种种,在在显示了新的整理本是一部精益求精、后出转精的力作。这样的成就当然是源于作者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较早的《荆公新学研究》到前些年出版的《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教授一直致力于对王安石的相关研究,对王安石的生平学行和各种史料文献了然于心,故遇疑异而能洞察微末、辨明原委。
当然,世上难有十全十美的古籍整理,新版的《王安石文集》亦是如此。一方面,王安石一生充满争议纠葛,史料文献真伪相杂,文集版本更是存佚更仆,复杂纷乱。尽管刘成国教授此番对王集版本作了更加详尽的考述和新辨,但依然留有空间深钻再进。另一方面,王集诸本繁多,校勘之时难免眼倦神疲,出现微小疏忽。譬如,新版《文集》第31页《赠李士云》中“大梵天”、第90页《彭蠡》中“龙山”,似皆漏标专名线。而第109页《惜日》“当时三千人,齐宋楚陈周”句,“周”字与前四国名皆加专名线。考虑到孔子弟子中有名者并无周人,孔子周游列国亦未曾入周,则此“周”字可能作周游、周遍之义而不划线更妥。此外,第76页《河间》校勘记中引李壁注曰:“武帝立三王,皆冇制册。”“冇”即没有,而据文义及《汉书·武五子传》此处当是“有”义,似是因书版漫漶而将“有”字误作“冇”。但一眚不能掩大德,新版文集的成绩是巨大的,是现今最为精良的版本。
众所周知古籍整理即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尽管有不少专家学者怀着一种热忱和奉献精神,愿意从事这项采百花而成蜜的工作,但在现今的高校工作中,也不得不因许多行政公务和日常杂事消磨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因分身乏术而难能周全。如今,刘成国教授以其专精的学养和对王学的娴熟,不计烦难地从事琐于《尔雅》虫鱼的工作,在千载后重新为王荆公洗剔眉目,更又嘉惠学林,这实在是可敬可佩的。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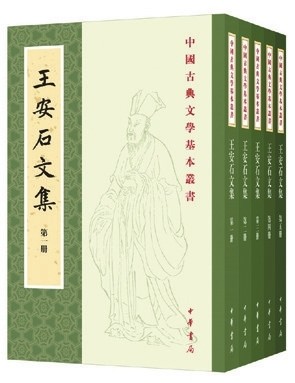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