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景琳兄相识于北大。他1955年出生,我1948年呱呱坠地;他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我忝列文学78级。同学入校年龄参差不齐,甚至相差十五六岁,是全国77、78级大学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必修课或选修课,两个年级的同窗在课堂时有交集,但交流的机会无多,即使人数不多的选修课,也只是“脸熟”而已。
77级朱则杰、叶君远两位学长在校时即有文章发表,却只闻其名,不识其面;认识两位学长是在毕业以后的学术会议上才“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77级的张鸣学长,毕业后考上赵齐平先生的研究生,后留北大中文系任教。因为他身材修长,又服饰整洁,给人以玉树临风之感,因而印象深刻,却久久不知其姓名。21世纪以后,因与这位高个子多次受邀一同参与人民大学叶君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才逐渐熟络起来。77级郭小聪学长,入学时已有“诗人”的名号,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2009年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举办的新诗研讨会上,我在与会者名录上发现了“郭小聪”的名字,于是通过会务人员在毕业二十七年后结识了昔日的同学,感慨良多。
然而与景琳的相识却是在北大图书馆中完成的。课余饭后,景琳兄常常出现于北大图书馆的201文史阅览室。然而201阅览室同学较多,在“静,轰轰烈烈的寂静”中也并没有相互交谈的机会。文科工具书阅览室的空间相对小得多,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景琳。当时我正准备毕业论文,他则在为考研做最后的冲刺,在如何充分利用《中文大辞典》的交流中,我们开始了迄今将近四十年的友谊。
我本科毕业后至中华书局文学室工作,景琳兄则至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因科研与出版的需要,我们之间的交集反而比在学校期间的机会多了。景琳兄擅长策划组织传统文化方面内容的选题,“中国古代文化纵横谈”丛书五种之一的《中国鬼神文化溯源》由景琳兄操觚,我则撰写了《智谋与艰辛——中国历代商人透视》,皆出版于1992年。《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由王景琳、徐匋主编,阴法鲁先生撰序,我则忝列于编委与撰稿人中,这又是一次愉快的合作。这部书也出版于1992年。在这前后,景琳兄还出版了《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鬼神的魔力:汉民族的鬼神信仰》等专著,与徐匋合作则有《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历代寓言名篇大观》《比目鱼校注》等,可见其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及时不我待的治学精神。
1991年以后,景琳与夫人徐匋辗转北美移居加拿大,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加拿大政府官员语言培训工作,在海外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2年以后,景琳兄回归科研,重操旧业,先后出版了《庄子文学及其思想研究》与《庄子的世界》(与徐匋合作,中华书局2019年 出版),后 者获评该年度“中国好书”。《燕园师恩录》则是由凤凰出版社作为“凤凰枝文丛”之一,于2021年6月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其八有云:“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凤凰社的梧桐树引来景琳兄这只五彩斑斓的美凤凰,大有眼力!
《燕园师恩录》可说是一部感谢师恩之作,共记述了十七位老师,其中有著名的吴组缃、林庚、吴小如、阴法鲁等老一辈学者,也有当时中年甫过的褚斌杰、陈贻焮、曹先擢、何九盈、吕乃岩、周先慎、彭兰、谢冕、乐黛云、孙玉石、徐继曾、袁良骏等知名学者,还有图书馆对同学热情有加、服务周到的李鼎霞老师。作者娓娓道来,情深意长,令我开卷竟难释手。
景琳兄性格外向、情商高,善于求教是他较早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治学境界的基础。我则性格内向,少壮未必没有努力过,老大徒伤的自卑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于治学长久处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阶段,而难以有所发微抉隐,羞于向老师问学当是原因之一。
所谓“问学”,就必须有问题意识,才能有的放矢,否则自己朦朦胧胧,何以请益?
在《诗化了的学者、教授——久闻其名的林庚先生》一文中,景琳兄写道:“我前前后后去过林先生家三次,遗憾的是,三次都没能尽兴地向先生请教,听其教诲。当时的想法是,研究《庄子》之后,下一个研究课题便是楚辞。届时一定要好好向先生求教。可惜事与愿违。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辗转于北美,最后定居在枫叶之国,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了。”于我而言,这样的遗憾却无从谈起,因为我与老师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交集。
在《何久盈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景琳兄饱含深情地记述了何老师借阅其课堂笔记以测试自己教学效果的轶事:“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又到了上古汉语课的时间。我急匆匆走进教室还未落座,便看见我的课堂笔记本已经端端正正地放在了讲台上。再一抬头,何老师正招手示意我过去。何老师一边递给我笔记本,一边对我说:‘你的课堂笔记,记得很详细,也很认真。古汉语跟其他课程相比,比较难,可是有意思,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如果你对古汉语有兴趣,想进一步钻研的话,我可以推荐几本书给你。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的笔记本里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如此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司空见惯,并非个别。
《我的第一位文学史老师——忆吕乃岩先生》记述了吕老师执教的情形:他讲授先秦文学课,甚至可以将三百七十多行的《离骚》背得滚瓜烂熟,引证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极大地感染了77级全班同学。这激励对吕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景琳下功夫背诵了大量楚辞作品,日积月累,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作者就此深有感触地写道:“后来研读《庄子》时,比较庄子与屈原神话运用的异同,分析两者之间不同的艺术特色的想法就很自然地冒了出来。我注意到庄子和屈原虽然都深受上古神话传说的影响,但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与意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想法直接启发我写了《庄屈对神话传说运用之异同》《庄子与屈原艺术手法异同试析》两篇文章,并分别发表在《求索》与《河北学刊》上。这两篇文章的完成不能不说是受吕老师影响背诵《离骚》以及其他楚辞诗歌的一个收获。”
在《宽厚仁慈,诲人不倦的师者——怀念陈贻焮先生》一文中,景琳又勾画出这样的场景,他轻松地写道:“跟陈先生聊天,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从学术界动态,当下的研究热点,文人逸事,到日常生活琐事,只要一开聊,那就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丝毫没有师长辈分间的顾忌与隔膜。”景琳在大三时选修了陈贻焮先生的“三李研究”课,向陈老师提交了《李白从璘辨》的课堂作业,提出李白追随永王李璘谋反属于自愿,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持之有故且言之成理,陈老师充分肯定了景琳的观点,并在其作业的空白处加以密密麻麻的批注,从行文逻辑到遣词造句乃至材料运用技巧皆精心指导,并先后看了两稿。最终这篇文章于1992年得以在《枣庄师专学报》发表,在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此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
《“清辉依旧透窗纱”——忆彭兰先生》一文记述作者选修彭兰老师“高岑诗研究”课及与彭老师的交往。景琳在毛乌素沙漠地区生活、工作过多年,熟悉西北塞外风光,因而对唐人边塞诗一直情有独钟。课下他与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彭老师探讨王之涣《凉州词》不同版本的问题。景琳认为通行版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远不如另一版本“黄沙直上白云间”的描述更加切合实际,因为玉门关与黄河相距千里之遥,诗人何所见而云然? 然而从意境上讲,“黄河远上白云间”似乎远比“黄沙直上白云间”更富有韵味,画面感也更强,后人遂将“黄河远上白云间”作正本,而将“黄沙直上白云间”作另说了。彭老师以为其分析有道理,就鼓励景琳就此写篇赏析文章,将两说一同介绍给读者。这种师生之间朴素自然的探讨学问之道,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彭老师还时常邀请同学去她家做客,以致事后作者无限感慨地写道:“那个年代,师生关系十分单纯融洽。拜访老师既不需要收到老师的邀请,也不需要事先预约,都是直接打上门去。”至于老师到学生宿舍与晚辈探讨学问之道,也是常有的事,景琳就此写道:“那时的老师也有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互动的传统。至少像陈贻焮、袁行霈、陈铁民、周先慎、吕乃岩等先生,就都曾多次来到77级中文系学生居住的32楼看望大家。”
最见景琳书写魄力的还是《学者教授群里的“性情中人”——纪念吴小如先生》一文,“在我心目中,吴小如先生首先还不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更是一位独具魅力的‘奇人’‘性情中人’”,景琳以“奇人”“性情中人”定位吴先生,并非无的放矢。不合时宜,与同事关系多呈紧张状态,当是这位颇显孤独的“学术警察”的常态。景琳写道:“最近翻看《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一书中收入的‘榷疑随笔三则’,我就颇有感触。此事的起因是文化名人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将‘宁馨’释为‘宁静、馨香’,将‘致仕’说成是‘到达仕途’。这本来是个不值一驳的错讹。但不知何故,著名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特地为此作文替余秋雨辩解。吴先生见状不禁拍案而起,撰文与章先生商榷。文中,吴先生首先中肯地指出‘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还提出‘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吴先生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认真态度。然而,更能见出吴先生无所顾忌、耿介率真性格的,还是他在文章最后向章先生提出的由衷告诫:‘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在今天博士满街走的社会中,错别字或词不达意经常出现于横幅、标语乃至公告、文件中,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所谓“学术警察”属于褒词还是贬词,这里不论,但呼吁更多的“学术警察”出现,说是当务之急,或许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四年本科,我向老师请益的机会无多,问学之道专注于图书馆。吴同宝(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一类的书籍,我买了不少,相互参看再按图索骥,意图从目录学入手,为以后从事文史工作打好基础。景琳则抓紧机会亲炙于北大的著名教授,再充分利用图书馆,双头并进,显然要比我“单腿蹦”有捷足先登的优势。
由此而论,这部《燕园师恩录》就不仅是纯粹的感谢师恩之作了,其揭示治学门径与方法论的意义也不能低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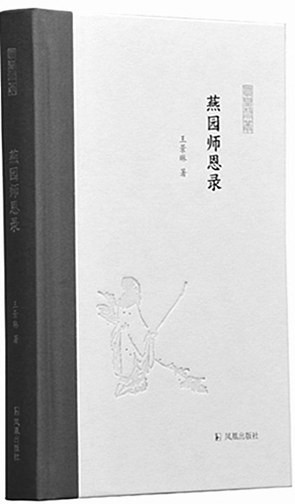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