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因其作品“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后黑塞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拥有最多读者的德语作家,他的小说一度风靡欧美、日本,深受青年人喜爱。而他于1922年创作的小说《悉达多》(Siddhartha)所演绎出的婆罗门之子悉达多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孤身一人展开独特求道之旅的传奇,一直到今天依然饮誉文坛。《悉达多》故事发生的场景尽管是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但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却是错综复杂的。
中国抑或印度?
夏瑞春(Adrian Hsia,1938—2010)认为,黑塞的这部小说所表现的无非是中国道家的智慧。他用了大量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引文和思想来证明,《悉达多》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中国思想。张佩芬(1933— )认为:“他(指黑塞——引者注)的《席特哈尔塔——一个印度故事》便是有力的论证。这本书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多层次地逐渐深入到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使一个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成为老子和庄子思想的体现者。”仿佛黑塞成为了一个汉学家,而悉达多也成为了一个纯粹的道家人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仅仅是华裔学者,于尔根·韦伯(Jürgen Weber,1941— )在《中国的悉达多:有关赫尔曼·黑塞“印度诗”〈悉达多〉的几点思考》中,就指出《悉达多》的第二部很多思想直接出自卫礼贤的《道德经》译本、马丁·布伯的《庄子的言辞与比喻》等书。
而印度裔学者乌里达吉利·迦奈什(Vridhagiri Ganeshan,1947— )却认为,整个的《悉达多》其实是受佛教和印度思想影响的产物:
有人声称,黑塞在他的《悉达多》中摆脱了印度的影响。我们要展示给大家看的正好是相反的尝试,黑塞在《悉达多》中恰恰成功地显示出了令他神往的印度宗教,以及后半辈子的他作为人和诗人从这一思想世界中所接受的东西。
在黑塞看来,佛教相对于传统的婆罗门教是印度的新教,它们都有精神内在化的倾向,也同样以个体的思考和良知来对抗旧的权威:佛教反对婆罗门教,新教则在很多方面与天主教背道而驰。因而在《悉达多》一书中,除了佛教思想之外,迦奈什想要说明的是整个印度思想都有所反映。
其实,任何企图将《悉达多》的思想解释为单一来源的尝试,都是片面的。
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
黑塞很少将世界各种文化、文学作高下之分。他在《悉达多》出版之后的1923年2月写给卡颇勒(Berthli Kappeler)的信中说:“我并不认为印度的智慧比基督教的智慧更高明,我只是感到它们更少精神上的东西,更少不宽容的东西,更宽广,更自由而已。”
美国著名黑塞的研究者齐欧尔科夫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1932— )认为,悉达多的发展也遵循 着“三 阶 段 周 期”(Drei-Stufen-Rhythmus):天真无邪的童真时代——尽管在小说中没有被描述;而我们所认识的悉达多已经是处于知识和怀疑的萌芽之中了;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在小说最后悉达多所达到的宁静,这是重新达到的一种更高的纯洁无瑕的状态。黑塞本人则认为人生发展有三个阶段: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纯真无瑕的(天堂、童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前阶段);第二个发展阶段是由此走向罪恶,走向对善恶的认知,走向应对文化、道德、各种宗教以及人类理想所提出的各种挑战,此时人会意识到道德无法实现,正义和至善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阶段以绝望而告终;黑塞认为,绝望或者导致毁灭,或者通往第三阶段的精神王国,这能使人体验到一种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状态,让人进入一种被拯救以及解脱的、一种新的、更高的、无须负担责任的状态,简而言之,是进入了信仰状态。三阶段周期并非基督教所特有,在印度的传统中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对黑塞来讲,重要的并非在南亚和东亚的文化中寻找欧洲所没有的思想,而是以欧洲文化、宗教、思想为基础,建立东西方相互沟通的桥梁。
其实在《悉达多》的行文中,到处可以看到黑塞作为虔信派后人的影子,举例来说,在讲到乔答摩佛陀出现的时候,黑塞写道:“是的,世界生了病,人生难以忍受——却看到这里似乎涌出一股清泉,这里似乎发出了福音的呼唤,其中充满着慰藉的、温和的而又崇高的许诺。”很明显“福音的呼唤”(ein Botenruf)是从《圣经》中来的,只不过从耶稣基督转到了佛陀那里而已。
在小说的最后,悉达多提到的“爱”(Liebe)的内容,所表达的是人优美而亲密的生命体验,而这显然跟印度各种宗教的爱都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圣方济各(Franz v.Assisi,1182—1226)的“爱”。其实黑塞早在1904年创作的小说《彼得·卡门辛德》(Peter Camenzind,也被译作《乡愁》)中就有过描绘:经过巴黎的颓废生活之后,主人公彼得最终是在圣方济各的精神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真实内心生活。此外,劬嫔陀最终在河中看到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脸,也让人马上想到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约1260—约1328)所描述的涌入到自身的河流图景。
至于黑塞为什么选择了印度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家庭的背景,有关这一点,黑塞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及。黑塞的研究者温特(Helmut Winter)指出,读者还应看到,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危机以及到远东的神秘主义之中去寻找心灵慰藉的尝试,对他者文化的理想化,这一切都在黑塞的《悉达多》中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这部书至今依然是德国人对印度文化向往的适当表述,也是德国人对印度哲学的力量和智慧的信仰。温特就此写道:
有关认同的神秘主义思想是通过“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为相互矛盾的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并且在超验的宇宙之神(梵天)的观念之中抽掉其意义,通过禅定去发现所获得的新价值。在黑塞看来,印度的神秘主义所指出的必然是一条从“主观的、实证的”自我向一个“更高的、神圣的自我”过渡之路,后者的 自我参与了“没有个人以及超越个人”(Un- und Überpersönlichen)的建构——完全放弃了所有宗教的,确切地说是世界观的各种责任。印度神秘主义的三个发展层级——从苦行的“纯净”(via purgati-va),到冥想的“光明”(via illumina-tiva),最终到达神秘之统一(unio mystica)——这符合黑塞对于实现一切精神可能性的需求。
其实所谓的“三层进路”实际上是基督教神秘主义所描绘出的追求身(soma)、心(psyche)、灵(penuma)的三层。后来这三种层次在西方教会中演变为洁净的(purgative)、光明的(illuminative)、统一的(unitive)固定模式。在这里,表面上是印度的神秘主义,实际上又回到了黑塞所熟悉的欧洲基督教传统之中。温特接着写道:
在悉达多的形象中,黑塞所要表达的是他自身的精神问题,他要让悉达多知道,所有通过禅定找到一条摆脱自我之路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努力——《悉达多》的第一部的结局是自我的回归,对涅槃的深深怀疑:……
因此,黑塞的问题意识是自己的,只不过借助于佛教的一个外壳和背景表达出来而已。这本书绝非一本佛陀传,黑塞也无意要创作一部释迦牟尼佛传,而只是借名为悉达多的求道者来表明自己对宗教的认识与体验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即便是在印度本土也备受关注,被译成过十几种印度方言的原因。
世界主义理想
由于外祖父和父母的特殊经历,黑塞从小就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想法,这是他朝向世界主义理想迈进的第一步。他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魔术师的童年》中写道:
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仅仅是陆地上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世间还存在着亿万的人们,他们有着与我们不同的信仰,另外的习俗、语言、肤色,另外的神祇道德和恶习。
黑塞继承了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以来的德国世界主义的传统,希望借助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的智慧重新回到全人类所共属的同一精神共同体中:
他(指歌德——引者注)即便在1813年未曾写出国歌来,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坏的爱国者。但人类总体带给他的喜悦大大超越了德意志整体,而后者是他熟悉并且爱戴的。在思想的国际世界中,在内在自由和知识分子良心的国际世界中,他是一个公民和爱国者,在他最伟大思想的瞬间,他是如此地崇高,以至于各个民族的命运对他来讲不再是单独具有重要性,而是以从属于整体运动之一种出现。
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构想,是因为他有着广阔的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及超越民族的世界意识。他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逾越了地域和特定人群的局限性,克服了民族主义的偏见和狭隘。歌德藉“世界文学”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所有的文学将合而为一的时代的到来,这是一种要将世界各国的文学统一成一个整体的构想。悉达多最终寻找到他真正的、最根本的本性和认同,是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的人性。在《悉达多》一书的结尾,黑塞多次提到了“统一”(Einheit),这可以说是他最高的追求了:所有生命现象和力量的统一。正是在这其中隐藏着与西方截然对立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大战的黑塞对西方文化中的冲突和矛盾可谓深恶痛绝,他希望在印度和中国的精神中找到一种和谐,特别是内在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摈弃西方精神的全部。这样的结尾,与其说是印度式的,不如说是东西宗教、思想的大融合。在探索东方精神的征途中,《悉达多》仅仅是中间的一站,在未来的几年中,黑塞又开始研究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尽管悉达多的求道故事穿着南亚的外衣,但这依然是黑塞自己的传记,是对自我的重新描述。他尝试着将自己从先辈们虔信派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部小说其实是黑塞自我信仰的陈述。
正如卫礼贤对人类未来的认识一样,黑塞也认为,欧洲、印度、中国文化中充分体现人性的东西,共同构成了他对人类未来的认识。中国对卫礼贤从来不是全部,同样即便黑塞以开放的胸怀来拥抱印度和中国文化,也无法洗去他欧洲文化的底色。他自己在《我最喜爱的读物》中专门强调了阿雷曼方言(das Ale⁃mannische) 和 施 瓦 本 方 言 (dasSchwäbische)的文学作品对他的意义,前者所指是流行于阿尔萨斯、巴登以及瑞士德语区的德语方言,后者则流行于德国的西南部,只要举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豪 夫 (Wilhelm Hauff,1802—1827)、黑 格 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海 德 格 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这些出自施瓦本地区的名字,大家就会知道这一方言区意味着什么。施瓦本地区尽管政治比较落后,但在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却出现了众多卓荦冠群的人物。其实,在接触到东方文化之后,黑塞的西南德意志以及虔信派的身份认同更凸显了,只不过这些是以另外的面目出现而已。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毕树棠(1900—1983)在介绍黑塞的文字中已经注意到他作品中西南德意志的特点:“黑瑟是德人所谓‘乡土艺术’(Heimatkunst)派之一典型作家,其作品几完全为施洼本或瑞士之背景,乃一色之地方色彩。”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
因此,很难将黑塞的主张归于印度或中国某一种文化之中。尽管黑塞盛赞印度和中国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蔑视西方文化。如果我们读他的《世界文学图书馆》一书的话,就会发现他所继承的世界文学遗产实际上90%以上来自欧洲传统。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在《印度与1900—1923年间的德语文学》中论述到黑塞的时候指出:“有些我们的思想家和作家能够将东方的理性观念作为自己的榜样,而不是将东方看成一切善的源泉,而西方只有没落。”正如徐进夫(1927—1990)在《悉达多》中文译本(他将书名译作《流浪者之歌》)的前言中所认为的一样:“黑塞志在印度或中国,与其说是回归亚洲,不如说是意味着东西方最高层次的精神会合。”
合题与“统一”思想
“统一”(Einheit)意味着,实际上黑塞已经从西方式的非此即彼(entweder oder)的“排中律”,到了中国式的“既……又……”(sowohl als auch)的包容性大融合(Synkre⁃tismus),这一“统一”同时也是对印度式的“双向否定”(weder noch)的扬弃。
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Proklos,410—485)率先提出,世间万物的发展都可分为停留、前进和回复三个阶段。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中,他将这“三一式”(Triade)发展成为了概念辩证发展的基本公式:一切发展过程都可以分为“正题”(These)、“反题”(Gegensatz)以及“合题”(Synthese)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并认为其中包含一系列对立面相互联系、转化和统一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一切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青原行思禅师(671—740)提出参禅的“三般见解”(三重境界):“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如果我们用黑格尔正反合“三一式”来看“三般见解”的话,青原的三重境界也可以作为正、反、合三个命题来看待。具体到《悉达多》的三部分结构,前四章悉达多对精神世界的正面追求,可以看作是“正题”,也是“看山是山”式对世界的最初认识;中间四章他对感官世界的沉迷,可以看作是对精神追求的反动,是“见山不是山”的否定认识;而后四章悉达多对精神世界的重新认识,达到了智者世界的层面,这是“合题”的阶段,也是“见山只是山”的新阶段。
黑塞1932年出版的自传味道很 浓的作品《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1932),主人公H.H. 的寻道经过也是经历了三个境界:一是天真烂漫的境界,二是怀疑的境界,三是悟道的境界。“三一式”几乎成为了黑塞小说中人物成长阶段的一个固定模式。
黑塞的研究者米歇斯(Volker Michels,1943— )认为,在《悉达多》一书中作者所持的是东西方两极的合命题(Synthese der beiden Pole West und Ost):“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有关这一点,黑塞自己认识得也很清楚,早在这部书刚刚杀青之时,1922年8月 25日,黑塞在写给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的信中称:“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悉达多》要有英文版的出版(德文版几个月后会出版);这部书对一些英文和一些亚洲读者来讲,是将跨越民族、不受时间限制的各种思想联系起来的标志。”如果他只是向欧洲的读者传递了一些亚洲思想和智慧的话,黑塞一定不会想将这部书再翻译成英文,再让印度和东亚的读者阅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部“将跨越民族、不受时间限制的各种思想联系起来”的著作,才希望能有机会向亚洲读者译介。1923年2月10日,黑塞在写给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信中说:“很早的时候我便专心致志于印度研究,也着迷于印度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印度和中国譬喻性的语言里面找到了我的宗教,这对我来讲也就是欧洲所缺少的。”黑塞在《悉达多》中所做的正是将欧洲所缺少的东方这一部分补足,从而形成东西方之间的精神互动。
黑塞在完成了《悉达多》之后,他于1922年在8月在卢加诺的国际会议上朗诵了最后一章《劬嫔陀》,后来得到了当时在瑞士的印度历史学家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1892—1966)的极力赞许。之后黑塞 在 写 给 威 廉 · 昆策 (Wilhelm Kunze)的信中说:“当然了这一令人愉快的证实和满足,与我费尽心力去寻求和争取得到印度智慧那些年月是不相符的,而正是在现在,对我来讲印度和东方的外衣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我看到,西方精神和西方历史所教导的与东方的并无二致。”他后来承认,《悉达多》一书其实是他自己的“信仰”(Glaube):“我并非仅仅会在文章中偶尔谈到我的信仰,大约十多年前我尝试着将我的信仰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悉达多》,其信仰的内容常常为印度的大学生和日本的僧侣加以验证,并予以讨论,而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没有这么做过。”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他写道:“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尽管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但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神秘的基督教,而非教会的基督教,不过它与带有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其唯一的信条是统一的思想——并非没有冲突,而是没有战争而已。”对于一个从一神教传统出来的人来讲,如何处理一种协调东西方不同信仰的关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黑塞来讲,好在这只是内心的皈依,而不需要教会方面的承认。除了“统一”的思想外,最终黑塞写到了“爱”。黑塞自己后来写道:“我的《悉达多》一书并非一种认识,而是将爱放在了第一位。在此我拒绝了教条,将对‘统一’的经验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可以作为重新回归基督教的一个标志,作为新教的一个真正特征而让我感受到。”
即便在黑塞自己看来,《悉达多》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亚洲的精神。这是“西方和东方的合题(Syn⁃these),是间于印度教、佛教、基督教、道教乃至儒教的一个共同的公式”。如果仅仅是用欧洲语言重复印度思想的话,这部作品在印度本土不可能受到如此青睐,不可能被“回译”成十几种印度方言,乃至译成梵文在印度出版,自然也不可能在印度产生强烈的反响。黑塞在1958年在《致〈悉达多〉的波斯读者》中写道:
现在离我写这部小说马上就四十年了。这是一个基督教出身并受过基督教教育人的自白,他很早就离开了教会,并致力于理解其他的各种宗教,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的信仰形式。我努力去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性虔诚形式的共同之处,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个个体所信仰和崇敬的。
德 国 哲 学 家 雅 斯 贝 尔 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1957年出版的《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中,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归入“思想范式的创造者”(die maßgebenden Menschen),德文直译过来是“给予尺度的人”。其实黑塞的思想中有三大组成部分,或者说有三大文化对黑塞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二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古典印度宗教思想;三是以老庄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作为一位以探求人类精神本质为使命的人文主义文学家,黑塞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善与恶、美与丑之对立的崇高的力量,以便协调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以便使得经历了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变得能令人忍受。因此,黑塞认为,人类需要一种崇高的力量——“统一”来拯救其自身。而黑塞在《悉达多》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同样是欧洲基督教文化(他的文化基础)、印度南亚次大陆的宗教精神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的智慧之和。任何一种从单一文化出发对《悉达多》的分析都是片面的。
现代性的问题
尽管《悉达多》的场景被黑塞安排在了古典时代的印度,但悉达多却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现代小说,因为它充满着人的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间的分 裂与疏 离。卢 卡 奇(Georg Lukács,1885—1971)认为,古典诗歌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先验本质系由无处不在的整体性构成的,人和世界是统一的完整体,人们不断进行自我肯定,心灵与世界没有断裂:
诺瓦利斯说,“哲学其实就是思乡”,就是“渴求处处都像在家里一样舒适”。所以,哲学,无论是作为生活形式还是作为规定生活形式的东西以及给诗提供内容的东西,总是“内”与“外”之间断裂的征兆,是自我与世界有本质区别的标志,是心灵与行动不一致的象征。所以,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
现代性便是由于整体性的终结而产生的。人生的内在意义被瓦解了,而黑塞的小说则希望以虚构的方式重构生活的整体,由于作为整体生活的历史状况本身已经破碎,以探索者身份追求整体生活的小说主人公成为了寻觅者和流浪汉。
悉达多自我的丧失和整体性的扼杀,人与其产物之间的异化越来越严重,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古代印度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生的现代性问题。黑塞的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人性,描写人如何挣脱既定的文明形态,对时代进行批判,以寻求自我的精神实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悉达多》一书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备受年轻人追捧和狂热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
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曾引无著的话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我想,有了这句话,我们就不至于曲解《悉达多》一书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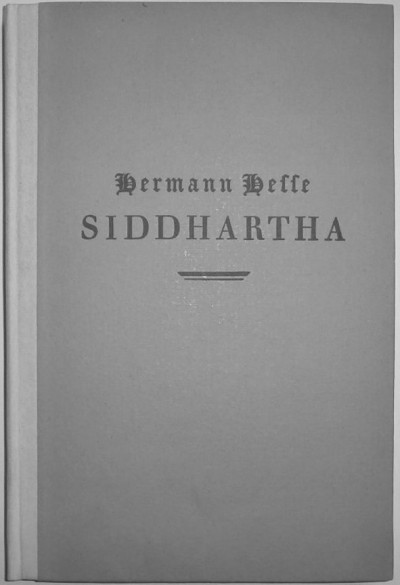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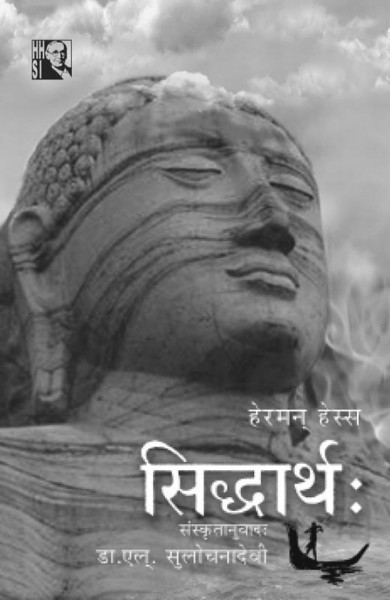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