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凯旋
美国仓皇撤兵阿富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主播不禁感叹“西贡时刻”重现。阿富汗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美国企图征服别国而失败的事例。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代表作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不止印度之行》(1969)一文中,将美国入侵越南和白人殖民者屠虐印第安人的史实联系起来,说:“印第安人的怨魂,至今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所以我们才对同样是黑发的年轻农兵痛下杀手。”
斯奈德此文是对19世纪的前辈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印度之行》的回应,甚至是批评。在《印度之行》中,惠特曼虽未言明“天命昭昭”,但他在诗中颂扬的正是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的理念:“这难道不是上帝自始的意图吗? /环绕全球,贯通寰宇。”这种对土地的征服意识,不仅体现在这位美国诗歌之父身上,也体现在其他美国诗人身上。人是历史的产物,惠特曼身上带有他生活的历史的特性,与其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1607年伦敦公司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从英国清教徒企图建造的山巅之城,到逐渐世俗化的西进运动,美国在土地这一他者身上,建立起他们自己虚幻的主体,割裂了自身与自身赖以存续的土地之间的共生关系。美国的侵略行为一再重演,其背后沉积的正是这种主宰与臣服、善与恶对峙的主客对抗思维,为了稳固自身“征服者”的幻觉,美国必须使陌生的土地成为有待征服的“邪恶”他者。
山巅之城与超验的自然
北美大陆对于早期英国殖民者而言,不是有羁绊的母国,而是需要征服的土地。早在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之前,英国殖民者们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就已经建立了定居点。对于他们而言,北美土地仅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用来种植收益可观的烟草和棉花。对怀揣崇高宗教信仰的清教徒来说,北美土地也并不是“流奶流蜜”之地,而是需要克服的恶劣生存环境。在残酷的生存环境里,人顽强地抗争并且不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借由克服恶劣环境,清教徒向上帝证明自身信仰的虔诚。这种对待土地的态度,在清教徒女诗人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在《观吾宅起火有感》一诗中,布雷兹特里特就再现了这种克服凡尘磨难,升华至圣灵之境的清教理想:“别了,我的钱财,别了,我的积蓄/这个世界我不再爱/我的希望和宝藏在天上。”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就称赞布雷兹特里特“克服了任何一个美国诗人所能克服的所有困难,写下了美国最早的诗歌”。早期的定居者对他们占有的北美土地持一种压榨和征服的态度,这片陌生土地对他们而言,是追逐利益的荒蛮地,是接受上帝考验的试炼场,而非家园。
在十七世纪末,清教传统逐渐式微。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急需新的、统一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去团结民众、抗击英国、实现独立。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人取代上帝,成了美国民族性建构的关键。但这种建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清教思想世俗化的基础上完成的。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布道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山巅之城”构想,即仿照基督教早期圣徒生活方式,在北美建立一个可以被世间所有基督徒仰望的宗教社区。这个宗教性的构想在十七世纪末演变成了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政治口号,建国的理想蓝图。侍奉上帝的“山巅之城”变成了以人为信仰的政治共同体。清教传统中为原罪所累的人,摇身一变,成了独立、自洽、天生高贵的大写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人为信仰的民族性建构,并未与上帝决裂,相反,它借用了神权。也就是说,美国建国的基石“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应该更准确地附加前提:在上帝的神圣法条下,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这样,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仅能获得凡人的拥戴,也预先获得了神圣的合法性。自此,凡以国家之名开展的任何扩张运动,都可以自称“天命”。
但对于人的推崇,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民族身份建构中,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土地仍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爱默生《论自然》中有关“透明的眼球”的论述相当经典:“站在空地上——我的头沐浴在宜人的空气中,升至无垠的天际——所有卑微的自我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什么都不是,却能看到一切。宇宙的本质一波波穿越我而过,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在布鲁姆看来,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品选段”。
布鲁姆对于这一选段的评判,初看确实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如果将它放置在大写的人和从属的土地的关系中去看,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确实非常典型地呈现了美国对待土地的态度。在爱默生的散文中,“所有卑微的自我都消失了”,“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他抬高的是人的位置。原先卑微的人类变成了与上帝同构的存在。而“我”原先站立的“空地”在“我”膨胀成宇宙本质后,被挤压的了无痕迹。爱默生沿袭清教徒升华“土地”的传统,在利用土地完成精神的升华之后,将被利用的土地置于隐形的位置。就像山巅之城的建立,尤为重要的是山巅的“城”,被忽视的往往是支撑“城”的“山”。从这个意义上说,爱默生的这个选段确实最能代表美国主体和北美土地之间的压榨关系。无论是升华土地取悦上帝,还是超越环境彰显膨胀的自我,美国主体将自身赖以存续的前提——土地,刻画成了一个从属的、割裂的陪衬。
移动的边疆与镜像的印第安人
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美国境内再无边疆一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西进运动确实已经推进到了美国陆地的尽头。然而,对边疆历史的复盘和衍生出的边疆传说,在西进运动结束后,仍影响并反映着美国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在《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一文中,美国西部史开山鼻祖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对西进运动的解读,就集中地反映了建国后美国对待土地的矛盾态度。特纳宣称西进运动不仅开拓了美国的疆土,同时洒下了民主的种子,让民主可以在原本荒蛮的地方,开出文明之花。特纳的这种解读,充斥着他作为白人历史学家,对印第安人被迫迁徙的“血泪之路”这一历史的美化。
但同时,这种解读也揭示了白人社群对待土地的双重态度:边疆土地首先是要从“荒野手中赢来的”,“荒野掌控这些殖民者”。人们必须要变成印第安人,“顺着印第安人的道走”才能在边疆这荒蛮之地生存下来。但随后,边疆土地在白人殖民者手中,又变成了滋养民主的富饶之地——“她将嫁妆赠与她的新子,这最偏僻处的新民主地,还施加影响使他高贵,对于自由狂热的爱涌上开拓者的心头。”特纳笔下的美国边疆是荒芜和富饶、落后和文明的矛盾共生体,这个共生体是不断变化的。又或者说,特纳讨论的边疆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借由不断征服“荒蛮”的边疆,扩大“文明”的范围,白人拓荒者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民族身份。这种美国主体性建立在对北美荒野的征服和改造之上。从某个方面来讲,白人对边疆的征服标志着美国真正的独立,“美国的民主不是来自理论家的梦想,既不是乘坐着‘萨拉-康斯滕德号’来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被‘五月花号’运送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并且在每一次接触新的边疆之时获得新生力量”。
但无论边疆如何具有流动性,土地依旧被美国主体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上,对它予取予求。美国根据自身的需要,不断变换对土地的态度,轮换对他者的对抗和认同关系。只要不是“我”的,那就必须要与之抗争,并将之视为荒芜、落后;只要是“我”的,那就是富饶、发达。无形中,美国在构建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在和土地的关系中,重演了宗教色彩浓重的主客对抗思维。
印第安人和土地是重像的关系。基于印第安人是土地原初主人这一现实,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再现的印第安人,是和土地对等的存在,也有一个从“异质”的野蛮到“同质”的高贵的过程,但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宿命,因为土地的主人只能是“我”——美国白人这一主体。在爱默生那里,自然和印第安人的重叠有着生动的体现:“森林之子(印第安人)看起来像是森林和湖泊的一部分。”无独有偶,在爱默生同时代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笔下,自然景色和印第安人也是融为一体的。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55)是一首传统的英雄史诗,不过主人公并非白人拓荒者,而是印第安战士海华沙。诗歌一开篇,就将印第安人、印第安村落、周围的土地糅合在了一起:“静谧翠绿的山谷/咏歌人那瓦达哈/涉水而居/环绕印第安村落/草地和玉米田一字铺开/远处的森林/丛丛柏树吟唱着歌/夏季青葱,冬雪白头/叹息不止,吟唱不停。”
在诗中,土地和印第安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交互、彼此交融的一体。此外,朗费罗在结尾处对柏杨拟人化的描写,模糊了婆娑的树和印第安人的界限,使土地和印第安歌手那瓦达哈共振联动,将土地和印第安人对等。在这种刻画下,土地与印第安人交织成了一体,所以也会“白头”,也会“叹息”。同时,印第安人也成了“土地”,在白人眼中,处于和土地同频的“他者”地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希恩(Bernard Shee⁃han)所言:“白人不会在印第安人和自然资源之间做一个区分,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
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中,毫不吝啬自己对印第安人的赞誉,这与他想要开创独具价值和特色的美国诗歌有关。但这种在当时看似创新的举措,在两方面落入窠臼:一方面,就像边疆异土一定要被征服一样,作为他者的印第安人在故事的最后,都要被白人征服。武力超群、对白人颇具震慑力的印第安英雄海华沙,最终也消失在了人界。另一方面,这种将印第安人刻画成“高贵的野蛮人”的笔法,也绝非“妙笔空前”。早在朗费罗之前,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笔下的印第安人就已经是矛盾化的善恶并存:“高贵”且“野蛮”的“人”。正如D. H. 劳伦斯所言,在库柏创造的狂野的印第安人身上,能看见“阿波罗的影子”。其实,这种从欧洲白人的视角出发,将印第安人刻画成“高贵的野蛮人”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一概念起源自蒙田(Montaigne),在启蒙时期,经由卢梭(Rous⁃seau)之手“发扬光大”。卢梭认为野蛮人虽然拥有的生活物资匮乏,但这种与世隔离的原始生存状态,也保留了他们天生的高贵。借此人人生来自有的“高贵”,卢梭和狄德罗(Diderot)试图消解贵族制存续的基石——血统论,以此去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将印第安人妖魔化的传统,出现得更早,同时深受白人主流文化拥簇。据考证,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1611)完成于北美第一个英属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后不久,剧中荒岛的原住民卡利班(Caliban)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人,后来成为白人主子的奴隶。种种证据都表明,卡利班其实就是在指代印第安人。
从野蛮的食人族到遗世独立的高贵先民,印第安人的形象转变,其实也重演了白人主体在对待土地他者时,所操纵的对抗和认同的心理博弈。如果主体需要,则主动凸显主体和他者的共同之处:原始的人类,同源的高贵。在美国,高贵的野蛮人概念最早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即印第安人的西迁运动已经完成的时候。但在印第安人西迁运动的早期,美国人还未成功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时,美国白人主体则着重突出“我”和他者印第安人的差异之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食人族。从这个角度来看,印第安人和北美土地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虽然曾被视为伊甸园和伊甸园里失落的先民,但都难逃被所谓的机器文明改造和清洗的宿命。移动的边疆和印第安人变动不居的形象,不过是美国白人主体在迎合自身需要时,建构出的虚幻的他者影像,实质依旧是为了迎合主体的剥削和利用:借由对边疆的征服,美国欧裔殖民者建构出脱离欧洲“母体”的美国性。
《彻底的礼物》与重新定居
1961年美苏瓜分全球地盘的冷战竞赛正酣,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鼓吹的其实就是全球版的西进运动:“我们一起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消除疾病、探测海洋……让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奉以赛亚的旨意。”正如蒂姆·迪恩(Tim Dean)所言,肯尼迪的演说预示了新的美国扩张时代,“扩张主义也不过是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的翻版”。在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上,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应邀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彻底的礼物》(1942)。这首诗歌应和的正是这种全球版的西进运动,或者说,弗罗斯特继承了美国对待土地的一贯作风——依靠征服他者化的土地来维系自身主体的意识。
在《彻底的礼物》一诗中,弗罗斯特将从印第安人那里窃取来的土地,包装成上天直接赐予的礼物,抹去印第安人的存在,只要白人愿意,土地就是白人的:“我们的克制使我们虚弱/直到我们发现,克制的正是我们自己/不肯献给生存之地/随即,在放任的当下获得救赎”。这种放任自己全情投入土地,并非出于“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是欲望驱使下对土地的血腥掠夺和疯狂占有。弗罗斯特在随后的诗节中轻描淡写这一史实——“战争功绩换来赠与契约”,同时他沿袭传统将逐渐西扩的土地刻画成“未被记载的、粗始的、未经提升的”。但弗罗斯特并非旨在回顾西进“光辉”历史,他更意欲顺应时势,所以这种粗始的、有待白人来提升的土地,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不远的将来:“她以前是,将来也是。”虽然弗罗斯特在多首诗歌中反思了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但他仍未跳脱出美国诗歌征服土地的传统,他仍将土地禁锢在低人一等的他者位置上。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则以更彻底的方式重塑了美国主体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在斯奈德笔下,土地终于剥离了他者的假面,开始以本真的样貌示人。斯奈德反对超验主义式的“寄情山水”,他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山水本真的样貌:“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此外,他将土地从从属的他者位置,拉回到与主体等同的同者地位。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解读杜甫的诗歌《春望》时,着意凸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意在说明“山河”和“草木”远超城郭的重要性。他提倡一种重新栖居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土地和世间万物,在他看来,都是彼此交融的共同体。在他的《致世间万物》(1999)一诗中,他集中地描绘了自己重新定居的理想:“我忠于土地/龟岛的土地/我忠于土地之上的一切生灵/一个生态圈/无限多样性/日光下/万物欣欣交融。”
斯奈德提出的重新定居的倡议,不仅事关人与自然,其实也意在修复美国一贯的主客对立的思维范式:“主体”与“他者”的善恶对峙、主宰与臣服。所以斯奈德才说:“没有天堂/没有堕落/只有风化的土地/飘荡的云彩”。那种继承自欧陆的主客对立的思维范式,在美国对待陌生土地的态度上重演了出来:无论是清教理想的山巅之城,还是在超验主义式大写的人下隐形的自然;无论是西进运动的流动边疆,还是全球版的西进运动——美国白人为了维护自身依靠征服土地而建立起的主体意识,将他人的土地视为亟待“拯救”的他者。斯奈德说的或许没错,美国不断挑起的善恶大决战,或许就是心中最初的他者阴魂不散。而重新定居,除了改变人和土地之间的压榨关系外,也意在颠覆“我”与他者的对抗意识,以一种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治愈“唯我独尊”的对抗思想:万物欣欣交融,谁的消逝都会削弱“我”。
在2021年拜登的就职典礼上,美国桂冠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我们攀登的山》,在诗中她反思过去的分离,呼吁将来的团结:“如果我们要配得上我们的时代/这份荣耀不能倚靠分裂的刀锋,要靠联结的桥梁/这样才能到达应许之地、攀上山巅,只要我们敢想敢当。”或许,这才是美国千禧一代真实的声音,它也诉说着美国年轻一代对于团结和集体的向往:“我们在悲伤中成长/在创伤中孕育希望/在疲惫中坚持/才能在将来和所有人共享胜利的果实/不是未来多坦途,只是未来的我们不再播下分裂的种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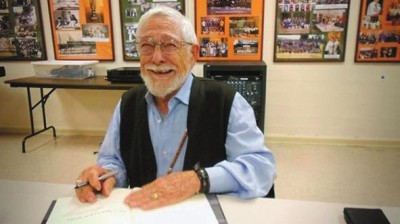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