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
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古尔纳1948年12月20日出生于桑给巴尔。1967年底来到英国,一开始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读书,1976年获伦敦大学颁发教育学士学位,随后在肯特郡多佛市的阿斯特中学任教。1980年至1983年回到非洲,在尼日利亚卡诺贝耶罗大学任讲师,同时攻读英国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获肯特大学哲学博士文凭,1985年进入肯特大学任教。目前是英国肯特大学英文系英语和后殖民文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后殖民写作等。他对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2018)、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等作家颇有研究,担任英国著名文学期刊《旅行者》(Wasafiri)的副主编,还主编了两卷《非洲文学论文集》(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1993,1995),出版了《剑桥萨尔曼·拉什迪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SalmanRushdie,2007)。
古尔纳迄今为止共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分别为《离开的记忆》(Memory ofDeparture,1987)《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多蒂》(Dottie,1990)《天堂》(Para⁃dise,1994)《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1996)《海边》(By the Sea,2001)《遗弃》(Desertion,2005)《最后一份礼物》(The Last Gift,2011年)《砾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来世》(Afterlives,2020)。
一、短篇小说
目前,古尔纳有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被查明建等译成了中文,收录于由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和英国的C.L.英尼斯在1987年选编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林出版社,2013年)中。另有一篇《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林晓妍译)是作为一篇论文的附录收于《中国英语教师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
《博西》《囚笼》是古尔纳的早期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早年经历以及少年心事的融入,但是已经展现出多头叙事的技巧、心理描写的功力,以及突破读者期待的写作路向。
《博西》采用了多头叙事:一是通过卡里姆的来信叙述非法移民的生活,一是通过哈吉的亲身体验揭示“暴力革命”给当地人带来的痛苦。
故事一开头,哈吉接到了卡里姆的来信,告诉他在外面的世界里小伙伴们的生活。卡里姆通过非法移民到了心目中的乐土,一边在工厂干活,一边在夜校学习。他迷上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什么书,因此拜托哈吉买了寄给他。小伙伴中,哈桑现在也逃来了这里,巴里斯特去了美国
波士顿大学读书,巴丘因为喝醉酒骂老板被踢出了办公室,拉希德的妹妹阿米娜现在成了妓女。
外面的世界并非乐土,故乡现在又如何? 哈吉看着卡里姆的来信,默默地怀念起死去的好朋友拉希德。
哈吉的思绪回到以前。他还有一个朋友尤尼斯,外号金属丝,得名源于人们认为他脑子里肯定有些线路没连上,里面都是些痴心妄想。金属丝跟哈吉说,他父亲在印度有大量的房地产,但还没有攒够钱回家一趟,所以金属丝要造一艘轮船,把他的家人都带回家。
而最好的朋友拉希德16岁丧父,拉希德不愿意离开家乡,因为他觉得不能丢下妈妈和妹妹不管,即使自己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意义。几年之后,哈吉和拉希德一起乘船出海,经历了一上午的历险后,拉希德跳进海里,准备游回城中。从行文推断,很有可能拉希德死在了海中。而对于哈吉来说,以后的日子生不如死。
当哈吉上了岸,回到镇上,却被人截住,用棍子、石头殴打,说阿拉伯人遭报应的日子到了。当哈吉清醒过来,流着血吃力地向前走,又被一群拿着大砍刀和枪的人拦住,说哈吉是军营里出来的民兵,不仅再次把他打得昏迷不醒,还往他身上撒尿。这呼应了故事一开头,金属丝躺在树荫下,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儿对着他的嘴巴撒尿。这不由使人意识到,金属丝说他父亲曾经在印度拥有大量房地产可能是真实的,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祖国,所以穷困潦倒,任人欺侮。
对于妹妹已经沦为妓女的亡友拉希德,哈吉只能在心中告诉他:我们看着邻居沦为乞丐,卖掉女儿换回鲨鱼肉,也会坐视不理,一笑而过。那些人专横地骑在我们头上,来教我们如何温顺。
这个故事很可能部分来源于作者古尔纳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1963年,古尔纳的祖国桑给巴尔脱离英殖民统治并和平独立几个月后,经历了一场革命,最终与坦噶尼喀合并成为坦桑尼亚。在阿贝德·卡鲁姆担任总统期间,用“阿拉伯人”这个标签剥夺、驱逐和谋杀了成千上万名对自身种族有不同看法的、认为自己是桑给巴尔人的人。
《囚笼》则描述了非法移民朦胧而无望的爱情。从故事内容推断,主人公哈米德应该是非法移民,所以他只能整天呆在店里,辛苦工作仅能换来三餐和在店住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像是被困在圈栏里;随后他坠入情网,也是画地为牢,这也是标题《囚笼》的双重含义。
哈米德十几岁来到这个小镇后,一直为老人法吉尔白天照看小店,夜里陪他聊天,并照顾入厕,法吉尔为他提供食宿。
当有一天一个名叫茹基娅的姑娘来小店买东西时,哈米德感觉她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自己的生活。店里的老主顾曼塞和茹基娅调情,茹基娅
皱着眉头走后,曼塞又对哈米德说,这个娘们儿肯定是个假装正经的妓女。后来茹基娅告诉哈米德自己在新开的赤道酒店做女招待。
为了不让茹基娅觉得自己粗俗,哈米德隔天就洗一次澡。每晚关上店门看顾过法吉尔之后,哈米德都去海岸边溜达一圈,实际上是幻想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和茹基娅在一起。每次茹基娅来店里买东西,哈米德都会多给一些;货品短缺的时候,还会从悄悄攒下的储备中取一些给她;偶尔还会壮起胆子恭维她长得漂亮。
《囚笼》也用了古尔纳一贯的突破读者期待的写法。曼塞断言“她肯定是妓女”,和茹基娅自承酒店女招待的身份,似乎都是“草蛇灰线”的伏笔;还有茹基娅可疑的动作——凑过身去接哈米德递过来的袋子,有好一会儿,她都保持着那个姿势不动,然后才慢慢往后退;以及茹基娅暧昧的话语,比如说“你总在给我东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报,那样的话,光靠这些小恩小惠就不够喽”,等等,似乎都暗示了茹基娅并不是那么纯洁无邪。
因此读者会疑心甚至认为,哈米德晚上在海岸边溜达的时候,有可能在站街妓女中看到茹基娅;或者到小说结尾会读到,茹基娅在酒店里堕落了。但是都没有。《囚笼》并没有采取出乎意料的欧·亨利式结尾,而是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哈米德不好意思地什么也没说,而茹基娅拿着买到的东西,瞥他一眼又冲他笑了笑,一头扎进了夜色中。或许古尔纳不忍打破哈米德青涩的暗恋;或许“扎进夜色”已经双关了茹基娅不太清白;但是也有可能这是两个异乡人都心存好感而羞于明言——《囚笼》这种不着一字的结局更具有多重性和丰富性。
《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讲述的故事是:一天下午,14岁的卡迪加和朋友们在家观看《走出非洲》的DVD,电影结束后,卡迪加向朋友们吹噓道:“我妈妈在非洲住过农场。”朋友们惊叹不已,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穆娜想去纠正,但又怕伤了女儿的面子,踌躇之中,思绪飞回到了自己14岁时。那时,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常年有头痛病,于是姨妈带她来到姨父所在的农场帮忙。她的失学问题根本无人关注,因为女性教育在当时根本不受重视。男女空间严格分开,所以小穆娜每天自觉地和姨妈待在一起。她住的是狭小逼仄、污渍斑斑的屋子,甚至邻居一位三十多岁的已婚叔叔,看来和蔼可亲,夜里却敲窗搔扰,甚至差点钻窗进来性侵她。《走出非洲》里有一望无际的优美自然风光、奢华的马车和瓷器、广阔无垠的农场、受人服侍的生活,作者却通过穆娜对非洲生活的回忆,构成了一种反写。《走出非洲》末尾凯伦说“我在非洲有个农场”,卡迪加说的是我妈妈“住过”农场,“住过”(Lived)和“有过”(Had)虽一字之差,但深刻地说明了非洲人本为这块大陆的主人,却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电影《走出非洲》的奢华和真实非洲的贫瘠,鲜明展现了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土著对“同一个非洲”的不同感受,格外启人深思。
二、长篇小说
古尔纳的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1994)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和科斯塔图书奖短名单。故事以优素福的视角进行讲述。12岁时,优素福被贫穷的父母卖给了富商“叔叔”阿齐兹作为契约劳工。阿齐兹的家里有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的
景色美如《古兰经》中描述的天堂。优素福跟随叔叔的商队到处游弋,深入到非洲国王查图的首都。美国文学评论家劳拉·温特斯在《纽约时报》上称《天堂》是“一个闪闪发光、隐晦的成长寓言”:在长达八年的商旅生活中,优素福从一个孩子成长为青年,而且经受了世态炎凉的磨炼。
由于《天堂》描写了不同空间的经历,如由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精英控制的沿海城市、在文明和荒野之间的内陆贸易城镇,以及非洲大陆,因此被评论家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黑暗之心》(Heart ofDarkness,1899)相比较。《黑暗之心》描写一名叫马洛的年轻人讲述自己在非洲刚果的冒险经历。由于船只在刚果河域搁浅,马洛改由陆路穿越茂密阴森的丛林抵达目的地(设在内陆的贸易站)。途中,马洛从同事口中听闻一个叫克如智的白人曾矢志将西方文明带入非洲,但却堕落成屠杀土著、掠夺象牙的殖民者。当马洛赶到克如智的象牙收集站并准备将他救出时,克如智已身染重病、心智丧失、奄奄一息。临终前,克如智托付马洛带回他个人丛林生活的手稿,并向马洛讲述了他在丛林中惊心动魄的经历,最后以“恐怖! 恐怖!”的喃喃之语,死在回程的船上。对于此,古尔纳本人在访谈中回应:“我不会称《天堂》是对康拉德《黑暗之心》的刻意改写,但有时人们可能会意识到其中的相似之处。”
《天堂》也从伊斯兰经典《古兰经》中汲取灵感。《古兰经》第十二章为优素福章。有一天,年幼的优素福梦见十一个星星和太阳、月亮向自己鞠躬,父亲告诫他不要把这个梦告诉哥哥们,以免遭到谋害。但是妒忌的哥哥们依然把优素福投进了井里,用假血染了优素福的衬衣告诉父亲优素福被狼吃掉了。来打水的旅人们救了优素福,却把他当做货物廉价地卖给了埃及人为奴。埃及人想把优素福当成义子并教他圆梦以及将来给他财产,埃及人的妻子却爱上了优素福,想要引诱他,优素福转身逃走,女主人从后面撕破了他的衬衫。优素福被投进监狱,后为国王圆梦得以洗脱冤屈,并被授予管理全国仓库的官职。后来,10位兄长前来仓库籴粮时被认出,经他一番精心安排,他们引双亲及胞弟前来团聚。团聚时,10位兄长皆俯伏向双亲和他叩头,此时,他才意识到幼年的梦兆应验了。在《天堂》的《血块》章节中,漂亮的奴隶男孩雷哈尼(优素福)面临着吸血鬼老妇祖莱哈的诱惑。就像在《古兰经·优素福》中一样,优素福是清白的,证据是优素福在逃离时,祖莱哈从背后撕裂了他的衬衫,但在这个腐败、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证据一文不值。
《古兰经·优素福》的结局是乐观的,《天堂》里的优素福却做出了一个懦弱的决定,放弃他所爱的女人阿米娜,绝望地加入了他曾鄙视的无情的德国殖民者。
第六部小说《海边》(By the Sea,2001),入选布克奖长名单、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小名单。讲述了二十世纪末,萨利赫·奥马尔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但他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遭到歧视和排外,以致于奥马尔很想知道移民官凯文·埃德尔曼是不是犹太人。移民局官员凯文·埃德尔曼厌恶地对他说:“先生,你们这些涌到这里来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危害。你们不属于这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点都不一样。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我们会让你们的生活
艰苦,让你们受气,甚至对你们实施暴力。先生,你干吗非得让我们这样做呢?”这一章的开头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这块太坚实的肉体应该融化、解冻并分解成一滴露水。”一般读者看到“犹太人”“肉体”,几乎第一反应这是莎翁名作《威尼斯商人》,但实质上这句话来自《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是哈姆雷特意欲自杀,因此自叹恨不得让自己结实的肉体消融。
《最后的礼物》(TheLast Gift,2011)被认为是古尔纳的巅峰之作。小说一开始,主人公阿巴斯因糖尿病和中风而倒下,回顾往昔,他认为这“一生毫无用处”,用录音的形式把自己的秘密作为“最后的礼物”告诉家人。阿巴斯向孩子们讲述他在桑给巴尔未提过的童年;讲他先使一位桑给巴尔女人怀孕,后秘密结婚,后来又与玛丽亚姆重婚的故事。他的妻子玛丽亚姆是个弃儿,直到她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34岁的阿巴斯并与他私奔。
作为在英国长大的移民后代,阿巴斯原名汉娜的女儿为了融入当地,改名安娜,与白人男友尼克住在一起,但她越来越发现他和他的家人有文化沙文主义,因此当她发现尼克有外遇时,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但是安娜为她的“移民”经历感到羞耻,她认为这段过去“可悲和肮脏”。儿子贾马尔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通过研究难民“绝望逃亡”的课题和加入伊斯兰阅读小组来应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
这部小说的独一无二性还在于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进行了评论,包括9·11、伊拉克战争和相关示威活动,以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
三、创作主题
古尔纳关注的主题之一是长期存在的种族间冲突和剥削问题,以及在印度洋沿岸东非部分地区发现的无数群体之间的混杂和容忍问题。他发现,欧洲人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以及持续的肤色和文化种族主义对非洲社会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地方争端都大。
古尔纳关注的主题之二是探索东非内部以及从桑给巴尔到欧洲(特别是到英国,其次是到德国)的移民、流离失所及过境等问题。古尔纳试图探索有些社会为什么无法阻止自己在几乎没有暴力手段的情况下被殖民者接管? 古尔纳毫不留情地批判英国社会及其机构普遍存在种族主义,而不是仅限于偏执的少数群体,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帝国主义历史。古尔纳注意到种族主义是通过“微侵略”、表面的幽默和暗地里的嘲笑来运作的,这些与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具有破坏性。
古尔纳指出那种表面看起来充满礼貌、善意、彬彬共处的“人间天堂”实质却是丑陋的,一些群体无情
地压迫其他群体,妇女和儿童尤其被父权制压迫得厉害,女性首当其冲受到侵害,因为她们往往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古尔纳振聋发聩地指出:“女人也是你男子气概的代表,因为你保护她的能力反映了你的荣誉和力量。能否确保你的女人不做她们被迫做的‘令人作呕’的事情,反映了你是否是一个合适的男人。”
古尔纳想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真的“融合”了吗? 在他的小说《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Silence)中,他建议大家将自己视为“我们一个整体”。可是放眼四顾,古尔纳悲伤地指出,实际上我们都被锁在各自的后院里。不光是学童分开上学,即使在成年人当中,这些群体中的某些人和其他群体的另一些人也根本没有什么交集。并不是比邻而居就是融合了。大家努力做了,但却没有真正做到。
惟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瑞典学院的授奖词——古尔纳的作品在不同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毫不妥协并富有同情心地道出了难民命运及殖民主义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9BZW16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A0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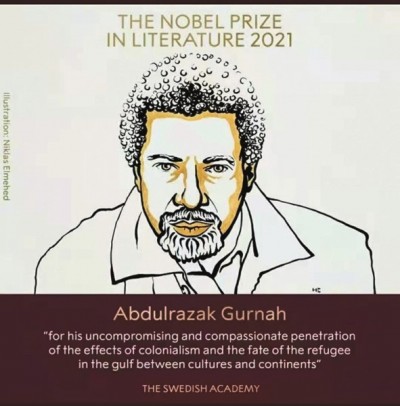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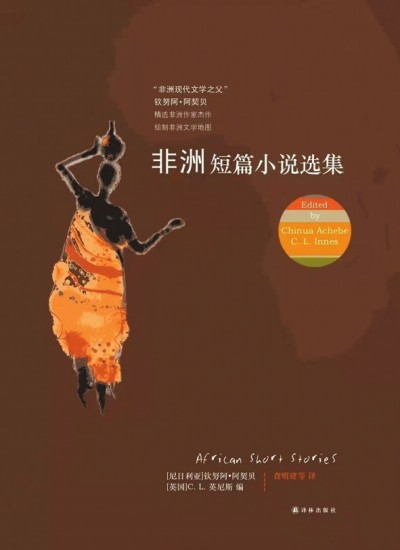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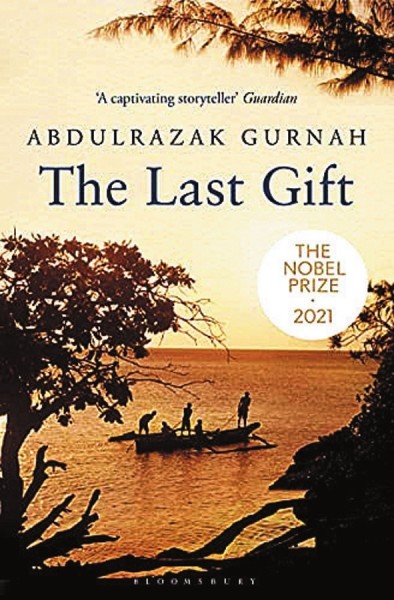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