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芳淑 赵霞
英国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汉语文学、包括汉语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创作、研究与译介。就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美学、儿童文学批评与阅读等被关注的话题,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赵霞与英国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蔚芳淑(Frances Weightman)展开了对谈。
中外儿童文学中的“淘气包”美学
赵霞:这些年来,淘气包一类的儿童形象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受到很多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有部著名的畅销作品《淘气包马小跳》。这部作品的英文版是哈珀·柯林斯出的,译作“Mo’s Mis⁃chief”。故事的主角是个男孩,名叫马小跳。英文翻译为Mo。我觉得刚开始,作者可能还没有完全决定要把他写成一个童话里还是现实中的角色,两者的边界有些模糊——马小跳出生就会跳的场景,就是这种模糊性的痕迹。后来她把它写成了一个现实题材的系列小说。很显然,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对于“淘气”一词有不同的定义。中国孩子身上被认为是越界的“淘气”行为,西方的读者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放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跟长袜子皮皮式的“淘气”相比,马小跳的“淘气”可能并不出格。故事里,马小跳常常打破规则,但最后还是会回到规则里,所有的顽皮淘气都是回归的必要释放。可能中国的家长也更愿意接受这样的故事。
蔚芳淑:说到《长袜子皮皮》,我想到了一部糟糕的儿童电视剧《讨厌的亨利》(Horrid Henry)。这部剧是由儿童故事改编的,很受孩子们欢迎。我只能看一点点,看多了就受不了。这部剧里没有一丁点儿关于做坏事的道德判断。讨厌的亨利好像有个他很不喜欢的兄弟,叫完美的彼得,但讨厌的亨利是主角,他处处让人讨厌。这背后的观念可能是,孩子们有他们自己关于淘气的各种想象。我不读这类书,因为我不给孩子买这类书。这类书跟《小屁孩日记》之类差不多,大概是以后者为蓝本的。
赵霞:我也正想提到《小屁孩日记》。你喜欢这套书吗? 它也是畅销书。
蔚芳淑:我女儿喜欢。我不喜欢。赵霞:我也不喜欢。有时候,孩子看到有个人摔倒在地,会觉得很好笑。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谈到文学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样的滑稽只是我们称为幽默感的表层,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幽默的水平线。我们首先要学会怎么笑,接着还得学着领会那种含蓄的、有意义的笑,这种笑带着复杂的情感;再接着是如何善意地笑。但在《小屁孩日记》里,只是你捉弄我,我捉弄你。父母孩子、兄弟姐妹、老师学生之间,大家互相捉弄取笑。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滑稽的效果,没有人彼此真正友善地相待。
什么是“淘气”? 或者说,什么是文学和艺术层面上的“淘气”?如果只是让小孩子跳来蹦去,做各种恶作剧,不一定是文学和审美层面的“淘气”。如何认识和表现这种“淘气”,我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文学任务。
蔚芳淑:是的。也许应该将“淘气”视作一种美学。不妨看一看“淘气”与“孩子气”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跟“幼稚”之间的联系。
赵霞:我喜欢“孩子气”这个词。说到“幼稚”,它常常跟一种儿童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即认为儿童是比成人更低的一种存在,他们尚不成熟。有一位英国儿童文学评论家彼得·霍林代尔,他曾经提出使用“儿童性”一词,以摆脱“幼稚”“孩子气”等词中传统的消极含义。
蔚芳淑:我认为“幼稚”和“孩子气”是不一样的。“幼稚”倾向于消极的评价,但我希望的是积极的评价。罗伯特·布朗宁说,天才总是带着点孩子气,却与幼稚毫无干系。在我看来,在孩子气这个观念里有某种童年观的理想色彩,就像“童心”一样。
赵霞:很多哲学家谈到过这种孩子气。比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智慧把我们带回童年。
蔚芳淑:我目前为一本书在写的章节,就是关于理想童年与现实童年的关联。我的基本想法是,尽管有时我们并非在指称孩子的意义上使用与儿童或童年有关的词,但即使这样,其中仍然有些微妙的内涵,牵涉到我们关于童年的观念。这其中的关系,跟我说的理想童年与现实童年的关系,“孩子气”与“幼稚”的关系,是同一个层面上的。
赵霞: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
要怎样写儿童
赵霞:不论在中国还是英国,都有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写到儿童角色或类儿童的角色,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现在跳到我脑海里的就是狄更斯的名字。美国文学中,比如马克·吐温,诗人如华兹华斯也多次谈到、写到儿童。中国文学中有余华、张炜、莫言、苏童等作家,也都在作品里写到儿童。如果把这些作家笔下的儿童形象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这些儿童非常多元,非常复杂。既有纯真、神圣的儿童,也有邪恶的儿童,还有处于两者之间、很难简单地说是好是坏的孩子。比如狄更斯的作品中,有些孩子永远都是纯洁的,不论你把多少罪恶之水倾泻在他身上,就像大卫·科波菲尔、奥立弗·退斯特。但也有邪恶的儿童。他们是坏孩子,因为被坏人和坏的环境给教坏了。
我们就来谈谈儿童形象的多样性。我想我们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天真的,善良的,他们代表了人性中善与好的一面。但读的作品越多,越会发现,这个形象其实很复杂。儿童性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词。
蔚芳淑:我认为就基本的人性观念而言,中国和英国文化都是一样。一方面,像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果有人看到一个孩子掉进井里,一定会想法去救这个孩子。这意味着善良的天性。但同时,荀子则说,人性本恶,他使用另外的隐喻来谈论人性的自私。因此,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需要经历塑造。我认为这两者各有道理。中文有“成人”之说,儿童是“未成”之人,换句话说,他/她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需要经受教育,长大成人。这个二分法,中西方都一样。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儿童也常被表现为社会的弱小者和易受害者,还有就是那些坏孩子。
赵霞:比如《雾都孤儿》里的南茜。蔚芳淑:即使这些坏孩子最后没有变好,小说表达的意思也是,他们是由于社会的环境才变成这样的。他们偷窃,是因为有人教他们偷窃。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天生就坏,而是社会的受害者。奥立弗·退斯特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孩子,奥立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淘气”话题的一部分。他不遵守孤儿院的规则,开口讨要更多的粥,导致自己陷入麻烦。但读者肯定不会认为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他挨着饿,只是想多喝点粥。也是他的天真和善良,还有常常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无知——使他在遇到那些小偷时,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做的是什么。
赵霞:有一点值得思考: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挥动童年这个符号的象征,使得关于社会的批判显得更猛烈,更突出,更令人印象深刻。通过强调儿童的天真,落在儿童身上的恶就格外让人感到难以容忍,就像你之前提到的那些现实案例。如果儿童由于被恶包围,最后成了坏人,这比其他情形更让我们觉得不能容忍。反之,如果想要表现我们社会和天性中的善,通过书写儿童或儿童式的纯真,也会令人更加印象深刻。儿童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及、塑造、建构的历史,也就是我所说的童年美学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这种美学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但其历史的线索始终在那里。不论在“童年的发现”之前还是之后,文学从未放弃这种对童年的书写,想到这一点或许令人鼓舞也引人深思。文学永不会放弃对此的表现。我们总是会将童年纳入我们的审美世界,用以表达特定的观念、情感、哲学。这里面包含着童年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意义。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至少对于文学而言,值得深思的是,通过将童年作为一种美学的符号,一个重要的美学因素,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 或者说,我们将会得到什么? 你正在研究的课题包含中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以及某种类儿童的品质,比如你论及的中国文学中的“痴”,在我看来就与儿童有关。事实是,我们视童年的观念为文明的一部分,也视其为我们审美情感的一部分。
蔚芳淑:在我看来的确如此。当我们谈论美学,谈论审美的纯度和高度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或转向儿童的观念。撇开社会和文化的包袱,当我们抽象地思考,在审美层面最无所不包的观念就是新生的婴儿。个体出生之后,贫穷啊,环境啊,各种问题才接踵而来。但在出生的那一刻,一种与新生的婴儿关联在一起的美学理想,存在于全世界。当你成为一个母亲,就能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母亲一起用母亲们的方式讨论问题。讨论的内容当然千差万别,养育孩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元素——孩子的出生与养育——把我们结构为一个拥有共同经验的共同体。我认为这就是童年美学的其中一部分价值。另外,我们刚才说到的作家,大部分是男性,他们对童年的看法,可能跟女性也有不同。我们没有谈到性别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她们写作的时间却最少。她们耗费很多精力照顾孩子。这是不是意味着,母亲们没有时间反思创作活动? 因为如果你每隔三分钟都得赶去处理一件孩子的紧急事务,显然没有时间回头思考。在英国,大部分脱口秀喜剧演员都是男性,他们都在脱口秀里大谈当个爹有多好笑。女性就鲜少如此。
推动儿童的批判性阅读
赵霞: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儿童观念是,儿童是纯洁的,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纯洁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把那些最纯洁的事物交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围绕着儿童的阅读,我们会设置各种审查的界限和警卫。
我记得你曾谈到教导孩子批判性阅读的重要性。
蔚芳淑:你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文学中的刻板印象可能比性和暴力问题更糟糕,因为性和暴力的问题往往很明显,容易辨识。孩子们常常也知道,这是少儿不宜的。但刻板印象的问题就比较隐蔽。在我看来,这种隐性的问题实际上更危险。比如儿童文学中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还有国家民族的刻板印象,当这些作品翻译到国外时,这些问题也被携带了过去。关于批判性阅读的培育,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想老师或者父母可以做些有趣的尝试。比如,阅读《亨赛尔和格莱特》《小红帽》这样的故事,可以让孩子们试着把故事里的女孩想象为男孩,从后者的角度重写这个故事。
改写之后,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为什么他们要做出相应的改动,为什么你觉得一个男孩会这样那样去做? 我的经验是,孩子们非常乐意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且可以谈得相当深入。因为还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女孩男孩的区分:女孩喜欢粉色,男孩喜欢蓝色;午餐时间男孩可以踢足球,他们在操场上玩得更多;为什么一个女孩想踢球,男孩们却不会传球给她?等等。这就是关于男孩女孩之间的平等性的讨论。成为一个女孩或男孩意味着什么?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样的讨论。
我认为在这里,大人的角色很重要。要是刻板印象在故事里扎根很深,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乍看之下不容易察觉,就需要成人来帮忙介入指出。成人也要鼓励孩子的批判性阅读。
赵霞:我想到的是批判性阅读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对文学的清洁或消毒,不是通过文学实现某种彻底的公平——这永远是不可能的。文学中永远会有不公正的现实存在,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如果儿童文学作品只表现男孩女孩的平等,反而成了另一种谎言。当你了解得更多,也许就能做得更好,或许那才是批判性阅读的最终目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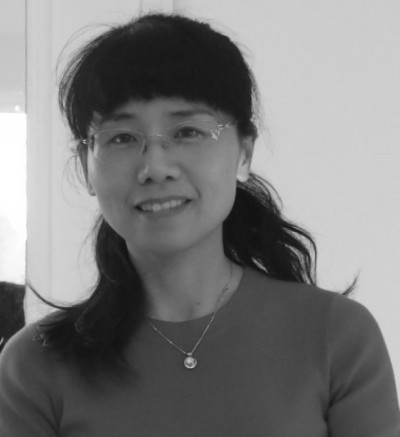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