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出发点都被德吕纳归结到了一点上,那就是一切以艺术创作为目的。他名副其实地为艺术付出了全部:物质、精神、情感,以及自己的和他人的名誉。
即使拿如今娱乐圈流行的“黑话”去套理查德·瓦格纳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他是最早开始有意识主动营销自己的艺术家之一,且在这方面也是大师中的大师。炒话题? 谁还没几个亲近的媒体。做数据? 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门票从第一届开始可就是预售的。卖周边? 看看歌剧院旁边的瓦格纳同款养活了多少小商小贩。如此种种当今称作“立人设”的行为,在当年有个更加高大上的名字:艺术家神话。于是各路绅士淑女们纷纷拜倒在他给自己贴的标签之下。
然而经历过现代娱乐圈洗礼的我们都清楚,人设必定是虚假的,就像神话成不了现实,即便它们经历了第二任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和各路“瓦粉”们的竭力堆砌。我们不妨来看看,同样是音乐家的乌尔里希·德吕纳是如何亲手对他深爱的大师“扒一扒”的。
无论以哪个时代的标准来看,瓦格纳与第一任妻子的邂逅都堪称浪漫的一见钟情:初出茅庐的年轻音乐家看到夸大其词的招聘广告前去应聘,大失所望之下正欲转身离去却在转角遇见年轻貌美的女歌手,“在这片轻浮而低俗的乌云中,她真的像是仙女一般出现”,瓦格纳在日记中写道。于是他为了她留了下来,如同浪漫戏剧中一样每天站在阳台下对她说晚安;她也不嫌弃他丹毒发病时浮肿丑陋的脸。爱情的开花结果水到渠成。但是对于这对贫穷艺术夫妇而言,生活不只是舞台上的辉煌与落寞,还有饿肚子时没有东西可煮的一锅锅徒劳烧开的白水。两个人终于发展成一对怨侣,明娜曾尝试离开瓦格纳,瓦格纳的回忆中也再没有了对青年时代爱情的热烈怀念,只剩下诋毁和扭曲。
在这样的背景下,瓦格纳的第二段婚姻似乎是多重背叛的结果。他与明娜从未正式离婚。而在柯西玛这边,无论是她的父亲李斯特还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冯· 比洛,都是瓦格纳的挚友,都曾在他落魄时给予经济和精神上的无私援助,而柯西玛和瓦格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甚至还顶着比洛的姓氏。面对纷纭的“谣言”,瓦格纳竟恳请路德维希二世出面以国王的尊严来担保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纯洁”的。愤怒的李斯特杀向瓦格纳的隐居地,但是瓦格纳给他看了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于是李斯特把它在钢琴上弹了出来,然后他沉默了,离开了,默认了他们的荒唐事。“李斯特来访:可怕,但可喜。”瓦格纳写道。
瓦格纳的一生之中当然不可能只有两个女性,在明娜和柯西玛之间还有玛蒂尔德、朱迪、杰茜等等,然而毫无例外,他与她们的感情都没有实质性结果。艺术家便天然地豁免于道德评判吗? 我们的作者德吕纳认为,与其说瓦格纳离不开爱情的滋润,倒不如说他需要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拿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若力比多无处释放,自然便会转化为创作力。于是越是撩拨更多的女人,他的创造力便越是会爆发。《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还有《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若干段落,无一不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与如今遍地黄金的娱乐圈不同,在19世纪和更早的年代,贫穷才是艺术家的标配。伟大如贝多芬都少不了一个贫贱不能移的设定。诚然,作曲家这种幕后工种在那时候是不为人所知的,音乐界能靠演出赚大钱的是克拉拉·舒曼、帕格尼尼这种演奏家或歌唱家,作曲家甚至没有版税收入,只有固定的一小笔报酬,如果某位作曲家能从一部爆火的歌剧中分得2%的利润,在当时已经是闻所未闻了。瓦格纳的同行中甚至有人因请不起医生而病死。因此,瓦格纳在自传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的贫困,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或许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瓦格纳这个觉醒了的抗争者明确地将自己贫穷的原因归结为“艺术界的犹太人”的残酷剥削。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诚然,瓦格纳前半生的漂泊完全是贫穷的结果。他因躲避债主的追索而逃遍全欧洲,在巴黎不得不变卖所有家具来维持生计,在维也纳差点因为还不上债而被扔进监狱。就在他因贫穷而对整个世界失去信念的时候,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如天神般的突然降临给他带来了救赎和金币。他诅咒犹太出版商对他的剥削,咒骂他们将他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作抄写乐谱的小工来使用,还压低、拖欠工钱……然而德吕纳在《瓦格纳传》中仔细算了一笔账:仅仅是瓦格纳在巴黎从事乐谱改编和抄写的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他的总收入就达到6750法郎,约等于现在的12万到15万欧元,这是当时一名音乐学院教授年薪的两倍,普通音乐家的三倍,普通劳动者的将近十倍,也比工程师、中学校长、法官等的收入高得多。单从收入上来说,瓦格纳是完全跟贫困不沾边的。那么,他是如何在同样的时间里不仅花光了这么多钱,还欠下了几乎同样数额的债务呢?瓦格纳的日记中有着些许蛛丝马迹。他曾经记录下自己的购物清单:24米丝绸,18米锦缎,35米细纱,4副小羊皮手套,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笔花费。钱不够的时候就去借高利贷,欠债还不上就去借更多的债,堪称一个19世纪的消费主义受害者。但是艺术家的事,算消费陷阱吗? 在瓦格纳看来,这些高级纺织品是他生活之中,尤其是工作之中不可或缺的。当他的创作力旺盛的时候,他需要手里摩挲着悬挂在墙壁上的丝绸,脚下踩踏着天鹅绒的地毯,好维持大脑的飞速运转。哪怕是穷得真揭不开锅,也要第一时间把赚到的钱全部花出去再说。真穷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对创作更是利好了,毕竟文章憎命达的道理不止我们才懂。每一个在穷困潦倒时迸发出的灵感,最终都会在奢侈品的簇拥下绽放出最艳丽的作品之花。那又何必在自传中拼命哭穷呢? 要知道,这部自传一开始可是完完全全的定制版,最初的目标读者有且只有一位,那便是路德维希二世国王陛下。把自己描写得越凄惨,国王给钱就会越痛快不是吗?
如上所述,瓦格纳将自己早年的穷困潦倒归结为“艺术界的犹太人”剥削压迫的结果,他为此专门写作了一本题为《音乐中的犹太性》的小册子,宣称要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艺术界,甚至在他的多部代表作如《尼伯龙根的指环》《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之中,也不乏对犹太人的含沙射影与指桑骂槐。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谓深远,因为他的狂热粉丝之中至少有一个只从中看到了“反犹主义”四个大字并立誓将其在现实世界中推行。
然而,德吕纳提醒我们,不要以政治的标准去评判艺术的成就,毕竟瓦格纳无法预知若干年后会出现一个叫作希特勒的人,而他的“反犹”一开始是有着具体目标的,那是一个确定的人:贾科莫·迈耶贝尔。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个名字陌生,但是在当年,这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横扫整个巴黎歌剧界的大人物。他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瓦格纳并非他唯一提携的后进,但或许却是唯一将他视若仇寇的晚辈。初到巴黎时,那些后来的瓦格纳瞧不上眼的改编工作正是迈耶贝尔介绍给他的,而这成了瓦格纳在自传中攻击他的口实。瓦格纳宣称,迈耶贝尔如此做并指示那些犹太出版商克扣工钱是因为嫉贤妒能,自己的原创作品在巴黎无人问津是因为迈耶贝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处处设障,甚至后来在柏林、在德累斯顿的失败都可以归结在迈耶贝尔身上,报纸上对自己的批评也是迈耶贝尔煽动那些犹太媒体人的结果。
但是种种证据表明,瓦格纳对迈耶贝尔的指控实属无中生有。他曾经谦卑地宣称,“我是迈耶贝尔的学生”,最终却在迈耶贝尔死后已经无法自辩的时候对之恶语相向。或许果真如德吕纳所言,瓦格纳此举只是在一个剧变的社会中无措的反应,他将新兴的现代性与金融资本主义误称作了“犹太性”并发出了错误的号召。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瓦格纳为自己打造的神话中,身为英雄的自己需要一个亟待打倒的劲敌,敌人越是强大,则英雄越显伟大。那么还有谁比当年的歌剧界“老大”迈耶贝尔更适合担当这个敌人的角色呢?再者,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假想敌,也是瓦格纳刺激自己创作力的手段。
于是,在我们简单归纳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到,瓦格纳的出发点都被德吕纳归结到了一点上,那就是一切以艺术创作为目的。他名副其实地为艺术付出了全部:物质、精神、情感,以及自己的和他人的名誉。如果我们在此时想起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瓦格纳的做法是否也称得上某种异化呢?
德吕纳的这部传记不止于对瓦格纳私生活的挖掘,而是力求通过对真相的还原来理解瓦格纳各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脉络,以达到对它们更好的理解与阐释。在此情况下,作者以音乐家的专业背景对瓦格纳各部歌剧所做的解读便显得尤为深刻了。
无论如何,凡有婚礼处必有瓦格纳的进行曲,艺术是不朽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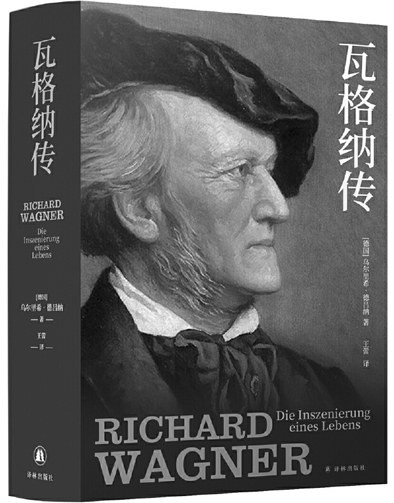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