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韦斯特,美国最出色的高海拔登山家之一,美国第一个无氧登顶所有十四座8000米级山峰的人。安纳普尔纳峰,是被他征服的第十四座,他对这座高峰的兴趣是从阅读一本书开始的。在这本《攀登者》中,我们将看到攀登不只是勇敢者的游戏,还将分享到勇士确立目标、制定计划、规避风险的智慧,还有,他深爱着的家人们。
我和维卡在顶峰上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比我平常在8,000米级山峰的顶峰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但是如果我曾经想要多享受一会特殊时刻,那肯定是现在。我们俩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这座山无法避免的危险,它很可能是一座我们永远无法登顶的雪山。我们经常谈到我们多么渴望登上安纳普尔纳,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功登顶,那一定是我们在所有世界最高峰的攀登行动中最为神奇的成就。对我而言,这一刻不仅意味着又征服了一座8,000米级山峰,也消除了五年来对自己的怀疑和担心,十八年的夙求终于圆满完成了。
当我在顶峰上眺望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正看着的,与五十五年前呈现在赫尔佐格和拉什纳尔面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壮丽景色。我顺着山脊的两边往南坡下面的悬崖望去。伯宁顿的团队1970年在那里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攀登,那里也是1992年拉法耶与死神殊死搏斗的地方。
三个意大利人——丹尼尔·贝尔纳斯科尼(Daniele Bernasconi)和两个马里奥[马里奥·马瑞利(Mario Mer-elli)和马里奥·潘泽里(Mario Pan-zeri),我们称他们为马里奥兄弟]一个接一个慢慢地走向顶峰。当我和维卡穿过顶部山脊时,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小山丘,以确保我们登上了最高点。现在意大利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正如后来加入我们的马里奥所说,“我们必须为霍利小姐这样做”,我们握手并互相拥抱。
当我们下山时,典型的午后云层开始滚滚而来。不久我们就陷入了四周白茫茫的境地。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风暴,不是像1992年在K2上使我们下山变得非常危险的那种风暴——这只是喜马拉雅山脉常见的午后天气。同样也下了几英寸厚的雪,我们意识到下面在地形相对平缓处的固定路绳可能都会被积雪所覆盖。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上山时从固定路绳最高锚点处的冰锥上方开始插的柳木条,被证明对于我们不会在下降途中迷失方向是至关重要的。丹尼尔是三位意大利人中最强壮的,他与我和维卡一起下降,而马里奥兄弟则落后地越来越远。
在第三营地,我没有足够的柳木条剩下来,所以在相对没有特征的山顶雪地上,我不得不将它们插得相隔很远。现在,我们三个人并排分散开,就像救援人员在森林里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在雪地里往下走,寻找下一根柳木条。在某些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们在冲顶途中留下来的冰爪痕迹,因此知道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风已经将我们的足迹清扫干净,或没入到小腿那么深的雪已然将斜坡覆盖了。
每一次我们都会在找到的柳木条处汇合,然后我们会再次尽可能远地分散开——但是仍保持在一片白茫茫中我们可以互相看得到的距离内——然后缓慢向下走,寻找下一根柳木条。不用说,这是缓慢又细致的步骤。当云层翻来覆去的时候,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我还没有开始惊慌,仍然觉得很有信心。只要我们有耐心和有条不紊,我想我们应该可以通过由柳木条标注出的那道线来找到下山的路。
当我们艰难地蹒跚下山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随时都需要可以看到上一根的柳木条。当它几乎快在视线中消失时,我们会停下来并向前看,来寻找下一根柳木条。如果我们找不到下一根,我们会坐下来等待——虽然这样的延迟是令人发狂的,而且我们变得更冷——直至能见度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在还没有找到下一根柳木条的情况下又看不到上一根,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迷路了,无法在一片雪白没有任何特征的世界中保持下山的正确方向。
这时安纳普尔纳开始逗我们玩了。在冰川上方固定路绳的最高处,我们用冰锥来做固定以保护锚点。在那上方几英尺处,我在一个从上面很容易看到的位置插了一对柳木条,来标识这里是通向一系列固定路绳的通道,指引我们轻松地回到三号营地。下午六点左右,天色开始变暗,我发现了那一对柳木条,方才感到如释重负。我现在知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转过一个小角落,那里会有一只冰锥,冰锥下面拴着固定路绳,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回营地的生命线。
我们翻过了拐角。“他妈的怎么了?”我低声说道。没有路绳,没有冰锥——什么都没有。有那么一刻,我以为它只是被新雪覆盖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那是解释不通的。我们特意将绳索固定在高处以防万一。难道我们是在上一根柳木条和固定路绳锚点之间那段微小的距离上拐错了弯?
我们记得西尔维奥曾说过,也许需要拆卸一些高处的固定路绳去加固下面某处通道。那天早上因为他的脚太冷而无法继续冲顶,他只能回头下撤了。他是不是将最上面的路绳拆卸下来,以便在下山的路线上使用? 如果是这样,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让我们这五个人陷入困境?
我在探险结束之后与西尔维奥联络。他发誓他没有碰固定路绳,而我也相信他。最后,丢失固定路绳的事件仍然是一个谜。
丹尼尔之前曾经爬过这座山,当时他的团队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慢慢将他们的营地推进到了比“镰刀”还要上一点的地方。现在他说:“我知道怎么走。跟着我。”天黑得很快,不到一小时之内,我们将会陷入一片黑暗中。我们打开了头灯,紧跟着丹尼尔。幸运的是,云已经散去。现在天空晴朗,风也停歇了。但是,唉,月亮没有出来。丹尼尔说,“我们需要从这个山坡走下去一段路”。但是我和维卡感觉不对。最糟糕的事就是我们快速下山,在没有看到帐篷的情况下错过了三号营地,然后发现自己被困在北坡某处不可辨的斜坡上,完全脱离了我们的登山路线。
维卡首先发言。“我不记得攀登过那里,”他谈到丹尼尔判断的路线,“艾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向上走一段然后向右横切。”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都不知道马里奥兄弟就在上面的某个地方,跌跌撞撞地沿着我们的路线(我们希望是如此)下山,但一切已经被降临的夜幕所包围。马里奥兄弟是一对经验丰富的老登山队员,而且他们一起攀登了很多次,我们认为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通过引导下降和开路,我们也在帮助着他们。
我真的很累。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找到帐篷,然后进去睡觉。我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我相信维卡天生敏锐的找路能力胜于丹尼尔不可知的预感。我和维卡偏离开丹尼尔判断的线路,先向上爬了一段,然后开始横穿。丹尼尔突然也有点不确定,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跟上了我们。我的胃突然收紧了。安纳普尔纳似乎不准备放过我们。
与此同时,在班布里奇岛上,宝拉正经历着我们婚姻生活中最严酷的考验。我会定期从安纳普尔纳的大本营使用我们的卫星电话与宝拉通话。而且我同意把电话带到山上,这样我就可以在我们出发前往山顶的时候打电话给她,然后在什么时候再一次打电话给她——如果那时我们成功地站在了顶峰之上。
尼泊尔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大约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当我们5月9日第一次到达三号营地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宝拉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三点出发冲顶。所以第二天下午三点,当她在忙于她的日常活动时,她敏锐地想象着我在安纳普尔纳海拔22,500英尺的高处正在穿衣服,准备在黑暗中向顶峰进发。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座8,000米级山峰,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安纳普尔纳,现在这些熟知的进程让宝拉更加忧心忡忡。
她曾经问我多久才能到达顶峰。我当时不得不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所以我说大约八个小时——严重低估了最后一段攀登的难度,最终我和维卡花了十一个小时才成功登顶。因此,当下午和傍晚的时光慢慢流逝,宝拉在家里想象着我离顶峰越来越近了。然后,大约晚上八点,电话铃响了——这并不是我应该登顶的时间。
“我们没有登顶,”我不得不告诉她。“风太大了。”
“哦,太糟了,”她回答。“我以为你在路上。”
回想起来,也许我应该在安纳普尔纳午夜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当时我们在三号营地醒来并决定不冲顶。相反,我一直等到了早上,在我们睡了宝贵的几个小时迷糊觉以后才告诉她。宝拉没有生气——只是失望。
第二天,我们又是沮丧地重复第一天的情况,风还是太大了,无法进行冲顶尝试。一再延期的不确定性开始让宝拉抓狂。我自己也有点想发疯,想着这天气是否会给我们一个到达安纳普尔纳峰顶的机会。
然后,在5月12日早晨,当我们向意大利人大喊:“我们动身吧! 就是今天了!”在离开营地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拿起卫星电话打给宝拉。而那时电话居然停止了工作,这让我感到极度烦恼和沮丧。
在大本营还有另一部可以用的卫星电话,所以我们通过无线电告诉在大本营的吉米我们要出发冲顶,同时我让他打电话告诉宝拉。吉米这样做了,最后宝拉知道我们已经在冲顶的路上了。
宝拉得到消息的时间是在班布里奇的下午三点。一个下午过去了,随着太阳的落山,夜幕降临了。我说过大约八个小时就足够让我们完成登顶。到晚上十点,她几乎是屏住呼吸在等待着电话。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接着是午夜。吉米可以用卫星电话打给她,但是她却不能给大本营打电话。她所能做的只是等待。
一直到三号营地,我都带着我们的卫星电话,维卡带着对讲机。当我们在那天早晨出发时,维卡没多想就把对讲机塞进了他的背包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非常清楚宝拉正在经历着什么。现在至少是上午十一点了,是我们离开三号营地八个小时之后,而我们离峰顶还远着呢。
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停下向大本营通讯更新我们的进展,这样吉米就可以打电话给宝拉告诉她我们一切顺利,只是比原计划晚。但与此同时,维卡正处于领攀位置,虽然我可以跟上他的速度,但我无法赶上他。我们正全力以赴地攀登,为了用对讲机而示意维卡停下来似乎太费劲了。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里,我只想继续向上攀爬。我和维卡是如此投入,我们甚至都没有停下来拍一张照片。在寒冷和大风中,这样做会很容易导致手指冻伤。对我来说,这时即使是吞下能量胶或者喝水都是过于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更不用说拿出对讲机联系大本营了。我和维卡此时此刻都需要完全专注于攀登。然而,我无法将宝拉的焦虑从脑海中摒除,我试图通过某种心灵感应向一万二千英里外的她提出我的请求:宝贝,不要太钻牛角尖了。你知道八小时只是预测。你知道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然而,在大本营里,吉米本人开始担心了。在某个时候,他打电话给宝拉。“他们凌晨三点钟离开的,”吉米告诉她,“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宝拉知道攀登8,000米级的山峰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我们总是同意“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除非你听到最坏的消息,否则就假设是最好的。但吉米的电话打击了她。
宝拉上床睡觉,但她当然无法入睡。夜晚是一个人的想法最黑暗、最糟糕的时刻。她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想象着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她的想象也越来越深入到最糟糕的情况上。一定出了问题,她很痛苦。艾迪不会回家了。
宝拉是个未亡人。她在黑暗中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试图想象着一个没有我的将来。我会好起来的,她给自己分析。我会卖掉房子。我会搬到离我的家人更近一点的地方。
但是,正如她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在凌晨时分,她的情绪在伤心欲绝和对我选择这个职业而感到极端愤怒间摆动。愤怒的声音在一声巨响中传来,直指世界另一边的我:该死的! 我怎么告诉孩子们?
宝拉排练了好几个小时怎么做。她会把孩子们集合到她的床上,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不会再回来了”这样可怕的话。但她所能想象的只是吉尔瞪着大眼睛盯着她,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说:“妈妈,你在说什么?”
凌晨三点左右,吉米很开心地告诉宝拉我们已经成功登顶,但宝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却迅速消退了。她知道攀登只完成了一半。如果我们花了十一个小时才登顶,而不是我预测的八个小时,那么下山又会发生什么? 在她余下的不眠之夜里,各种可怕的场景又重新占据脑海。到了早上六点,当早晨的太阳在地平线上方照耀着普吉特海湾时,她知道安纳普尔纳已经夜幕降临,而我们还未返回到三号营地。
事实上,在那个时刻,维卡、丹尼尔和我还在山坡上用前照灯到处寻找那根可以带我们回到帐篷的救命的固定绳索。我们仍然不知道马里奥兄弟在哪里,但毫无疑问他们从山上更高的某处在连夜下降。幸运的是,天气持续良好。当我们跟从维卡横穿斜坡时,记忆开始变得有点熟悉了。我认为从大范围来说,我们肯定是处在正确的地方,现在我们可能比最高的固定绳索位置要低一些,就是那根我们找不到的绳索。因此,我觉得那段绕在冰塔上通往三号营地的固定绳索可能就埋在附近,被一层薄薄的新雪覆盖着。
现在感觉不像是生死攸关的情况。天气很好,我们在海拔大约23,000英尺之上,而不是在28,000英尺的珠穆朗玛峰,不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已经露宿了。但这会是一个悲惨的夜晚。我现在想要的是在三号营地的舒适帐篷里,但最终是回到班布里奇岛的家里。
当我们开始横穿时,我每走一步都拖着我的冰爪。仅仅几分钟后,我的右侧冰爪刮到了下面的东西。“维卡!”我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找到了固定路绳!”
终于可以回家了——一段段首尾相连的固定路绳,将我们直接带回到了营地。只要将绳子握在手里,我们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下山。然而我们直到晚上十点才到达帐篷。我们几乎没有停顿过(除了在顶峰上的一个小时),连续十九个小时在上山下山。我很少像现在这么累过。
我们一走进帐篷,我就说:“维卡,把对讲机给我。”我按下发射按钮,呼叫吉米。“大本营,大本营,”我咆哮道,“老鹰着陆了!”在大本营庆祝一番后,吉米再一次打电话给宝拉。
我仍然有足够的力气来写我的日记,全部都是大写的:“今天我们成功了!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那天晚上马里奥兄弟没有回来。我很担心他们,但丹尼尔说,“别担心,他们会没事的”。
事实证明,在山顶的雪坡上,马里奥兄弟在黑暗中磕磕绊绊下山,其中一人踩破了一座雪桥,掉落在一个小的冰裂缝中。他自言自语地说,嘿,没有受伤,而且这是一个露宿的好地方。马里奥兄弟在冰冷的洞窟里度过了一夜,还算相对舒适。他们的露宿复制了1950年的那次偶然事件,当时四位法国登山者在风暴中绝望地下山,基本完全迷路了,在拉什纳尔堕入冰裂缝后,他们四个人就在冰裂缝中熬过了痛苦的一夜,但幸存了下来。
早上,当我和维卡躺在我们的单人睡袋里时,我突然闻到香烟的味道。“马里奥兄弟回来了”,我轻笑道。这些大胆的意大利人在上山下山时都抽很多烟,当他们安全抵达三号营地,就有忍不住点燃香烟的冲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看起来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尽管他们是在高海拔的荒野露宿了一晚。
我们还没下山。我害怕最后的一次穿越。我们进入帐篷后,煮了几罐温暖的果味饮料,在炉子旁待到午夜,尽管我们什么也没有吃。我们俩的脚趾都酸疼,维卡的脚趾还有点麻木,但没有看到冻伤的迹象。我们自很多天以来第一次睡着了,我们两人头脚相对,睡在我们的单人睡袋里。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晴朗,但是风很大。在过去几周内,5月12日给了我们唯一适合冲顶的好天气。不知何故,我们居然这么幸运赶上了。我们尽管感觉很疲惫,但仍然收拾好了装备,早餐也没吃,在早上九点三十分就动身离开了。我们留下了帐篷、炉子、燃料,一些剩余食物和睡垫给我一起攀登K2的老朋友查理·梅斯,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我们之后到达安纳普尔纳大本营,并计划晚一点冲顶。
我们尽可能快地穿过北坡危险的开阔地带。在那段危险的通道上,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屏住呼吸。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撤出北坡了,我们迈开疲惫不堪的双腿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川高原,向二号营地前进。在我们能够轻松呼吸之前,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远离北坡。2000年我们在此目睹的吞噬了冰原上半部分的巨大雪崩景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维卡也是同样的感受。
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已经到达了相对安全的二号营地。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查理为我们留下的两升水,我们就像沙漠中的骆驼一样狂饮。我在五天以来第一次脱下了我的羽绒服,却发现连体羽绒服里的羊毛衣上面都布满了从羽绒服里渗出来的羽毛和碎片。羊毛衣裤就像是一个大的麻袋一样挂在我身上。我和维卡看着彼此只有九十八磅的孱弱的身体大声笑了起来。
在二号营地,我们带上了一些我们留在那里的装备,然后沿着路绳走下最后一段山路。在地形缓和之前,我们有一段短而陡峭的冰裂缝地带需要通过,然后是一段长而平坦的冰川伸向一号营地。走在这段路的中间,午后的云层再次滚滚而来,像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邪恶薄雾,决心再最后一次折磨我们。
很快,我们陷入了和前一天登顶下撤时相似的一片白茫茫之中。更糟糕的是,我插在这里的所有柳木条都因为积雪融化而倒下,并被埋在新雪的下面找不到了。因为害怕迷路,我们停下来等待了一个小时。我们非常沮丧,试图用嘲笑自己来改变情绪,但我们其实都快哭出来了。我们知道通往营地的大概方向,但之间有一片布满了冰裂缝的雷区。我屏住呼吸一边说:“拜托! 放我们一马吧!”安纳普尔纳似乎不想让我们离开。
最后,云终于都散开了。一号营地就在二百码之外。我们几乎不需要从那里带上什么东西:它只是下降路线上的一个关键路标。从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向左急转弯,然后穿过一个小的冰瀑。
我们和吉米用无线电进行联系。他承诺,所有随行人员都会徒步到冰瀑的底部来迎接我们。我不得不告诫自己不要放松警惕——还没有真正结束。只有当你从山上下来,最后一次脱掉靴子时,才算是整个登山过程的真正结束。
最后,可以看见所有人都在冰瀑的底部等着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叫喊声和欢呼声。我们在冰瀑上方平稳而缓慢地绕绳下降。最后一次,我们屏住了呼吸,祈祷当我们在通过最后的一段冰塔和裂缝中间时,不会有任何崩塌事故。
然后——终于! 我们下到了他们之中。西尔维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把我抱离了地面,威胁着要让我窒息。这些家伙带来了啤酒和薯片,还有我们的徒步鞋。我们换下了靴子。这是与新老朋友非常愉快的一次重聚。终于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泪水从我的眼里夺眶而出,被太阳镜的黑色镜片遮掩住了。一股巨大的解脱感压倒了我所有的情感,我抑制住抽泣和维卡拥抱着,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他人帮我们背上了背包。我们又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到达大本营。在那段时间里,天又开始下雪了。现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这美好的一天。感觉像是圣诞节,而我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我刚收到了最美丽的礼物——安纳普尔纳。
很多人问我,除了一种深刻的满足感之外,在完成了这个伟大追求后我有没有感到有些失落。毕竟,这十八年来,我的生活是被登顶高山之巅的热情所掌控的。在我选择放弃了我的兽医生涯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就是我的生活。它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但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在我的三十次探险中,我登上8,000米级山峰的顶峰总计达到了二十次。这意味着我曾经不得已,或者判断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弃十次登顶的可能:在珠穆朗玛有四次,在安纳普尔纳有两次,希夏邦马、布洛阿特、道拉吉里和南迦帕尔巴特各一次。其中有四次是我在距离顶峰仅仅三百五十英尺的范围内决定转身下撤的。我为自己从未因为缺乏准备、力气或欲望而转身下山感到骄傲。我选择放弃和下撤永远都是因为恶劣环境条件造成的。
2005年春天以后,我既为普通听众做公开演讲,也给公司做私人化的活动。来自后者的收入是进入我的口袋,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维持生计的一部分收入。但是我将公开演讲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我虽然已经完成了所有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但我也希望我能继续用我自己探险的经历来鼓舞和激励其他人。正如宝拉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会给世界带来一些小的好处,那么登山运动也许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自私。
当我们离开安纳普尔纳时,我觉得好像有天使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在山里,我有一种敬畏感,当我在登山时,好像有个人或什么东西在默默注视着我。人们常常问我是否有宗教信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我相信一些不是那么有形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统治宇宙无所不能的神。
大约三十年前,我是一个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长大的天真小孩。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莫里斯·赫尔佐格的《安纳普尔纳》。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向。最终,它指引我转向了一个追求,一个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美国人完成的追求,甚至是企图完成的——攀登世界上十四座最高的山峰,并且用最纯粹的风格来攀登。
很多个探险旅程的日日夜夜,我都在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感到一种恐慌的绝望,我怎么能让自己坚持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同时还能通过它来谋生? 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做到了这一点。我从不停止相信自己。
(本文摘自《攀登者:站在雪峰之巅》,[美]艾德·韦斯特、大卫·罗伯茨著,杨婕、善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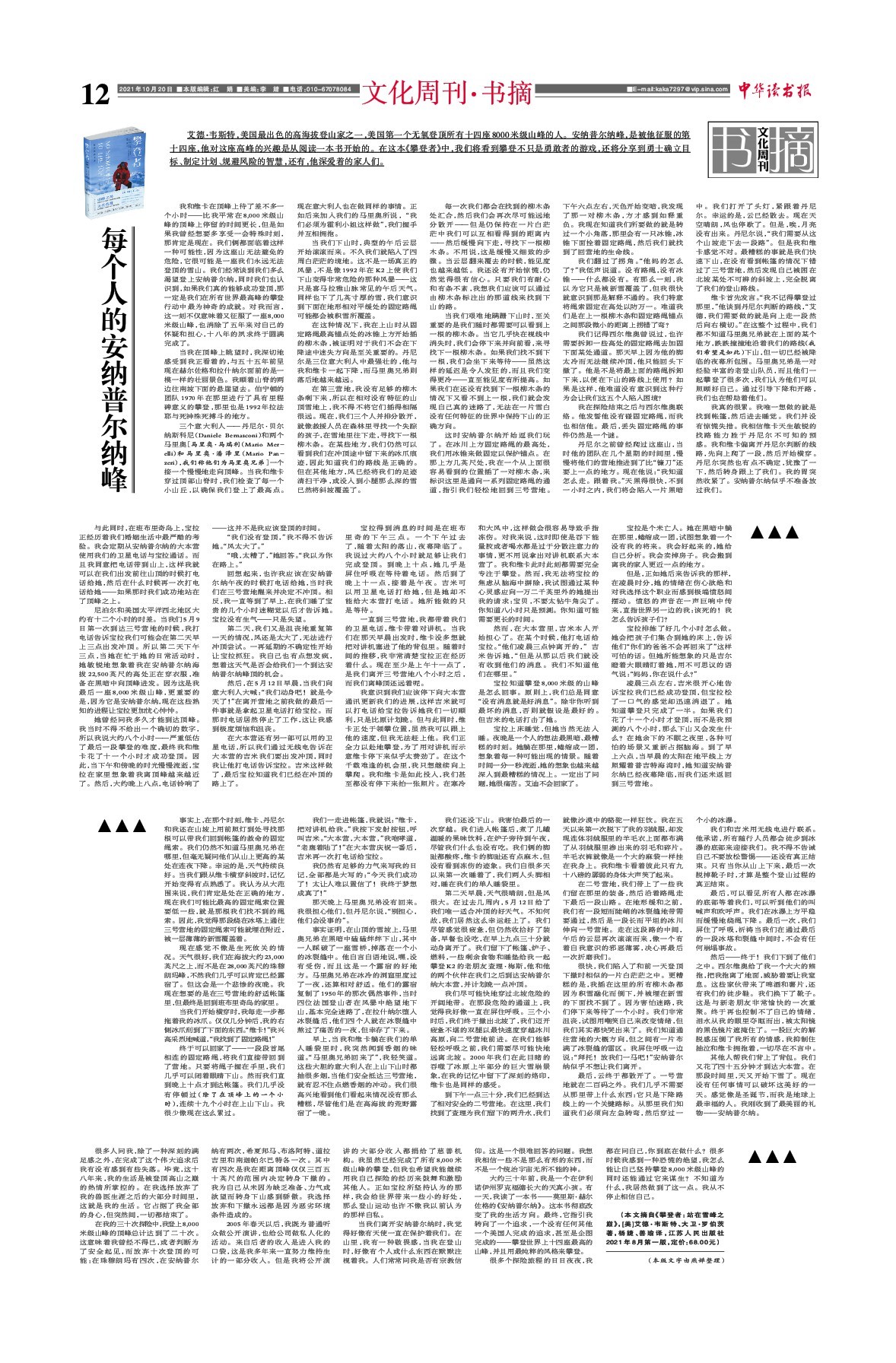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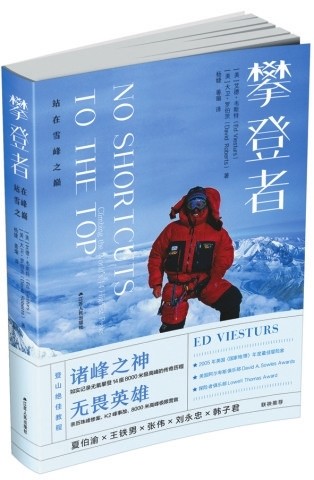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