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尽管这是一则简洁的格言,可以作多种解读,但从专治人文学的历史学者看来,若论及今日全球人文学科的纷繁复杂的“多知”,语文学便是那个“以一当十”的刺猬的“大知”。这并非我的随意解读,而是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詹姆斯·特纳的暗示。他的专著一开端引述了这句话:“这两种动物是否可能知道的是一样的事? 刺猬的‘大知’是否能包含刺猬的‘多知’?”(James Turner,Philology:The For⁃gotten Originsof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ix.)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特纳这本重要著作的第一章《“幽居的书虫,在缪斯的鸟笼里争论不休”——语文学从古希腊到约1400年的历史》如今被译为中文,收入新出版的《何谓语文学》一书中。
沈卫荣、姚霜主编的《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文学研究和古典学等相关领域学者讨论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文章十九篇,主要关乎语文学历史与未来、实践与批判两个方面。
一、语文学的转向
20世纪末,西方有一个重新思考语文学的转向。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在文选第一篇中。哈佛大学古典系专治中世纪拉丁语文献的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教授真实记录了1988年哈佛大学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如何苦口婆心才获得资金支持,召开了名为“何谓语文学?”的主题会议,也记录了其后续的出版与学术影响。作者用灵动活泼、不乏自嘲的文笔,带我们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理论热时代,自视甚高的语文学遭遇的尴尬:旧日“学问的女皇”语文学也需要借助保罗·德·曼《回归语文学》一文的“加持”才能重回舞台中心。会议议题“跨越了从古代印欧语言到当代非裔美国文学的整个范畴”,茨教授坦诚表达了这次会议各执一词的剑拔弩张、激烈争论及其带来的学术成果。他最后提醒我们“不能将自身的专业割裂为两个层面,一层完全专注于概念上的问题,另一层完全投入文本与技术工作”(P.55)。茨奥科夫斯基1990年的告诫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这次会议的后续反响,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语文学。
斯坦福大学文学文化语言系荣休教授汉斯·乌里奇·贡布莱齐(Hans Ulrich Gumbrecht)主要研究法意比较文学。他的文章从几位德裔罗曼语文学名家着笔: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与斯皮泽,谈及他们与传统的古典语文学家为何多有不同。贡布莱齐1995-1999年之间参加了五次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语文学研讨会之后,写作了《何谓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文选选译了该书导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比较文学教授,他与古典学家、版本校勘学者、艺术史家多次讨论之后,对文献“历史化的能力”“历史距离”的体悟:“历史化意味着将过去的物体转化为神圣的物体,也即与此物同时建立一种距离,一种让人想触碰的渴望。”(P.61)
说到底,语文学的核心,不单纯是处理原始文献的实践能力,关键的是如何将这些材料,编织进历史和文化的网络。它考验的是语文学家的历史观:如何理解古代材料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正因如此,《方法与实践》文选最后选取了谢尔顿·波洛克的三篇雄文,就是对语文学历史回顾所遗留下问题的当代回应。这三篇文章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二、当代语文学的历史应答
《未来的语文学? 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语文学的三个维度》《语文学与自由》可以说是波洛克为危机中的语文学寻找新路的系列之作。波洛克化用了当年维拉莫维茨批评尼采《悲剧的诞生》时那个讽刺意味的题目《未来语文学!》。因为对于维拉莫维茨来说,任何关于过去社会或文化现象的真正知识只能完全从今日的视角中抽离出去;而尼采认为,回到区隔出古代“那一刻”的语文学方法完全僵化了古老的事物,它必须有当代意义。“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历史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科学与教化之间,学术与生活之间的争论。”(P.396)波洛克先简要回顾了近代欧洲、印度和中国,语文学面对强悍而坚硬的科学和技术时作为“软科学”的微妙命运。他直面了语文学自身的学科性缺陷,承认在学术制度上她的垮塌。但波洛克引入伽达默尔和布尔迪厄的理论,他想用“双重历史化”:语文学家和文本都要历史化,来调和维拉莫维茨与尼采的争论。(P.423)
波洛克让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互补共建出真正的“未来语文学”,是在《语文学的三个维度》中。该文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篇文献。虽然波洛克的专业领域非常狭窄——梵文语文学,他却体现了坚实的理论建构能力、极强的历史意识和包容多维的学术视野。他说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即把语文学当作一门解读和诠释文本的学问;同时,他认为语文学及其研究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展现:文本的创生(“历史的层面”)、文本的接受传统(“传统的层面”)、文本对于语文学家自身的意义(“当下的层面”)。语文学家若要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并能说明白它的意义,就必须同时兼顾这个文本于这三个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所有意义。(P.431)
三、影视剧里的语文学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有一个纲举目张、骨肉相应的导言,虽然多达45页,但是非常有趣。开篇是从2019年梅尔·吉布森饰演的电影《教授与疯子》说起的,那关乎19世纪下半叶《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传奇,发生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里的语文学故事。值得对照的是此时正在热播的Netflix喜剧《英文系主任》 (The Chair):一位过气明星要依靠捐赠获得该系的荣誉教授头衔,靠自己30年前未完成的贝克特博士论文来系里上课;吴珊卓饰演的亚裔女系主任对这个“老白男”进行了降维打击,那就是用花样理论震慑他:知道这20年文学研究发生了什么?“情感理论、生态批评、数位人文学、新唯物主义、书籍史、性别研究发展、批判种族理论!”
是的,很遗憾,尽管《方法与实践》开篇就告诉我们哈佛大学茨奥科夫斯基在1988年的“语文学”会议成效卓著,但今天北美英文系里仍然没有语文学的位置! 如果把《英文系主任》里的这个场景作为一个当今大学学术现状的参考样本,你会发现,系主任举证的,的确八九不离十,它们都是新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热门。它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个理论是关乎文学的内部研究的,修辞、文本、诗学、美学? 不,那都是需要语文学功底的。最流行的全都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且基本都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憎恨学派”。它们看似深刻,新见频出,目标并非是对过去的文本抱着“同情之了解”,也没有“历史的温情”。但是缺乏了语文学的态度和方法,听众和读者甚至没有耐心听完、读毕就急着下结论,也并不在乎理解是否正确。这也是《英文系主任》剧中多个抗议活动和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要知道,旧时代精英化的语文学在今天也必须有勇气、有智慧推广自己精湛的手艺,目的是在消费主义盛行、大众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里,让读者学会有耐心按照本来的样子去正确理解上下文语义和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别人遗忘了你,你就必须自己大声疾呼:日新月异却日渐割裂的世界,更加急需古老的语文学!
四、“大哉问”里的困境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被问礼时说“大哉问”。何谓语文学? 就是如今那个“大哉问”!
语文学到底是什么? 一个学科? 某种方法? 还是一个研究领域? 是,又都不仅仅是。
要知道语文学曾经是一个“学科”:她作为学术的学科化(the aca⁃demic disciplinization of philology)始于哥廷根,德国学生沃尔夫拒绝在神学、哲学、医学当时的三大学科注册,最终要求增设选择“语文学”。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今天在北美的学院设置中,语文学“化盐于水”,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要找到参照就会明白语文学的尴尬:语文学对人文学科之重要,就如同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数学如今在学术界根基稳固,而语文学岌岌可危,需要理论家大声疾呼“回归”。
《方法与实践》收录了多篇阐释语文学概念与内涵的文章,仁智各见。谢尔顿·波洛克将语文学更开放地视为一个统一的全球知识领域(a unitary global field of knowl⁃edge)(见谢尔顿.波洛克等编:《世界语文学》,“导言”,第22页);编者认为是“一门十分特殊的语言学科,一种实践已久的人文学术方法,或者是一个具体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它也可以是一种解读文本的手 艺 (the craft of interpreting texts),一门阅读的艺术和学问(the art and scholarship of read⁃ing),甚至说,它只是一种学术观念(academic perspective)或者一种学术和生活的态度,或者一段有趣的学术掌故”(P.11)。最终编者总结了六个范畴,但一句话:“语文学实践的核心是要求学术研究必须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将文本放在它原有的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它做出合理和正确的解读。”(P.44)在这本书中,语文学更多被视为“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一个“框架结构”(P.16)。这还不包括类似本书没有收录的语文学家文泽尔(Siegfried Wenzel) 认为的:“语文学与其说是一门有着清晰定义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毋宁说是一种态度( atti⁃tude)。”(Siegfried Wenzel.“Reflec⁃tions on ( New ) Philology.”Speculum65,1(1990):11-18.P.12)正因如此,这本书的主标题“何谓语文学”并非是提供一个答案,而是提出这个问题,试图让读者去回答、去思考,甚至提供更多非西方视角的答案,这也是本书编辑的目的之一。
多元的回答当然丰富了论题,但是在一个“学科为王”的制度化时代,语文学如果无法再学科化,她如何“回归”呢? 她如果是一切,那就什么也不是!
五、“语文学式的”刺猬与狐狸
回到刺猬与狐狸的比喻。
它固然因以赛亚·伯林在同名文章中对俄国思想家的类比而尽人皆知,但伯林在1953年版注释中标明了这句谚语的希腊文,而且注明来自阿奇洛克斯(Archilochus)的诗句残篇,出处仅写了“Diehl,Frag103”。他应该指的是德国著名古典学者恩斯特·狄尔(Ernst Diehl)1925所编、1949年重印的古希腊抒情诗集(Anthologia lyrica Graeca,aedi⁃bus B. G. Teubneri,1949)。
文首所言詹姆斯·特纳201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语文学:现代人文学被遗忘的起源》一开端引述了这句话。他是从伊拉斯谟1500年的《格言集》(Erasmus of Rotterdam,Adages,1500) 翻译的,特纳专门注释了伊拉斯谟的拉丁文“Multa no⁃vit vulpes verum echinus unum magnum.”说伊拉斯谟翻译得不好(stuck),因为翻译为英文成了(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one big thing)后半句似乎“噎住”了。
在韦斯特所编书中 (M. L.West (ed.), Iambi et elegigraeci ante Alexandrum cantati,2nd ed.,vol.2,Oxford,1992),谈到该句谚语在荷马(残篇,5)和阿奇洛克斯那里都曾出现,最早被记录在古希腊智术师泽诺比乌斯(zenobius)的寓言之中,但是该诗句韵脚属于抑扬格,而不是扬抑格,若归于荷马,韵脚只能和喜剧史诗《马尔吉特斯》(Margites)相配,该书一般现在被认定为是荷马的伪作。即使归属该书,时间上也晚于泽诺比乌斯(C.M. Bowra, On Greek Margins(Oxford,1970), P.59.)。
因此严格地说,“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按照语文学的考察和推断,最有可能是很多人都使用,却不属于某个个人。但是鉴于泽诺比乌斯比之其他人似乎更喜欢使用动物的意象,且在传世可靠文本中他的记录最早,该格言的这一韵律格式至少从目前材料看来,是阿奇洛克斯首先使用的。当然这些推断伯林显然并不知道。
这繁复的推论就是典型的语文学的一种判断!
这是一个因果世界的长链条的考察与推理,需要“板凳愿坐十年冷的研究者”,更需要有耐心的读者,特别是在七分钟短视频席卷世界,人类的关注时长已经被“豢养”为最多12秒时,就更需要“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就是一种愿意共情,提倡“理解、宽容和和谐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
尽管语文学就是基于文字、语言和原始文献,说出事实。套用巴塞尔大学语文学家尼采的话,总是“不合时宜”!《何谓语文学》编者之一、作为藏学家的沈卫荣教授常常破除公众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从早年的随笔集《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西方“妖魔化”“神化”西藏的揭示,到疫情期间提醒“丁真热”中媒体的“自我东方化”,以及隔离期间带着学生用“语文学的方法”重读仓央嘉措去发现那些“误读”,都可能让大众“扫兴”,但这就是“语文学的”! 因为如波洛克所言:语文学是“诠释的约束”(P.451),是现代人“解放自我的方法”(P.465)!
那么到底“何谓语文学”?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宗教中类似象头神迦尼什的“一神多化身”(the multiple avatars of a deity)或者上帝的“三位一体”去类比理解:历史上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层面,对语言、文本进行的正确解读,就如同各个化身或者“位格”,最终都是“语文学”之神这个“一”。或者我们至少明白,狐狸的“多知”,其实最终都在刺猬掌握的语文学这个“大知”之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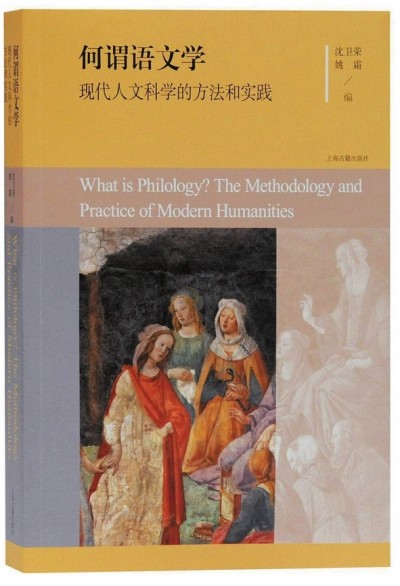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