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生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8月28日,夏目漱石(1867—1916)在给弟子小宫丰隆的信函中写道:
我在《新小说》上发表了一部名为《草枕》的作品,预计9月1日刊发。你务必要读一读,这样的小说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不过,莫误解为开天辟地以来的 杰作)。(『漱石全集 · 書簡(上)』)
“开天辟地”,自然是开玩笑的话,这也说明了夏目漱石和弟子关系的融洽,但“未曾有过”无疑也表达了夏目漱石对《草枕》(1906)创作的艺术自信和自觉。“未曾有过”指的是什么呢?
对此,夏目漱石在不久之后撰写的《我和〈草枕〉》(1907)一文中提供了较为明晰的线索:
我的《草枕》是以与一般意义的小说截然相反的意义写成的。若能给读者留下这么一种感觉,即美的感觉就满足了,其他的没有任何目的。……一般意义的小说,也就是让读者玩味人生真相的小说也是不错的,但我想,还应该有一种让人忘却人生之苦起到慰藉作用的小说存在。我的《草枕》就属于后者。……以往的小说是川柳式的,以表现人情世故为主,但此外还有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的小说。……如果这种俳句式的小说——名称很怪——得以成立,将在文学界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种小说样式在西洋还没有,日本也还没有,如果在日本出现了,就可以说,小说界的新运动首先从日本兴起了。(『漱石全集·第16巻別冊』)
由上可知,夏目漱石所言的“未曾有过”的小说,其独特性主要在于:文体上是“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小说”,而主题内容是表现“非人情”。
《草枕》是夏目漱石继《我是猫》和《哥儿》之后创作的第三部小说。或许,正是因为文体尤其是主题上的独特性(也可以说是实验性),虽然没有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可,却引来文学评论者们的持久关注。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自从小说诞生以来,《草枕》中“美”的核心理念,就“自然而然地”被命名为“非人情”的美学,这似乎早已成为了一种常识。日本学者村松昌家的《作为小说美学的“非人情”——〈草枕〉的成立》一文就颇具代表性。该文指出,当时的明治文坛流行的是“人情写实论”(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和自然主义文学风潮,以《金色夜叉》《不如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为代表的描写“情欲”甚至“肉欲”的作品才是主流。《草枕》以描写“非人情”为主题,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文坛的一种文学的批评和反抗。总之,夏目漱石在和主流文学的抵抗中创作了《草枕》,实践了“非人情”的美学。也就是说,《草枕》中的美学,是一种与描写“人情”相对立的文学审美,故而被称为“非人情”美学。
此外,主张“非人情”美学的学者还指出,1907年夏目漱石出版了《文学论》(底稿为东京帝国大学授课讲义),在该书中也出现了“非人情”的概念:
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样的诗篇怎样呢? 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说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也许是没有一点礼貌,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中略)吟咏与人事缘分较疏远的、未混入人情的自然现象的诗,其中较多含有“非人情”的、“没道德”的趣味,实不足怪也。古来东洋文学中这种趣味较深,日本的俳文学尤其如此。”(『文学論』)
总的来说,主张“非人情”美学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夏目漱石自身在《文学论》《我和<草枕>》等处提及了“非人情”这一概念;第二,《草枕》小说的内容以“非人情”为主题。
这样看来,主张《草枕》“非人情”的美学似乎实至名归,也理所当然。但若回到小说,细读文本,仔细聆听作品的声音,我们会发现《草枕》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现“美”,而不是“美是什么”。也就是说,《草枕》借助主人公“我”并没有追问“美”的本质和内涵,夏目漱石交付给主人公“我”在《草枕》中的任务,是思考通往“美”的方法和途径,即小说集中呈现的“美学”不是本体论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美学。
鉴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草枕》核心的美学理念并非“非人情”,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观照”的美学。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草枕》的美学理念主要体现了禅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下简称“无住”)的观念,而“观照”是“无住”观念内在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无住”观念指导下的方法论。
《草枕》与禅宗思想关系密切,禅宗的意象俯拾皆是、随处可得,文体用语也充满禅机趣味。鉴于此,韩国学者陈明顺甚至建议称之为禅宗公案小说(《漱石汉诗与禅的思想》)。不过,迄今为止,鲜有学者指出《草枕》中禅宗的思想,实则集中在“无住”观念的事实。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个文本,甚至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及环境的文本,都是能够阅读和被理解的;而且,任何人都不需要完全以作者式的理解来阅读文本;因为,理解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的主观体验性。尤其对《草枕》这样“以美为生命”的作品,我们更应该回到作品自身,去感受和理解作品中审美的情感和思想活动。我们相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为读者设定了通往文学王国的暗道和密码,因此,我们建议回到作品本身,且看小说的开篇:
我一边攀登山路,一边这样想。
若是发挥才智,则棱角分明;若是任凭感情,则会随波逐流;若是坚持己见,则可能处处碰壁。总之,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之时,便产生了诗,产生了画。
这段译文(有诸多版本)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可以看作是夏目漱石假借主人公之名,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诗和画(艺术)进行了独特的解释和说明,即诗和画(艺术)产生于对人世难居的“觉悟”,而且这一“觉悟”是在一刹那、一瞬间发生的。这里的诗和画(艺术)是指生成于内心的诗意和画境,而“觉悟”也十分接近一种审美意识的心理活动。换句话说,此处的“觉悟”即是顿悟,是禅宗式的体悟与认知(有趣的是,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出这个判断,依凭的不是理性逻辑,恰是颇具禅味的直觉)。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开篇“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之时,便产生了诗,产生了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尤其是《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说,《草枕》的开篇就是“无住”思想的具体化和文学形象化表达。据传,六祖慧能正是听到五祖弘忍讲授到这句话时,豁然开悟。受“无住”观念的影响,《六祖坛经》中禅法(无念、无相、无住)的关键,也是落在了“无住”这一环上。
“无住”这一观念,体用不二,包括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在方法论上,劝诫人们不要执着万物虚相,而要以觉悟之心,以佛教之眼(佛有五眼),发现一种纯粹的真实之美(本来面目 ),这就是“观照”。这一“观照”的过程,若以《草枕》开篇的另外一段文字来说,就是:“我观我所居之世,将其所得纳于灵台方寸的镜头中,将浑浊之俗界映照得清醇一些。”《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正是这个意思。因此,“观照”实际上与“无住”互为表里,相互通联。我们也可以把“观照”理解为“无住”思想的一部分,是“无住”思想在方法论层面的集中表达。
其二,“非人情”之“非”,需要在禅宗思想的脉络中去理解和把握。
小说在结尾处抵达高潮,这里也藏匿着理解《草枕》美学的关键线索:
女主人公那美在送别前夫之际脸上呈现出哀怜之时,我拍了拍那美的肩膀,轻声地说:“就是它,就是它,它就可以成为一幅画。”(『草枕』:192)
小说中,那美请求“我”为她画一幅画,但“我”一直未能从那美身上找到可以入画的美感,但在上述那一刹那,“我”终于在女人脸上的“哀怜”之中发现了“美”。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此刻的那美,不再是那个佯狂、闪现机辩锋芒的女人,而是以“忘我”的方式抵达了本来面目。不过,那美的“哀怜”是在旁观者的视角下完成的。因此,此处可以入画的“美”不是“哀怜”本身,而是对“哀怜”的一种“发现”,一种观照,从而也是一种审美。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美”自“观照”中来,即对“人情”的“观照”产生出“美”;第二,“美”并不否定“人情”,而是以特殊的方式接受、肯定了“人情”。所以,若是仅仅站在“非人情”美学的立场,就难以解释清楚“非人情”“哀怜”“美”和“观照”之间的互动联系。而对此理解的关键,或许就在对一个“非”字的解读上。
也就是说,“非人情”之“非”不能按照日常用语的逻辑规则去把握,而应从禅宗思想的立场去理解。对此,日本学者近藤文刚就曾说过:“世间的‘非’多半含有否定的意味,不过若从佛教特别是禅的思想的视角考察,‘非’表达了对于肯定、否定之意的超越,反而指向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因此,“非人情”在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视角下,就不再是对“人情”简单的否定抑或肯定,而是在“扫相破执”“无相无住”的观念指导下,用“非”“不”等解构的方法,对世俗人间“人情”的谛观和再发现,从而恢复“人情”的本来面目。这样的禅宗思想,恰恰典型地展现在《金刚经》之中。
总之,如上所言,此处的“非”,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的谛观,也是一种美学的“观照”。
其三,达到“非人情”的审美境界,“观照”是其唯一的途径,“非人情”也是一种“美的观照”。
冈崎义惠曾解读“非人情”时,写道:“所谓‘非人情’,即抽离人情而谛观世界。根据漱石的观点,人情世界即是道德世界,离开道德世界,即为‘非人情’。如此,它应该或是宗教世界,或是艺术世界,或者是科学世界。”(『鷗外と漱石』)。按照他的说法,所谓“谛观”,即“观照”,是实现“非人情”唯一的途径和方法。“非人情”,就是通过“抽离人情而谛观世界”,从而抵达宗教或艺术的世界。
如在《草枕》的第一章,夏目漱石写道:
为了了解这一点,只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这样才有可能弄清楚本来的面目。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戏颇有意思,读小说也是如此。读小说感到有趣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利害念头束之高阁了。在这一看一读之间,便成了诗人。
又如,同一章节中,有如下文字:
芭蕉看到马在枕头上撒尿,也可将之风雅入诗。我也要把即将碰到的人物——农民、商人、村长、老翁、老媪——都当成大自然的点缀加以描绘和观察。
松尾芭蕉马尿入诗,这种超然物外、就地成佛的风采背后是以禅宗思想为依托的。同理,“我”想要学习芭蕉这种态度将世俗的世界审美化,其方法也必然是禅宗式的“观照”。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观照”这一禅宗思想的视角和立场,正是理解“非人情”的关键。而《草枕》的内在思路就是借助禅宗的“无住”观念,观照世俗情欲,从而抵达一种“非人情”的审美境地。
其实,“非人情”不仅是“观照”带来的结果,经由“观照”这一过程,“非人情”也就成为了“观照”美学的内容。日本学者藤尾健刚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非人情”就是一种“审美认知的态度”,也是一种“美的观照”。(『漱石の近代日本』)
其四,将《草枕》的美学看成“观照”的美学,才能发现《草枕》隐含着构建“介入性”美学的努力,才能理解《草枕》美学向伦理学的延展和变异,也才能更好地把握夏目漱石文学思想的方法论以及他深层的思想困境。
日本学者水川隆夫曾在《夏目漱石与战争》一书中,认为《草枕》就是围绕日俄战争设置的一个隐喻。其分析虽然有过渡诠释之嫌,但也向我们提示了《草枕》并非一个纯粹审美世界的事实。
表面上看,《草枕》描写的是青年画家远离城市,来到一个偏远山村的“非人情”之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寻求一种抽离世俗人情的、静观的、纯粹的美。但这种“美”最终的完成,却是在这个偏僻而封闭的世界被打破的时刻——女主人公那美为远赴“满洲”战场的弟弟送行,却又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突然看到了前夫的脸——也就是那美脸上露出“哀怜”的那一瞬间。
对于小说的这一结尾(也是高潮)段落,我们不仅要注意到“美”的发现是在“观照”的视野下完成的,而且还要看到所谓“观照”的视野,正是男性画家“我”的眼睛。也就是说女性之“美”的发现者以及管理者是来自都市的男性画家“我”。可以说,《草枕》是夏目漱石借主人公“我”之眼,创造出的一个“非人情”的审美世界。
韩国学者朴裕河曾论及《草枕》的基本线索是寻“美”之旅:都市青年男性画家来到一个相对封闭——远离西洋/现代文明——的田园世界,发现了日本传统之“美”,这样的“美”带有明确的男权支配意识。(『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とジェンダー;漱石·文学·近代』)
藤尾健刚也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认为《草枕》美学思想中扫除个人情欲、回复人的本性的努力,带有某种伦理诉求:
作为夏目漱石美学成立的条件,即超越利害观念,被更多地表达为排除“私欲”之“人情”以及美的观照、保持心之“本性”的内外一体化。《草枕》亦是如此,发现美,就意味着要养育未被私欲污染的澄澈精神,未被恶俗所附身的清洁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与叔本华哲学相同,《草枕》中的美学,即伦理学也。(『漱石の近代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11)
从藤尾的观点出发,将《草枕》的美学看成伦理学也不为过。不过,我更愿意将《草枕》的美学思想,理解为“美学—伦理学”。在“美学—伦理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草枕》美学的丰富性,认识到《草枕》并非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纯粹审美世界。不过,藤尾文中所指的“伦理学”主要是面向个人道德内修的伦理学(ethics),而非政治伦理学抑或服务于国家道德论建设的伦理学。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日本文化语境中的“伦理学”概念和范畴,不同于汉语中的“伦理学”,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日本近代的“伦理学”首先出现以“个人”为关键词的理论性伦理学“ethics”,其后与意图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国民道德论”潮流形成既对抗又融合的态势。随着日本近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个人的话语受到压制,这两种伦理学最终被统合于“人类共同体之理法”(和辻哲郎)为代表的日本战前伦理学的潮流之内了。
那么《草枕》美学中的伦理学是怎样的状态呢?
回到《草枕》文本,我们还发现“我”的美学思考,也是在“观照”的思维框架中展开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西洋/现代vs东洋/传统”这样对立的图式中得以展开的。
如,小说的第一章就颇费笔墨地讨论起东西方诗歌之别,以叙事者“我”的视角,主张与西方/近代入世的诗歌相比,东方/古典诗歌摆脱了世俗人情、同情、爱和正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让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可以抛却一切利害得失、超然世外。
从“美学—伦理学”的逻辑上讲,通过上述比较和参照,《草枕》在美学意义上肯定了东方/古典诗歌的价值,确立了东洋/传统诗歌相对于西洋/现代诗歌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夏目漱石在东洋/传统文化比照下发现(指摘)西洋/现代文化之不足,进而思考和建构当代日本文化之美。不过,对当代日本之“美”的确立,并非只是面向西方/现代的否定,还有面向日本内部(国民和政府)的质疑和批评。如在小说结尾,借助“火车”这一强烈的隐喻,夏目漱石对日本现有的文明观念和海外殖民行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那美“哀怜”之美的发现(明线),也完成了在国家话语层面的伦理学批评(隐线)。换言之,夏目漱石在“观照”美学的框架下,对西方/现代美学的质疑和否定(向外),实际上和前面所言的对日本女性/传统之美的发现和管理(向内)互为表里,一并构成了《草枕》“美学—伦理学”的“个人—国家”话语两个层面。这样的“美学—伦理学”也暗合了一种男性支配观念下的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和明治时代国民道德秩序的意味。
整体而言,《草枕》的“美学—伦理学”,一方面可视为创作者夏目漱石对日本追随西方列强对外发动殖民战争——以“私欲”的立场暴力占有—的国家“美学”的反抗,一方面也可视为对个体如何建构世界观的道德建言,且两方面共存于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文化之美的追问和思考之中,充分表达了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主体性建构的关注思考和不安。
美学,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历史维度,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容,具有一种超越时代又融于时代的特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近代美学的确立者康德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世人眼中这位无比纯粹的美学家和哲学家,却也是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首倡者和思想革命的引路人。也可以说,审美基于情感的历史维度和人性的哲学深度,以形象和感性的方式显现了人所在的确切位置与生存困境。
夏目漱石的《草枕》之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它“以美为生命”的主题,更在于它寻找、发现美的方式即“观照”。因为“观照”既可以通往美学,也可以抵达伦理学。在“美学—伦理学”的互动中,我们看到了夏目漱石以文学审美“介入”社会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夏目漱石(甚至日本近代作家这一群体)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的方法论——通过东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复兴),强调一种道德的修养来补救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弊病。对很多作家而言,这一方法论至今都没有过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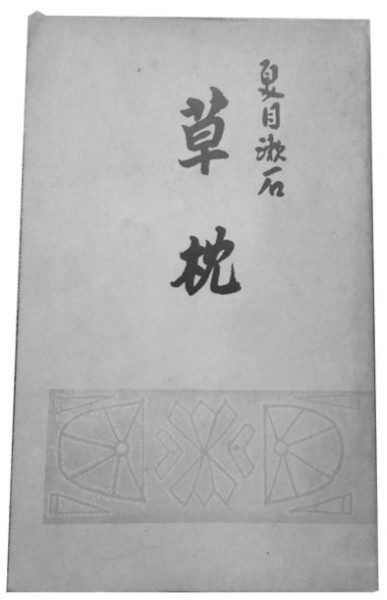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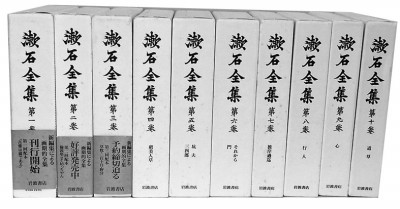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