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张兴博士的《经学视野下的〈大学〉学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在他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是在经学的视野下对汉代以来《大学》诠释学术史上几个重要阶段、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所作的学术史梳理,初步形成了《大学》学史研究的框架。
这部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经学视野或者说经学基础。作者把《大学》诠释史上郑注、孔疏为代表的汉唐经学与以朱子、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一同放到经学史中进行研究,辨析了经学的狭义和广义,指出他所说的“经学史的视野”是广义的“经学”,是将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一起作为中国经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分了“汉唐经学”与“经学史的视野下”两者的联系与不同,深入到了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关注不够的经学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思想观念的梳理与阐发。
中国传统学问是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这不是一种平面并列的学科分类,而是一种立体的思想价值架构,即以经学为核心,而经学是儒家道统(核心价值)的载体,代表中国文化的根本和灵魂,史、子、集则为辅翼流裔。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犹如树根,史如树干,子为树枝,集为花叶,构成国学大树的整体,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所以,以经学为基础,才能抓住学术思想的大本大源。经学有一个不断扩大、增加的过程,如唐宋之际“四书”的升格运动,从先秦五经到清末十三经,形成了经学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成中英先生归结为一种范式转换,“先秦是一种典范,汉代又是一种典范,宋明是一种典范,清代也有典范。典范一旦形成,就主要在典范里面谈问题。但典范又是变化的,这样就呈现出经学的发展。需要不需要典范呢? 经学嘛,是大经大法,价值系统,是为社会提供规则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不能变来变去,要保持相对的稳定,但经义一旦固定下来,又面临僵化、教条化的危险。这样,就需要新的典范出来。而且需要对经学经常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寻求新的典范。”(梁涛:《国学、经学与本体诠释学——成中英教授访谈录》,《国学学刊》2010年第1期)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每一次经学的发展都是典范的转移。
近代以降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一结构与体系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变。左玉河先生考察了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怎样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性的变革是相互呼应的。对于这一转变的利弊得失,功过是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反思,“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更是显示了国人学习、研读传统文化基本经典的热情与努力。这是中华文化复兴,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体现。
长期以来,《大学》包括“四书”的研究者,主要是做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大都集中在《四书集注》基础上如何构建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相对忽视汉唐注疏。张兴博士在广义经学的视野下大跨度、长时段、历史性地考察了《大学》诠释的历史,并提高到“《大学》学”的高度,这是学界还没有人做的。就“四书”而言,目前已经有了唐明贵的《论语》学史、黄俊杰的《孟子》学史,《大学》《中庸》还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因此,对《大学》学的发展演变与流传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将对《大学》,乃至整个《四书》学的研究,甚至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
这部书是在经学史的视野下梳理《大学》诠释的学术史,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框架,这很难得。经学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变化当中,有汉学和宋学两大阶段、两大范式,呈现互为胜负、互为消长的历史,至清代汉学与宋学从分化、对立、相争,到汉学繁荣、宋学衰微,到道咸以降汉宋兼采,一起走向衰亡,经学乃至中国文化,完成了一个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如今正在走出万类萧条的冬季,迎来了全面复兴的春天。本书在内容结构上把汉唐的《大学》学和朱子、阳明的《大学》学为作为主体,引用清代四库学者的观点,《大学》在汉唐属于经学(狭义),而在宋明则属于理学,到了清代又重新回归《礼记》,成为“礼学”。作者着重梳理了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四人的《大学》注释,认为郑玄的《大学》注体现了郑玄的政治理想——即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思想解读;而孔颖达的《大学正义》则是以“诚意之道”为理论基础,以“为政之道”的顺利实行为宗旨;而朱子的《大学章句》则是以“修己、治人”作为宗旨,以“格物致知”作为学者的最重要修养工夫,自然而然推之“新民”(即治人);而阳明的《大学》学,虽然早年以“诚意”为解《大学》的核心,但是在晚年则以“致知”结合《孟子》之“良知”,结合自身之切身体悟,提出“致良知”学说,则阳明的《大学》学是以“致良知”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这就能够抓住了《大学》学史的主要方面及其思想主旨,并进一步揭示出汉唐经学与理学、心学,以及汉学与宋学的内在区别与联系。
如果要说不足的话,本书在揭示各家思想主旨时虽然注意到了时代特点的不同,但还未能把思想学术史与社会政治史结合起来,从《大学》文本的诠释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联中中分析各家思想主旨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对清代学者研究《大学》学的成果和近代以来学界对《大学》学的现代诠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探讨,将来可以扩展补充。
今天如何诠释《大学》? 如何在新的诠释中揭示出《大学》的新意,以为今天的儒学重建提供思想资源,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是大人之学,即成圣之学。
《大学》一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即成为大人之学的道理。这里的“大学”,可能与古代的教育制度有关,但远超出我们今天理解的学校教育。《礼记·学记》载:“比年入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孔颖达疏曰:“‘此大学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论,是大学贤圣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大学,谓天子诸侯使学者入大学,习先王之道矣。”可见,古代“大学”从学制讲属于高等教育,从内容来讲是学习先王之道、圣贤之道。学习先王之道、圣贤之道目的是为政,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是说之所以称为《大学》是因为是教人广博学习以从事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郑玄的这个解释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朱熹《大学集注》把“大学”解成“大人之学”。那么什么是“大人”呢? 所谓“大人”,原本是指在高位者,如王公贵族,后来指圣人。朱熹《大学集注》注曰“大学者,大人之学”。在《经筵讲义》中仔细解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故以《大学》名之。”这也与《大学》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只是他更强调穷理。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借用《孟子》的观点对“大人”“大人之学”解释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可见,大人就是具有仁心的人,他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整体,对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事物都能够以仁爱之心待之,无私欲之弊,能够明其明德。反正,则为小人。所以,大人之学就在于其私欲之蔽,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由此可知,大人就是圣人,“大人之学”的真正意义是指希贤希圣,学为圣贤的大学问。
第二,《大学》以修身为本,本立而道生。
《大学》的文字结构,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1)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从大纲讲大学之道。(2)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细目讲大学之道。这两大部分的关系是——“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相对应,修养途径是知、止、定、静、安、虑、得“七证”,都是“修身”份内的事;“亲民”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都是“修身”份外的事。“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实现目标、达致理想的根本环节是“修身”。《大学》的修身不是单纯对帝王和为政者讲的,是包括所有人,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作为关键环节,具有内外相合的特点。熊十力说:“八条目虽似平说,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熊十力:《读经示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8页)杜维明也说:“按照《大学》的说法,自上层统治者和文化精英直到贩夫走卒,都应以修身作为根本。根本不立则道不得流行。所有为着人的发展的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设施都依赖于修身,由此方可达致家庭稳固、社群规整、邦国安定乃至天下太平。这种与道德、社会和政治相通的个人主义基于一种简单的观念,即整体健全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活力。人的终极完善意味着家庭、学校、社群、国家乃至天下之每一以及一切成员的良好修养。”因此,“修身在自我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构成的社群的链环中居于中心地位。就个人方面而言,修身涉及复杂的经验学习与心智锻炼过程。就人类总体发展而言,修身则为家庭稳固、社会有序和世界和谐的基础……修身的核心地位促使中国思想家们将伦理付诸实施,将审美作为经验,将形上学转化为智慧,将认识论运用于沟通。”(杜维明:《修身》,《杜维明文集》第4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628-629、614-615页)修身为本才能确立大学之道。
儒家的修身是指修养身心。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提出内外交养的修身之道。所谓“内”指修心养性。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提出“修己以敬”,《大学》指出“修身在正其心”,后来孟子提出了“四心”说,认为人都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此“四心”即是道德之心(仁、义、礼、智)的萌芽。此基础上,孟子强调人要确立“本心”,人虽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是人生在世,受各种物欲引诱,本来的善性在一天天变恶,这就是失其本心,“失其本心”也就是“放其良心”。他教人修养的方法就是“求其放心”,即把失去了的善心寻找回来。善心要“操存”,即好好保护。他还讲“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减少欲望是保养善心的最好途径。荀子《荀子·修身》篇讲治气养心之术:“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根据人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性格、心理的弱点有针对性的进行心性修炼,以达到提升整个的人生境界。所谓“外”指践行礼仪。礼仪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生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随时随地的道德律令、行为规范,使人自立于社会,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立于礼,成于乐”,“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知,进退揖让无所制”。礼可以使人立足于社会,不懂礼,一个人言行举止、手脚耳目、进退回环都不知道怎么办,就不懂得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孔子还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君子广博地学习典籍,并用礼来约束自己。礼还能陶冶人的性情。人具有动物性,有情欲,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不像动物一样放纵自己的情欲,而是通过道德礼义节制自己的情欲。古圣先贤制礼作乐,是本着人内在的性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是按照人情人性制作的。“礼”的功能就是以礼节制、以乐调和人的情感,不使人因为过分情欲放纵而堕入动物界,这就是《毛诗大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修身的途径是下学上达,达到最高境界——与道合一,实现最高目标——超凡入圣。
第三,《大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大学》虽然没有出现“内圣外王”四个字,但三纲八目都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是内圣,即把圣人内在的德行加以彰明;推圣人之德于天下就是外王。在三纲中,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在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相对应,修养途径是知、止、定、静、安、虑、得七证,属于内圣方面;“亲民”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是属于外王方面。“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二者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统一。由内圣达于外王,外王以内圣为依据,儒家内圣外王的意蕴在这里表达得十分圆融。
尽管“内圣外王”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家,但《庄子·天下篇》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确实能够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主体精神,后来就为儒家思想的基本结构,也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内圣外王的渊源就是古代圣王。在儒家看来,古代圣王代表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是指如何以这些古代圣王为典范,实现“内而成圣,外而成王”,即成为圣王的道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上古圣王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圣与王一分而为二,孔孟荀就在理论上探讨圣王、圣人的内涵,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儒学更新发展过程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结构。孔子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既有德行又有功业的古代“圣王”,是真正有“盛德大业”的人物,是完满地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人物。但在现实中圣王一分为二,所以孔子在理想上强调内圣外王的统一。《论语·宪问》载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谓“修己”即是“内圣”,“安人”“安百姓”,即是“外王”,体现了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的统一,是对古代圣王二分后重新的整合。梁启超说:“《论语》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于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梁启超:《儒家哲学》,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孟子心目中的圣王就是尧舜,但现实中尧舜不再,他就强调圣人:“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显然,他凸现的是圣人的人伦道德方面,把圣王的外在事功回落到了内在心性方面,但仍然以尧舜圣王为道德楷模和政治典范,期望现实中的君臣能够效法圣王之道。孟子对孔子内圣外王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道,即以仁义为本,构建起以内圣外王之道为主体的思想体系。罗根泽说:“孟子之学,修身治国经世致用之学也,非空谈心性之学也;其论心性体相,为修齐治平之资助焉尔。”(罗根泽:《孟子评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86-87页)蒙培元认为孟子的思想“一是向外在的社会政治层面发展,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以期统一天下,实现儒家的理想国。所谓儒家‘伦理政治型’的思想模式,从这时开始便基本形成了,这就是所谓‘外王’之学。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基本上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信念没有改变。二是向内在的心灵方面发展,提出心性合一、天人合一的‘诚’的境界说,为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这就是所谓‘内圣’之学”(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159页)。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政治纷争,战乱不休,孟子的外王设计没有条件付诸实践。随着孟子政治抱负的失败,孟子后期学说逐步走向了重内在心性培育,重道德人格的树立,必然偏向内圣,如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的外王,是落实在挺立内圣之本上”(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内圣挺立而外王不足,为后世重“内圣”而轻“外王”埋下了伏笔。
荀子也通过对圣与王的分疏,试图使圣与王二分的情况下得以整合。《荀子·解蔽》云:“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在荀子这里,圣与王便有了分工,圣与王不但在现实中一分为二,而且在理论上各有分工:圣的伦理道德的楷模,王是创制立法的权威。这两种功能在古代圣王那里是一体的。荀子的分疏是为了整合,所以他说圣王是兼两“尽”(伦与制)与一身,学者应以圣王为师,试图在“分”了之后又“合”。但这种“合”显然是一种理想,而他就以这种“理想圣王”作为当时天下的最高标准。荀子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仁为基础的内圣外王之道。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如果说荀子的礼义体系和以礼义为主干的治理体系是外王之学,那么他以“仁”为基础,还提出了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荀子讲心的地方也很多,只是与孟子在理路上有明显差别。荀子以心为天君以治五官,为身形之主宰,其《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也强调“心诚”,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与孟子相似,荀子的思想基本结构也是内圣外王之道,但由于战国末期,天下统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成为时代主题,荀子更重视圣人的外在事功,侧重于外王之道。
总之,孔子以及稍后的《大学》内圣外王思想最为圆融、圆满。相对而言,孟荀仍然是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结构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现的,但各自略有偏向:孟子侧重于内圣,荀子侧重于外王。秦汉以后的儒者也都在把握内圣外王的精义,重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但有的侧重于对孟子内圣一面的发挥,发展出了心性儒学,有的侧重于对荀子外王一面的发挥,发展出了政治儒学。
第四,“七证”——《大学》的性命修炼工夫。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早期儒家通过身心修证而由“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心传,现代大儒段正元就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大学》之道是先天后天、天人一贯、性命双修之道,他说:“《大学》之真道乃是先后合一、内外一贯、性命双修之学。”(段正元:《道德浅言》,《师道全书》卷六,北京: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53页)“《大学》一书,明明德一节,穷理尽性,先天之学也(后天中之先天)。知止一节,炼凡身,了凡命,后天之学也(先天中之后天)。后天炼净,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末交修,还我本来真面目,性命合而为一(性中有命,命中有性),完全先天中之先天。《大学》能事毕矣。”(段正元:《阴阳正宗略引》,《师道全书》卷一,北京: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21页)他又说:
定、静、安、虑、得,明明德之命功,然必先之知止。知止者,止于至善也。《书》曰:“安汝止”,又曰:“钦厥止”,《诗》曰:“夙夜基命有密”,皆是。至善,人身中之中也。能止于中,而后有定;有定则稳贴,不动不摇。有定矣,而后能静。静则万缘皆了,万事皆空。了与空者,了后天而还先天,空后天而实先天也。此了即真了,不了之了;此空即真空,不空之空,如是者即安。安则乐在其中矣,无边乐景皆从中现。本来无思无虑,而一觉之明,自见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无物不与,无处不在,万物皆备于我,而我与道合而为一,乃所谓得也。(段正元:《道德学志》,《师道全书》卷五,北京:道德学社总会印,1944年,第2页。)
“知、止、定、静、安、虑、得”的七证可以说是儒家的命功,在后儒失传了、隐晦了。段正元也就是说,儒家的修养工夫也是性命双修,即以性功为主,命功为辅。儒家不可能出家当和尚、做道士,放下父母家人,放下世间的一切牵挂,隐居深山参禅、打座,成佛成仙。儒家不逃离社会,不抛弃人伦,它就在社会人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去修炼这个“知、止、定、静、安、虑、得”。同时,儒家也有自己的性命修炼工夫,只是未曾彰显,未能很好传承。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是怎么养的? 不清楚。孟子也重视养“平旦之气”。《孟子·告子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平旦”,是太阳露出地平线之前,天刚蒙蒙亮的一段时候称“平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黎明之时。此时人经过一夜的休息,浊气销蚀,清气恢复,心情平静,无所挂虑,情绪稳定,思维清晰。为什么? 因为此时阳气主宰,生命特征处于最佳状态。宋明儒家也曾借鉴佛家和道家的“修定”的方法,故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说。宋儒的“半日静坐”不是虚语,是有修证实践的。孟子的“平旦之气”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清明之气”,《朱子语类》五十九载:“仁父问‘平旦之气’。曰:‘心之存不存,系乎气之清不清。气清,则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则事物之来方不惑……’又曰:‘大者既立,则外物不能夺。’又问:‘平旦之气,何故如此?’曰:‘歇得这些时后,气便清,良心便长。及旦昼,则气便浊,良心便着不得。如日月何尝不在天上?却被些云遮了,便不明’。”“‘平旦之气’,只是夜间息得许多时节,不与事物接,才醒来便有得这些自然清明之气,此心自恁地虚静。”(《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93页。)圣人禀清明之气而生,清晨的静坐,修正“知、止、定、静、安、虑、得”,最易得清明之气,是趋圣贤之途的必修工夫。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曾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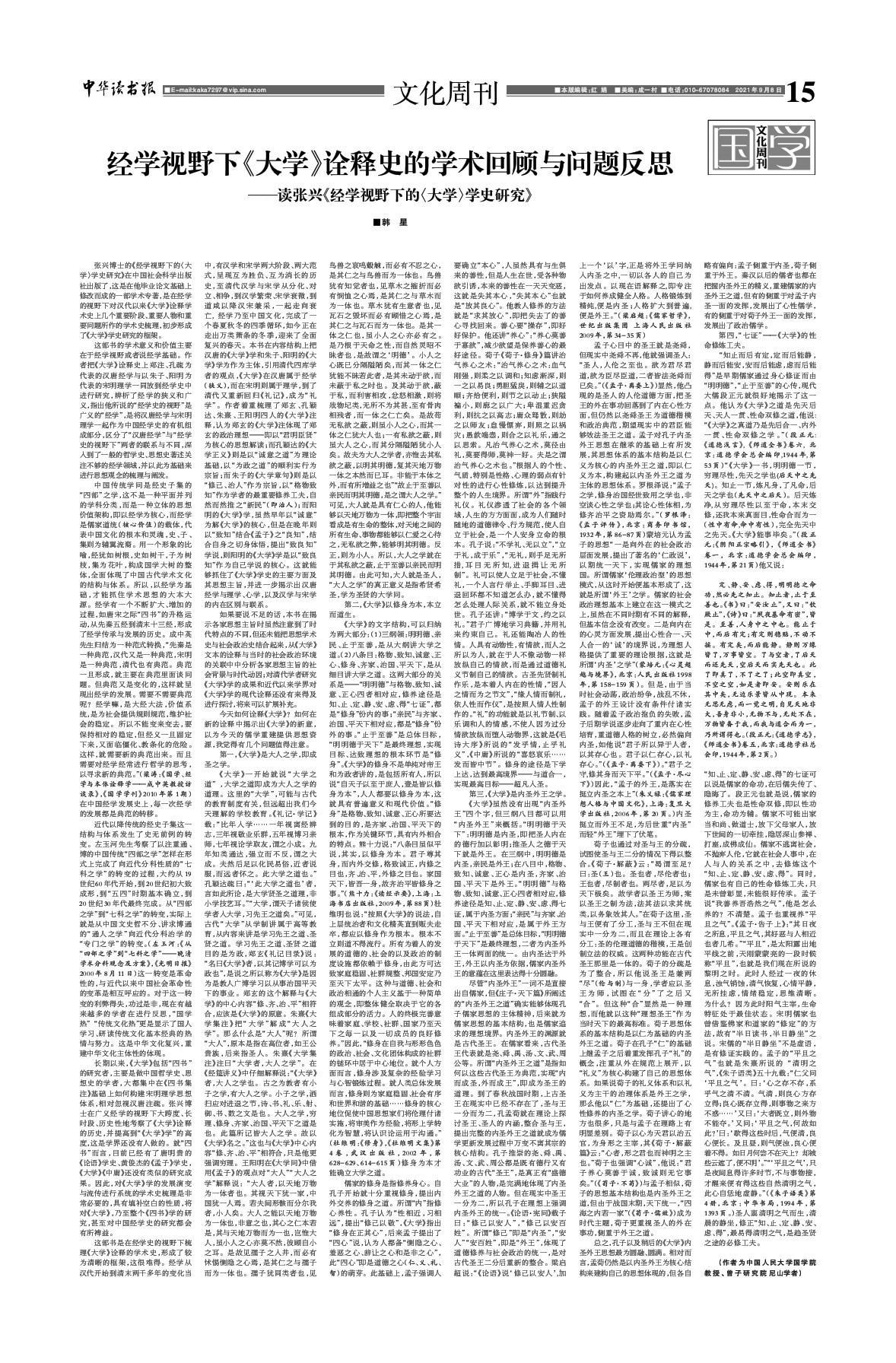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