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引用了赫尔曼·黑塞的一句话:“每一个新的开端都蕴居着一种魅力,它保护我们并帮助我们去生活。”在接下来的演讲中,默克尔与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分享了她年轻时在东柏林生活与学习的经历,并呼吁当代的年轻人在新的环境中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而造成的阻隔,号召人们推倒心中无知与狭隘之墙。默克尔之所以引用黑塞的话,当然是因为黑塞在美国知识界曾经以及依然具有的影响力。
1922年黑塞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悉达多——一首印度的诗》(Siddhartha.Eine indische Dich⁃tung)一书。这是有关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历经各种磨难寻求人生真谛,最终获得解脱的故事。在《悉达多》中,黑塞尝试着以佛陀时代的印度作为背景,展开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小说的主人公悉达多尽管是佛陀同时代的修行者,但黑塞所要展示给读者的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时代精神。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印度和远东的宗教和文化很早便与他的精神发生了关联,而基督教和德国文学传统的思想财富,也深深地影响着黑塞《悉达多》的创作。
一、黑塞早年生平与《悉达多》的创作
赫尔曼·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施瓦本地区一个叫卡尔夫的小城。他于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46岁时加入了瑞士籍。作为诗人和作家的黑塞,深受德国文学的浪漫派传统影响,尽管他的作品多以小市民生活为题材,却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黑塞深感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他在远离尘嚣的瑞士乡间以他的小说寻求心灵上的解脱。他的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辛德》《悉达多》《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黑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由于其作品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遒劲的气势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85岁的黑塞于瑞士家中去世。
黑塞的父亲约翰内斯·黑塞是巴色会(Basler Mission)的传教士,曾经跟随黑塞的外祖父赫尔曼·贡德尔特在印度传教。身为新教传教士的贡德尔特博士也是印度学学者,他曾编写过第一部马拉雅拉姆语(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通行的语言)的语法书。作为传教士的女儿,黑塞的母亲出生于印度,早年便是在椰林旁边长大。黑塞自幼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长大,接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欧洲的宗教、人文教育外,他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也很感兴趣。1911年他曾去亚洲旅行,试图从宗教和哲学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但这次旅行让他非常失望。他对印度精神的理解主要来自他的德文阅读,与印度现实的关系并不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德国人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除去死于饥饿的75万人之外,还有200万士兵阵亡或者失踪,如果算上各参战国的阵亡和失踪人数的话,总数达850万之多。这些牺牲究竟意味着什么? 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和文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并且将视线转移到了东方。这次战争对黑塞来讲是一种所谓“是死是活时期”(Stirb-und-werde-Epoche),不论是作为人还是艺术家,他内在和外在都遭受到了生存危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认识到之前宣扬要拯救世界的西方理性和狂热的民族主义使欧洲文明陷入了危境。当他对可怕的流血和民族间的仇恨表示谴责时,人们却认为他是叛徒而孤立他。他为了更深一层地探求自己的灵魂,开始转而研究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思想,并且通过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的德译而接近中国智慧,进而摆脱自身的困境。《悉达多》就是他研究东方智慧的结晶——一部用散文诗的方式创作文学作品。让人倍感吊诡的是,黑塞的基督教先辈是要到印度去让那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他的《悉达多》却走了另外一条相反的道路,要到东方去寻找人生的解脱之道。
1913年《来自印度》(Aus Indi⁃en)出版。尽管这部书被读者认为是报道黑塞印度之行的一部杰作,但他自己对此不满意,因为对这一古老的文化仅作浮光掠影式的报道,显然是不够的。黑塞内心对东方的向往当然远远超过了一次旅行的经历。早在年幼,他精神上就曾沐浴着东方的异域风情。他后来在《我的信仰》(Mein Glaube)中写道:
我在《悉达多》一书中信仰一个印度名字和一个印度的脸庞并非偶然。我经历过两种形式的宗教,作为虔诚、正派新教信徒的孩子与外孙,以及作为印度神启的读者,这其中我排在最前面的是《奥义书》《薄伽梵歌》以及佛陀的教说。尽管我是在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的氛围之中长大的,但我第一次经历的宗教性的冲动却呈现出了印度的形态,这并非偶然。我父亲、母亲以及我的外祖父都在印度履行着基督教传教的职责,尽管在我的一个表弟和我这一代在认识方面才有所突破,对各种宗教才不再有等级划分,而在我父亲、母亲和外祖父,尽管拥有相当全面的印度宗教信仰的知识,但他们对这些印度形式的信仰仅有不完全予以承认的好感。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将精神性的印度特质,像对待基督教一样完全予以吸收并经历了。
……后来不仅是印度的精神世界,我也认识到了中国的精神世界,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使我认识到孔子和苏格拉底成为了兄弟,我深深为老子那隐蔽的智慧及其神秘的生命力所感染。
除了基督教之外,印度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本小说是黑塞所创作小说中极少以东方作为背景的作品,开始写于1919年,很顺利地完成第一章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至1920年完成小说的第一部分前四章,第二部分的八章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1922年才告完成。1922年10月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印了6050册,一直到1935年才再次重印。其中第一部是献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而第二部是献给他当时在日本的表弟威廉· 贡德尔特(Wilhelm Gundert,1880—1971)的,这位表弟后来成为了东亚语言、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著名学者。
尽管《悉达多》的篇幅不是很长,但黑塞从开始写作到完成却用了三年时间。这期间黑塞也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和人生的危机,这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其家庭环境有关——妻子马丽亚患精神分裂,小儿子患神经方面的急症,最终家庭破碎。1921年的上半年,他还三次专门到著名人格分析心理学家C. G.荣格的诊所接受过治疗,其中一次他还为荣格朗诵了《悉达多》的片段。从黑塞来讲,他创作《悉达多》是42岁到45岁之间,这正是人的一生中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同时也对世界、人生有着成熟的认识。我不认为《悉达多》是一位年轻的作者可以完成的文学创作。黑塞出生的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Schwaben)地区有一种说法,人过了四十岁才会变得聪明。因此德语中有Schwabenalter的说法。同样是施瓦本人的海德格尔有两次在给雅斯 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封信中谈到这个说法:“作为半个施瓦本人,我现在也到了不惑之年,这个岁数应当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去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1931年12月20日)“大家都知道,施瓦本人只有在四十岁以后才会变得聪明,我还算得上是其中一个吧——刚好能够领会,在哲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1936年5月16日)
在创作《悉达多》的时候,黑塞已经有近二十年阅读印度和中国思想史的各种文献的经历。《来自印度》一书,仅仅是有关这个国度的一些外在报道而已。毕竟这样一个国度自他儿时起便吸引着他,《悉达多》一书的完成,可以认为黑塞已经完全进入了东方精神世界的智慧之中。与黑塞其他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以对大部分德语读者来讲具有异域风情的印度作为背景,以悉达多为主要人物,以佛教、道教,也包括禅宗的思想作为探讨内涵,描述了悉达多一生求道的经过,并借此来阐述作者个人与宇宙统一的人生哲学。
这部作品德文版自1922年面世以来,在德国备受欢迎。据苏卡普出版社的统计,至1970年,这部书共销售41万册,被列为黑塞作品中的五大畅销书之一,常年居于销售榜之首。而英译本由于美国嬉皮士运动将之奉为“崇拜之书”(Kultbuch)发行量更大,成为美国书店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之后的日译本的发行量也大大超过德文原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他一直是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德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量达几千万册之多。
二、《悉达多》的情节
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婆罗门之子悉达多与同伴劬嫔陀共同求道,他们按照吠陀的伟大传统在河中沐浴,在神庙中献祭,在禅定中练习着“唵”字呼吸。但这样的每日生活给悉达多带来的却是失望。于是他背叛了父亲的意愿,跟劬嫔陀一起跟随苦行沙门来到林中修行。三年的苦行并没有使他们获得解脱。当两个人见到了乔答摩的时候,劬嫔陀立即为佛陀的讲道所折服,从而立志要追随世尊一辈子。悉达多尽管对佛陀的教义十分赞同,却没有皈依佛陀的道,使他折服的只是世尊那获得解脱后安详的面容和崇高的人格。在悉达多看来,重要的并不是教义等言诠,而是对人生实际的体验,这些都是无法言传的。因此,他走上了独自求道的征程,希望通过自己的体证去寻求生命之解脱、与宇宙之统一。
之后,他经历荣华富贵,纵情欢愉,为所欲为,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妓女伽摩罗,也离开了这种奢靡生活,孤独地走上流浪的路,走向那条象征善恶、美丑分界的河流——多年前正是一个摆渡人将他从苦行的沙门一岸渡到了充斥着欲望的另一岸。
悉达多曾经想过死,但那河水却给了他无限的智慧。河水在不停地流着,时间对它来讲仿佛不再起作用了。在河边,悉达多那沉睡的灵魂猛然清醒,他从河中听到了声音,这是存在者的声音,是永恒者的声音。悉达多终于觉醒了。其后他与摆渡人婆薮提婆一起在河边过着简朴生活。这期间他也经历了他与伽摩罗之子的叛逆,以及他对天伦之乐的超越。
最终他又碰到了行脚僧劬嫔陀——这位追随了佛陀大半辈子的修行者,并未开悟得道。再行分手时,劬嫔陀吻悉达多的额头,他在悉达多的脸上看到跟佛陀一样的微笑。劬嫔陀因此获得了觉悟,并向悉达多鞠了一躬。全书到此戛然而止。
悉达多离开了乔答摩佛陀的言教,历尽万劫,终于以自己的体验获得解脱,证得圆觉。这才是黑塞想要说明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而这一心路历程又必然由自己来证悟。悉达多重视自身的体验,而不是别人的教义等言诠,甚至对佛陀的教义也不例外。作为文学作品,黑塞所塑造的悉达多这一形象对人生的探索与体验,对备受污染的现代人的心灵有着强烈的涤净作用。
三、德语文化传统之中的《悉达多》
黑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写给一个对他仰止的日本青年作家信中专门谈到了欧洲文明对他的意义: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培养保护着我,让我不会由于对当下的精神状况感到绝望而放弃迄今的依靠,去追求印度或其他的瑜伽学说……有时确实存在这样的诱惑,……但我的欧洲教育告诉我,对于亚洲的各种学科……不懂或一知半解的那部分……要予以怀疑,对于真正理解的部分要予以把持。而正是这后者与我自己精神家园中的信条和经验是相近的。
欧洲文化传统对于黑塞来讲,是他接受印度和中国学说的“解毒剂”。欧洲文化,特别是德国文学传统是黑塞文学创作的底色和源泉。
(一)德语文学中的佛陀小说
尽管黑塞由于家庭的原因很早就与印度文化发生的关系,但《悉达多》的产生很难完全归结为完全是异域文化影响的结果。跟黑塞一样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的丹麦诗人和小说家盖勒鲁普(Karl Adolph Gjellerup,1857—1919)由于1906年出版的德文小说《朝圣者伽摩尼塔——一部传奇小说》(Der Pilger Kamanita.Ein Legen⁃denroman)而获得191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的佛教小说。伽摩尼塔的故事发展,也同样是跟乔答摩佛陀平行的。商人之子伽摩尼塔在经历了尘世的荣华富贵和情爱的生活后,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踏上了求道之路,希望能够得到佛陀的教诲而获得解脱。他在旅途中偶遇一个行脚的僧人,同住在一个房间。曾享受过金玉满堂生活的伽摩尼塔对这个跟他讲解佛教教义的出家人甚是不满,希望尽快摆脱他。殊不知这位僧人便是佛陀。伽摩尼塔向佛陀倾诉了自己的不幸,最终获得了解脱。
盖勒鲁普早年的作品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的影响,充满了浪漫派的色彩。自1885年夏季开始,盖勒鲁普从丹麦移居到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几年后,由于受到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他开始着迷于印度佛教。除了《朝圣者伽摩尼塔》之外,他还创作了小说《牺牲之火——一部传奇》(Die Opferfeuer.Ein Legendenstück,1903)、戏剧《女成就者》(Das Weib des Vollende⁃ten,1907)、小说《世界漫游者——三部曲》(Die Weltwanderer.Roman⁃dichtung in drei Büchern,1910)等这些与佛教思想相关的小说。他晚年的作品重又回归到了基督教的传统,继续关注精神的拯救。黑塞对这部德文的作品自然不陌生,早在1910年他就曾论及这部小说:
丹麦诗人盖勒鲁普的传奇小说《朝圣者伽摩尼塔》少了些生动性和轻松愉快,但在印度精神和深刻性方面,上面提到了几部好看的小说跟它是无法比拟的。在这部出色而深刻著作中所体现的真正是一种精神的印度,而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有趣的记录,而是众神和佛陀的神圣印度。《朝圣者伽摩尼塔》不如古老的《薄伽梵歌》或最好的佛陀传奇那么好看,但它却是从对印度智慧最鲜活的领会中产生的,它是真诚且深切的,是以十足的佛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精神虚构出的一个传奇故事。
尽管他认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深刻,但并不认可其文学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悉达多》也是德语文学中佛陀小说的一种延续。
(二)启蒙运动以来“教育小说”的传统
除了在佛陀小说方面与德语文学的承继关系之外,德国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也译作“成长小说”,日文译作“教養小說”)也在黑塞的作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其实除了《悉达多》一书,其他的早期著作如《德米安》(Demian,也译《彷徨少年时》,1919),也都可以归在“教育小说”的范畴。从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开始,“教育”的概念指的是脱离了家庭和国家的角色伦理的个体发展,一般来讲这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是针对一个更高、更积极的目标的发展。而这些都符合悉达多的形象特征。其实,除了《德米安》之外,《荒原狼》(Der Steppenwolf,1927)、《纳尔齐斯与哥特蒙特》(Narzißund Goldmund,也译《知识与爱情》,1930)、《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1943)也都有类似的基本结构。充满天真和理想的主人公与冷漠、现实的世界所形成的对立,使得他不断能“入世”,在他的环境中获得具体的经验,最后与世界的和解,从而获得解脱。
黑塞在《德米安》的前言中写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通往自身的一条路,是一条路的尝试,是一条路的暗示。”德米安说:“如果一个动物或一个人,将他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意志力集中在特定的事情上,那他就会达到那个目标。没有别的。”小说中主人公辛克莱最终达到了神秘之统一(unio mystica),是在他默想的时候与他梦幻的图景相统一时发生的。而神秘之统一是“三层进路”之最高一层。德国作家、黑塞 的好朋友巴尔(Hugo Ball,1886—1927),早在1927年出版的黑塞传记中就对指出了《悉达多》与《德米安》极其类似的主题。
在《纳尔齐斯和哥特蒙特》中,黑塞所强调的将理性视为高于一切的“理性者”(die Vernünftigen)和以敬畏之心作为信仰和情感生活依据的“虔诚者”(die Frommen),这二者的品格同样得到了充分得发挥。纳尔齐斯是修道院教师,一位苦行学者。他治学严谨,信仰坚定,准备将毕生奉献于神。而他的好友哥特蒙特却是一个在天性中有太多浪漫气息的人,他追求官能的享受,是一个奉献于美的艺术家。他们各人走着自己的路,过着自己的生活,并且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侍奉着神,各人也以自己的体会来验证人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自我追求。而在《悉达多》中,这种表面上的对立最终也变成了统一。
悉达多经历了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与已存的社会秩序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要寻找一条与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同相背离的道路。他不仅违忤了让他做婆罗门祭司的父命,也违背了做沙门的誓言,最终也离开了乔答摩佛陀之道,因为这些“权威”的教义并没有真正触及到悉达多的灵魂。摆脱了社会和权威的束缚后,最终他发现了自己内在生命发展之路:他在生命的多样性中寻找到了统一性。这是典型的“教育小说”的结构特征,而并非像某些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体现的是什么《道德经》的朴素观点:
小说主人公最后一个历程正是由于领悟《道德经》而修成正果。席特哈尔塔一生坎坷,他从探索自我出发,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来的立场——探索自我,这种貌似倒退的绕圈环形,实质上却以形象地体现了《道德经》中一个朴素的辩证观点:祸福相倚,有无相生,一切矛盾无不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的发展也无不处于循环往复状况。
如果从德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悉达多》显然更多地是继承了“教育小说”在结构上的特征。
此外,“教育小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历史问题,而是主人公与所处时代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也是他的精神历程。将理性与情感、外在与内心、现实与理想、世间与精神等一系列的对立在理想的整体性中予以统一。悉达多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与迷茫中,在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最终获得了解脱。德国的黑塞研究者赫尔穆特·温特(Helmut Winter)认为:“大约在这一时期的黑塞增强了这样的信念,文学作品也必然是信仰,是作者宗教和哲学信念的表达。《悉达多》首先应当被理解为自我发现的尝试,作为一种艺术家的实验,并以此来阐明自己和时代问题的解决之道。”即便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佛陀时代的印度,悉达多的求道之路也跟佛传很少有共同之处,而是与他的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非常相似。因此,《悉达多》尽管罩着一层印度和佛教的外衣,其实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自我问题。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它后来能一再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之一。
(三)德国浪漫派的文学传统
德国是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浪漫派思潮的发源地,与唤起人文主义力量的古典主义不同,浪漫派唤起的是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如何在自然之中体验、在艺术之中表现这种力量。在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是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的论文《基督教界或欧罗巴》(“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1799),在文中他所要陈述的,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三段式过程,正如他在自己身上所经历、体验和悟解到的。他希望借助美学的方式重新发现基督教,并将中世纪看作统一的文化纪元。而他的诗歌代表作《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1800)以及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802),都以宗教和诗歌般的体验对自然、爱情和死亡做了阐释。
黑塞在《世界文学图书馆》中特别强调了他对包括诺瓦利斯在内的德国浪漫派作家的钦佩。很明显,他的作品也是德国浪漫派传统的延续,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复杂的社会思潮不可分离。德国著名电影剧本作家吕茨肯多夫(Felix Lützkendorf,1906—1990)在他的论文《赫尔曼·黑塞与浪漫派和东方的关系》(“Hermann Hesse in seien Beziehungen zur Romantik und zum Osten”)中集中分析了他作品与浪漫派以及东方精神的关系。吕茨肯多夫在文中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包括《悉达多》在内的黑塞不同时期作品受到浪漫派的影响情况。正因为黑塞对浪漫派的继承和发展,他被后世称作“德国最后的浪漫派代表”。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在东方国家的殖民地的不断增加,欧洲的文学家开始建构他们的东方观。对于德国的诗人和文学家而言,东方成为了理想的“他者”。随现代性的产生而失落了的整体性,以及新的精神性和艺术灵感之源,重新在东方发现。浪漫派的诗人和思想家们,如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1775—1854)以及克罗伊泽(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倾心于东方的“神秘思想”。而正是在18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的梵文文献被翻译成了欧洲文字,特别是德文和英文。这样的一个东方学的传统,一直影响到黑塞。
黑塞的传记作家巴尔认为:尽管悉达多认为语言是不可以相信的,但巴尔依然认为《悉达多》的语言是极其认真的,它那庄严的声调超越了诗歌和思想,“因此我认为,这部书正是因为其‘语言’,而名留青史,它将东方与德意志精神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没有黑塞之前的德语佛陀传书写,没有德语教育小说以及浪漫派的传统,黑塞能写出《悉达多》这样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悉达多》更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传统的回音。
尽管《悉达多》的主题来自东方文化的传统,这除了表现在启蒙以来的“教育小说”、德国浪漫派外,即便是佛传,也接续上了盖勒鲁普的德语佛教小说的风格。因此,黑塞的创作深深扎根于德语文化传统之中,这同样包括这部具有佛教特色的《悉达多》。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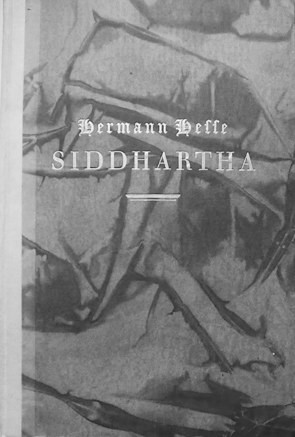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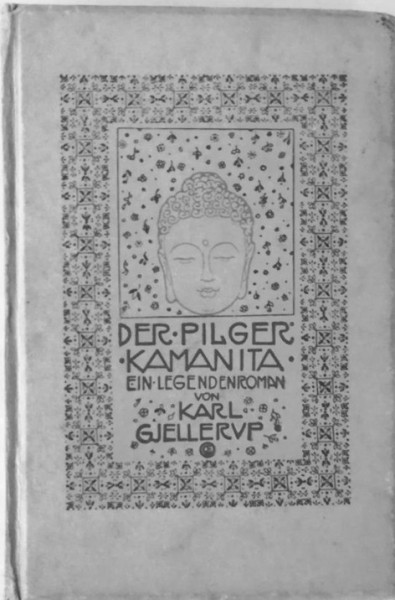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