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提到意识流小说,我们首先会想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与此相匹敌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以及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等一系列世界文学名著。但乔伊斯曾多次宣称他的意识流手法得益于一位名叫爱德华·迪雅丹(Édouard Dujardin,也译艾杜阿·杜夏丹或杜雅尔丹)的法国作家,并说自己的“内心独白”手法就是从迪雅丹那里学来的,他还称迪雅丹为“内心独白的创始人”,而称自己是“死不悔改的窃取者”(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金隄等译)。如此谦虚的坦承对向来傲慢的乔伊斯来说非常少见。作为象征主义诗人、作家兼评论家的爱德华·迪雅丹于1861年出生于法国卢瓦尔-谢尔,1949年逝世。代表作《月桂树已砍尽》(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发表于1887年,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早了三十五年。可见,意识流文学的源头确实可追溯至迪雅丹的《月桂树已砍尽》。但长期以来,这部意识流文学的开山之作似乎被乔伊斯等意识流大师的盛名所淹没了。
国外学界对迪雅丹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国内则鲜有专门论著讨论迪雅丹及其《月桂树已砍尽》,通常是在对整个意识流文学进行综述介绍时有所提及。1990年,柳鸣九先生主编了一套《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月桂树已砍尽》被收入法国部分第三卷,译者为沈志明先生。1995年,该译本又被收入“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第5卷《意识流经典小说选》。作为国内最早也是唯一的汉译本,沈译《月桂树已砍尽》为我国当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基础。不过由于篇幅较短,并且一直未有单行译本和复译本问世,也未被收入外国文学史课程获得讲授和分析,《月桂树已砍尽》逐渐被学界忽视了。直到2020年,沈志明先生主编了一套“先驱译丛”,《月桂树已砍尽》作为“意识流先驱小说”终于重回大众视野,久被忽视的意识流文学之源得到了新的关注和讨论。
那么,《月桂树已砍尽》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作者是如何开创性地使用“内心独白”手法的?“月桂树被砍掉”这一书名源自何处? 有何象征意义? 此书为何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理清楚这些源头性的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意识流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
内心独白:“我思”与“我想”
《月桂树已砍尽》讲述了一个巴黎青年达尼埃尔·普兰思(Dan⁃iel Prince)与女演员莱奥·达赛(Léa d'Arsay)的恋爱故事。“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叙述主人公从晚上6点至子夜(12点)共6个小时的主观情绪变化,使读者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意识活动。”(《月桂树已砍尽》译序,后简称“译序”)贯穿全书的是“我思”与“我想”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活动。小说开头就具有明显的意识流风格: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空气绵邈,天际悠远;人群混杂,熙熙攘攘地影影绰绰地接踵而来;人海一望无际;一个朦胧的黄昏……在混乱的嘈杂声中,在时间的绵延中,在美丽的景色中,在万物自生自灭的幻影中,我突然出现,出现在其他人中间,像其他人一样出现在其他人中间,既有别于其他人又与其他人相像,一个相同的人,在无数幸存的生命中增加了一个相同的人……
迪雅丹的内心独白手法虽是初创,但这一开头描写是极其高明
的。主人公(兼叙述者)“我”由远及近,穿越了广袤的时间与无垠的空间,聚焦于此时此地,从千千万万个“非我”中脱颖而出。这个“我”出现之后,外界万物瞬间成为其次,“我”之所见所闻成为内心所思所想的参照物,“我”的意识慢慢成为主宰,开始流淌起来。“我”通过观察周遭环境,慢条斯理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在4月的一个傍晚,6点,巴黎街道上。
“我”(以下称达尼埃尔)来找朋友吕西安·沙韦纳,相约去广场。在二人边走边聊的谈话中,读者得知,原来达尼埃尔爱上了女演员莱奥,他们约定晚上9点见面。他追求她三四个月之久,为她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还有三百余法郎,但仅仅得到过她的一个吻,始终未能真正确立关系,于是沙韦纳嘲笑他在“搞柏拉图式的恋爱”。谈话过程中达尼埃尔脑海中不时浮现出莱奥的娇媚容颜和曼妙身姿,回忆着他们在一起时的温存,并不时自言自语地表达着对她的爱和思念。
与沙韦纳分手后,达尼埃尔来到一家廉价的咖啡馆,内心开始一系列细碎而不间断的沉思,仅就“将手套放在哪”这一小问题就思量了许久:
跑堂的。餐桌。我的帽子上了衣帽架。脱手套吧;应当漫不经心地把手套扔在餐桌上,扔在盘子的旁边;最好还是放在外套口袋里;不,放在桌子上吧。小节见风度。我的外套挂上衣帽架;我坐下;喔唷! 我累了。等一会儿再把手套放进外套口袋吧。灯火辉煌,红色,金色,玻璃窗闪闪发亮。什么? 咖啡馆;我终于坐在咖啡馆。啊,我累了。
这些嘟嘟囔囔的表达,实则是典型的内心独白,展现了达尼埃尔意念的反反复复,意识“流”走又“流”回来,而这正是人类潜意识跳跃性和不连贯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艾布拉姆斯认为:“迪雅丹将这部小说里的所有情境和事件都按照它们对中心人物意识的影响程度表现出来。”(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在迪雅丹笔下,外在情境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体现和反映。达尼埃尔吃完饭时已近7点半,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计算着时间以免迟到。见到路边豪华的房子时,他内心涌起一夜暴富并携莱奥远走高飞的意念。达尼埃尔偶遇老朋友保尔,得知他要结婚,达尼埃尔既羡慕又不屑,并怀疑保尔及其未婚妻之间是否存在真的爱情。这时,他到家了,收到的却是莱奥派人送来的信,对方告知他别去剧院找她了,而是10点钟直接去她家。获此讯息的达尼埃尔失落不安,担心有人插足他和莱奥之间的感情。于是他打开窗户,想在阳台上欣赏夜景来解闷,而心中眼中却都是莱奥的倩影。
达尼埃尔主观意识的流淌与客观时间的流动并不完全同步,而是有所差异:终于等到8点半,达尼埃尔精心梳洗,换上干净的白衬
衫,打上领带,穿好礼服和高帮皮鞋。一切准备就绪的他,发现还得等一个小时才能出发,索性坐下来,找出了他和莱奥之间的通信,一边读信,一边回忆。他对过去的回忆与对以后的憧憬交织在一起。被爱情和欲望充斥头脑的达尼埃尔并未注意到,莱奥与他的每次通信,几乎都会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向他索取经济方面的帮助。
好不容易等到9点半,达尼埃尔将信件放归原处,满心希望自己今晚能在莱奥家里留宿,渴望与她共度良宵。抵达莱奥家里后,他们谈起了女演员布朗什(Blanche),谈起了莱奥的母亲。后来莱奥困意来袭,蜷在达尼埃尔怀里睡着了。美人在侧,达尼埃尔激动不已,内心泛起层层涟漪。就在他臆想幸福时刻即将到来时,莱奥突然醒了,并提议要去爱丽舍田园大道兜风。然而就连在马车上欣赏夜景的时刻,莱奥也在请求达尼埃尔予以她金钱资助。达尼埃尔则始终在揣测莱奥是否会留他住下,越猜越焦虑。
快到凌晨12点,两人一起回到莱奥家里。莱奥请达尼埃尔脱掉外套稍加等待,他满心欢喜地以为心愿即将实现,结果莱奥以买新衣服为由,又向他索取了3个金路易和50法郎。此时,付出了一切的达尼埃尔以为这下准可以留宿了,便问莱奥:“这么说,您留我过夜喽?”不料,莱奥惊讶地张大眼睛,非常委屈地说:“今晚不行,我求您了,我不能……我确实不愿意……”达尼埃尔大失所望。事实上,莱奥的拒绝并不意外,她不过是为了得到达尼埃尔的钱才与他约会,而从未想过献身于他。而达尼埃尔本身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对莱奥的感情也不完全忠诚真挚,他脑海中常常会想起初恋情人安托妮娅。当最终意识到莱奥看上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钱并感觉到莱奥不会留他过夜之后,达尼埃尔尽管失落无比,但仍表现出非常绅士的样子,他吻了吻莱奥的前额,并将其视为“可望不可即的欢快! 致命的、绝望的欢快!”最后他很识趣地离去了。
至此,6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清醒了,“我”的意识逐渐退出,小说也结束了。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迪雅丹“竭力捕捉稍纵即逝的直觉和琐屑的、幻想的、倏忽不见的印象,以求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冲突和隐秘,即刻画人物潜意识的发泄心理”(译序)。如小说最后,尽管达尼埃尔答应莱奥下次再见,但他内心是很矛盾的:“不,我不再见她了;我不应该再见她了;为什么还要见她呢? 她和我之间产生爱情的可能性永远消失了……”而后达尼埃尔很快转移注意力,想起了另一位女演员:“我的女友布朗什,漂亮的布朗什,令人难忘的布朗什,正在向我伸出她的手。”评论家莱昂·埃德尔认为,读者阅读迪雅丹的这类小说时,实现了在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实际上,读者成功地渗透到了另一个人的意识中,有时甚至渗透到了几个人的内心世界中。
在迪雅丹看来,人的意识时时
刻刻都在流动,不受控制。他借达尼埃尔之口发出感慨:“我多么分心哪! 从来不能把思想集中到一点上;真叫人失望。”正如美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所分析的:“迪雅丹使用的内心独白技巧很像是常规的独白,但是未说出口,是在脑海里,而且很不成型。迪雅丹立刻意识到的,思想能想去哪就去哪,不服从逻辑、随意跳跃,并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托马斯·福斯特:《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译)由于缺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逻辑清晰的故事脉络,在阅读意识流小说的时候,读者的意识也很可能时不时地“流”走——“淹没在意识流中”。
象征:“美人”与“月桂树”
作为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弟子,迪雅丹在《月桂树已砍尽》中也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译者沈志明先生认为,迪雅丹的功绩不仅在于初创内心独白手法,而且“把象征主义的诗歌形式成功地移植到小说中来”,从而开创了意识流小说之先河。而象征主义诗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意象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因此,《月桂树已砍尽》的书名出处颇值得关注:迪雅丹为何以“月桂树已砍尽”为书名?“月桂树”这一意象到底有何深意? 为何月桂树“被砍”了?“月桂树”的意象与达尼埃尔的恋爱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这得从一首很流行的法国民歌说起。这首歌名为《我们不再去树林了》(“Nous n’irons plus au bois”/“We’ll go to the woods no more”),“月桂树已砍尽”正是这首歌的第二句歌词: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月桂树被砍掉了。)对法国人而言,这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经典歌曲。1753年,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创作了这首歌曲。法国民间据此所编的圆圈舞(circle dance)广为流行,尤其是在儿童中间:孩子们围成一个圈,选择其中一个孩子作为“美女”并开始游戏。在第一节歌词中,孩子们边唱歌边跳舞。唱到“参加舞蹈”时,选中的“美女”走到圆圈中心跳舞。唱到最后一行歌词时,她可以选中另一个孩子并让其站到她的左边,这个被选中的孩子将是下一个“美女”。中国民间的儿童游戏“丢手绢”与这种圆圈舞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1804—1876)在自传《我的生活故事》中提到了这首儿歌。那是在她儿童时期,和小朋友们跳起圆圈舞,其中一个女孩唱道:“我们不再去树林了,月桂树被砍掉了。”敏感的乔治·桑听到这里突然悲伤起来:
我知道我之前从未去过树林,或许也从未见过月桂树。但是我大概知道树林与月桂树是什么,因为那两句歌词勾起我很多遐想。我退出舞圈,就为了想象那两句词儿,竟然陷入了一场深深的忧伤。我不想把心事告诉任何人,但我会自愿大哭一场,因为我觉得失去了
那迷人的桂树林,很是伤感……我总是在想象中看到那座树林在遭受砍伐之前的样子,我在现实中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树林。我看见那树林里铺满了新近被砍下的桂树枝,我觉得我恨死了那些砍伐树木的人,因为他们把我永远逐出了树林。(乔治·桑:《我的生活故事》,管筱明译)
乔治·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心灵也非常敏感,这首歌给她的童年留下了悲伤而痛苦的记忆。
后来,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Debussy)在交响组曲《意象集》(管弦乐)第三乐章《春天回旋曲》(1910)中,就以《我们不再去树林了》及其系列变奏为基调而展开创作。这个旋律曾在德彪西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中多次出现,可见这首歌深刻地影响了德彪西的音乐创作,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养分。
《我们不再去树林了》的广泛流行一方面得益于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法国政府的大力推广。法国当代学者研究发现,这首歌实际上暗示了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社会性病严重流行,路易十五下令关闭妓院的决定。在当时的法国,月桂树枝通常被放置在妓院门窗的上方,因而歌词“我们将不再去树林”的字面意思背后,其实指的是“我们将不再去妓院”。这种推测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在西方文明中,“月桂树”有丰富的隐喻义和象征意义。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河神之女——美丽的达芙妮,不堪追逐的达芙妮最后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因此“月桂树”既是爱情和艺术的象征,同时也有强力追逐和强求的意味。
迪雅丹在《月桂树已砍尽》中虽未对“月桂树”这一意象作明确解释,但有几处关于“月桂枝”象征含义的地方值得注意。达尼埃尔第一次遇见妓女是在回家的路上,晚上7时40分左右。路边一个妓女向他打招呼时,他的反应是:“上帝! 快跑吧! 啊! 莱奥,莱奥,我的美人,我的好人……”无论是从内心深处还是身体上,他都表现出决绝的拒绝姿态。达尼埃尔第二次遇见妓女则是在去见莱奥的路上,晚上9点半之后:“妓女开始出现,三个妓女聚在一起聊天;她们没有注意到我;有一个非常年轻、娇弱,不知羞耻的眼睛,撩人性欲的嘴唇!”很明显,此时的达尼埃尔已有所动摇,不仅开始偷偷观察她们,脑海里甚至出现楼上房间里的朦胧幻象。事实上,达尼埃尔爱上的“美人”莱奥是一名三流歌女,她交友甚众,达尼埃尔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她的住处颇有“月桂宫”之嫌。迪雅丹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熟稔象征手法,用“月桂树被砍掉”来暗示达尼埃尔的内心想法亦不无可能。小说最后,达尼埃尔内心对自己说:“不,我不再见她了;我不应该再见她了”(Non, je ne la reverrai plus; je ne la dois plus re⁃voir),与歌曲中的“我们不再去树林了”(Nous n’irons plus au bois)是高度互文的。
柳鸣九先生则是从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差异角度来解释《月桂树已砍尽》的书名的。他认为,虽然书中人物活动的时间是从傍晚到深夜短短几个小时,然而人物的心理活动却具有更大的时间跨度,这一解释显然更加切合原文原意:
在他这段时间的心理活动里,既有对现时的感知,也有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出现了柏格森后来所区分的实际时间和心理时间。小说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时间的差距上,即通过有限的实际时间中的心理时间,表现出更为绵延的实际时间中更多的生活内容,使读者从这个青年这一次毫无结果
的约会看到过去很多类似的约会,看到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他对这个歌女的徒劳的追求与他的精力与钱财的白白消耗,从而对那个象征意味十足、其隐喻来自一首民歌的首句“月桂树已经被砍尽,美人把树枝捡个干净”的小说标题有所领悟。(柳鸣九:《理史集》)
意识流:序幕的拉开
与小说开头那个与众不同的“我”不同,达尼埃尔遭遇莱奥的拒绝后,内心思索道:
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从今以后,像其他人一样,开辟着自己的前程;今天,此地、此时,生活在我身上产生了效应;就是说,我成了一心想拥抱的人;所谓今天,就是想念女人;我的‘此地’,就是接触女人的肉体;我的‘此时’,就是接近女人;这就是我的生活走向。
结合小说开头,“我”最初从“非我”中脱离,最终不得不回到“非我”,回到“类我”,向人的本能欲望屈服。译者沈志明先生认为:“意识流作为艺术形式,体现了作家的人生哲学和处事态度。迪雅丹的意识流作品和某些意识流大师的作品一样,也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名流雅士、侯门权贵个人的命运、孤立的行为、内在的气质,描绘他们对人类状况的忧虑,对生存意义的怀疑,个人事业或爱情幻灭之后内心的矛盾与苦闷。”(译序)因而意识流自然成为他们最富表现力的艺术手段,迪雅丹可谓开创了内心独白艺术手段的先河,从而“拉开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尝试期的序幕”(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
迪雅丹的《月桂树已砍尽》全部是内心独白式的,作者几乎不作任何多余的插话。作家刘恪在《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也认为:“《月桂树已砍尽》在内心独白技巧上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过,在乔伊斯看来,这种手法导致的一个瑕疵在于“当主人公不得不描述外部环境时,这种写法有些不大灵活”(《乔伊斯传》)。1903年,乔伊斯在一个火车站的书报亭里买了这本书,此后便以迪雅丹的内心独白手法为师,并在此基础上修改、精进写法,将内心独白与作者叙述结合,最终成就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乔伊斯后来结识了迪雅丹,并鼓励、帮助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将《月桂树已砍尽》译成英文,不过英译书名《我们不再 去树林了》(We’ll to the Woods No More)借用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的歌名。从这个意义上说,迪雅丹的名声和价值实际上得益于乔伊斯,是乔伊斯的宣传与肯定扩大了迪雅丹的影响,并成为其后意识流小说发展演变的基础。而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则主要以回忆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迪雅丹“意识正在流动”的方式了。
迪雅丹曾对自己的创作技巧作如下评价:这种技巧同舞台演员的台词十分相似,其目的是将人物的内心生活直接介绍给大家,作者不介入小说,也不作解释或评论。这种技巧与传统的独白形式迥然不同:在题材上,它表达了隐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意识活动;在形式上,它用最直接的言语和最有限的句法来表达意识。“1931年,迪雅丹把有关内心独白的论文收集成册,取名为《内心独白及其出现、来源和在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地位》。时至今日,法国人一直把‘内心独白’作为‘意识流’相应的术语加以使用。”(译序)因而,作为“内心独白创始人”的迪雅丹与其《月桂树已砍尽》值得“意识流”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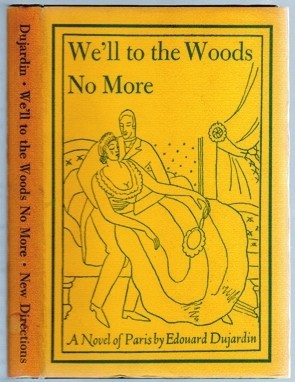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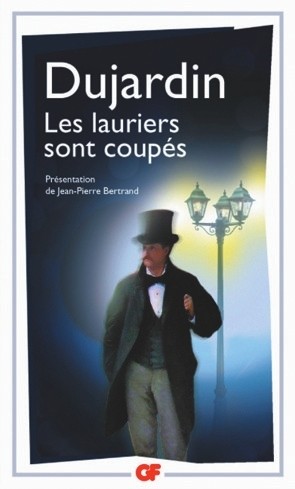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