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人问大仲马写作秘诀,这位法国大作家说“有的,秘诀就是,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百多年后,中国著名作家高建群以老迈之躯,完成了一次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行,七十天时间,汽车里程22000km,护照上盖着十七个国家的印戳,归来后写成了《丝绸之路千问千答》。
楔子
我是在2018年首次进行丝绸之路穿越的。当时有八家电视台组成“丝绸之路卫星电视联盟”。这个联盟要完成一次穿越欧亚的“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聘请我当文化大使。“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之前已经举行过三次了,都是由肖云儒先生担任文化大使,我参与的是第四次的“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
为了这次大穿越,我做了很多的准备。首先就是思想准备:像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坐着车,完成这一次二万二千公里的行程。犹豫再三,我还是坚定决心,拼死一搏也要参与到这次行程中去。甚至做了“身后事”的安顿,把家里的几张银行卡,有的交给老婆,有的交给母亲,我采用中国人的叙述习惯,隐晦地暗示她们:一旦我回不来了,这些就作为你们养老、送终的费用吧。
当年有人问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你为什么能写出《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这样优秀的历史小说,有没有什么秘诀? 大仲马回答说:有的,秘诀就是,历史是一枚钉子,我在上面挂我的小说。
这是我以老迈之躯,完成的一次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行。汽车里程表给出的数目是:“22000km”,而护照上盖出的印戳是十七个国家,是整整七十天时间。
很好,我没有倒毙在路旁,从而像法显高僧说的那样:“哪有路呀,那倒毙在路旁的前人的骨骸,就是路标呀!”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而今,我就龟缩在西安我的“高看一眼”工作室,完成这本纪行之书。
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像压缩饼干一样,将这一堆庞杂的素材压缩到一本书中。换言之,我得找个叙述视角才对。当我在丝绸之路每一个钉子上御风而舞时,总有一根绳在拽着我,把我拽向前面的方向,丝绸之路“千问千答”是一个贯通全书的叙述视角。
当年法显西行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左宗棠西征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古人较之今人,寿限要短一些,想他们到了这个年龄段,该都是齿摇摇、发苍苍、弯腰驼背,一走三咳嗽的垂暮之人了。
法显领着他的四个同学,从长安城出发,穿越了河西走廊,穿越了塔里木盆地,然后翻越大雪山,进入古天竺国,完成了佛教史上称为“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的西行求法之旅。
二百多年后玄奘,就是我们说的唐僧,“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就是说玄奘法师又从中开辟了一条王者之路,进入西域,进入古印度,进入天竺八十六国。
所以这次远行,我首先就带了一张欧亚大地图,还带了一个放大镜。我从丝绸之路一路走过,脚之所向,目之所及,我要用放大镜,寻找大路两边一枚一枚的钉子,然后在这些钉子上兴风作浪,御风而舞。
我还带了自己重要的一本书,一本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开始写,六十四岁生日那天完成的书,叫《我的菩提树》。这本书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次庄严巡礼和崇高致敬,写的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支撑这个大厦的三根支柱——儒、释、道,它们的发生和流变。我要把这样一本向历史致敬的书带着,一直走到世界的十字路口——中亚的撒马尔罕。然后在那个地方向我们光荣的先行者张骞致敬,向玄奘致敬,向道路致敬!
张骞当年凿空西域,就是为了到撒马尔罕去寻找大月氏人。我们的高僧玄奘,他当年为了求得真经,备尝艰辛,一路走到撒马尔罕。面对当时称为葱岭的帕米尔高原天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他在撒马尔罕足足休整准备了半年,这才决心出发,继续他九死一生的征途,他的随行人员基本上都死在了翻越大雪山的途中。在玄奘历尽千难万险、用时十九年的求法途中,撒马尔罕是非常重要的停泊点。所以我要把《我的菩提树》这本书,像纸钱一样,烧在撒马尔罕,向历史致敬,向张骞致敬,向玄奘致敬!
我还带了烧水壶、茶壶、建盏,带了朋友为我准备的最好的茶。带了两双布鞋,这布鞋是家做的,灯芯绒鞋面,千层底。布鞋是老家的村长来西安看我,给我带的。村长是我的本家侄儿。
行前,年近九旬的老母亲,还将治高血压的药、治高血糖的药以及两盒速效救心丸,装在塑料袋里,打入我的行李箱。她还说,你一顿饭都离不开辣子,没有辣子吃,你路上咋活哩。于是她到市场上,买了些干辣子角,回家来焙干,碾成碎片,装了十个罐头瓶子。
行前,我还专程去洛阳偃师的陈河村。在玄奘的故居,我从院子里的那眼井里,满满地打了一桶水,将自己的肚子灌饱。
行前,我还专程去汉中城固的张骞墓。我从张骞的坟头上抓了一把土,带在身上。我神往着在撒马尔罕那个奇异的黄昏,双膝跪地的我,口中念念有词,将这土扬起,将这土撒向风中。
我就带着这几样东西,去实现我的一个梦:世界的尽头在哪里? 让我去看一看。
在这条道路上,几千年来一直有人在走着。在这条道路上有很多匆匆的背影,而我和我们,只是道路上那名不见经传的后来者而已。从张骞开始,我向每一个行走过的人致敬。用我的脚步向道路致敬! 我们将穿越各个文明板块,我们穿越的目的是学习,因为每一个文明板块在历史上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一个持续进步的民族,需要不断学习各个文明板块的智慧,唯其如此,他们才能更有力地向前行走。
罗布泊之谜
从阳关、玉门关西出,面对的就是被誉为“地球之耳”,又被称作“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沧海桑田,鱼龙变化。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为礼物,他送给中国方面一摞从卫星上拍摄的中国地貌照片。这其中有一张是罗布泊的图片。图片上的罗布泊,像一只风干了的人的耳朵,每一圈轮廓线都记载着它逐年干涸的过程,这就是那张著名的大耳朵照片。
在三亿五千万年以前,正如中国的东方有一个太平洋一样,在中国的西方亦有一个大洋,它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它横亘在中亚细亚腹心地带。现在的新疆的大部分,现在的中亚五国,那时候正是这个大洋的洋底。后来地壳变动,海水干涸,大洋露出洋底。地壳的挤压令天山山脉隆起,而洋底则成为草原和戈壁,成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至十万年前时,海水浓缩成一个三万平方公里的水面。它先被称作蒲昌海,后则被称作罗布泊,或罗布淖尔。它位于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东。大耳朵照片显示,这个从浩瀚的准噶尔大洋开始,到硕大的三万平方公里的水面的罗布泊,如今已经干涸,一滴水也没有了。
到了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对罗布泊有过几次闪烁其词的提及,司马迁称罗布泊为盐泽。东汉班固的《汉书》又称之为蒲昌海。
罗布泊之所以被《史记》《汉书》提及,是为了记述当时统治者的拓边之功,记述中原统治者对位于罗布泊深处的楼兰、龟兹等的征伐,对匈奴的征伐。想那时罗布泊从三万平方公里再度缩小,露出许多的陆地了。后来的唐诗中,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句子,证明那时候楼兰已处在一片黄沙之中。
这以后罗布泊便被历史遗忘。它的重新被记起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事情。先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边缘地带探险,接着又有许多西方探险家到那里去,试图揭开这块亚细亚腹心的神秘面纱。而在这些探险家中,成就最大,或者说运气最好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率领他的豪华驼队,以罗布泊人和回族人做向导,在这座死亡之海上游弋。一个刮大风的日子,他们迷路了。大风后来把他们刮到了一座死亡了的城堡面前。湮失了许多世纪的楼兰古城至此被发现,西域探险重要的一页自此揭开。这个时间是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
自此,西方世界“楼兰热”“罗布泊热”“丝绸之路热”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
罗布泊在国内重新成为一个焦点,则是一九八〇年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的失踪,和一九九六年旅行家余纯顺在罗布泊的死亡。彭加木在罗布泊探险时,给同事留下一个纸条:我去找水,吃饭不要等我。尔后便消失在茫茫罗布泊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解放军战士成散兵线,从这一处处沙丘中梳头似的搜索几遍,仍不见蛛丝马迹。这事于是成为一个谜。余纯顺遍踏名山大川,后来却轻轻易易地死在罗布泊中了,这事也十分蹊跷。罗布泊从此成为一个险恶的地方,令人谈而色变。
罗布泊是一个大神秘。仅就它的昨日波浪拍天,万顷一碧,今又黄沙漫漫,盐壳高耸而言,它活像一个有着百变面孔的怪兽。仅就它地狱般荒凉的地表,永远死气沉沉的天空而言,它活像造物主为我们所预兆的地球末日的情景。而它又像一个神秘莫测的险恶非常的地球黑洞,无情地吞噬着送到它口边的生物和类生物。“塔克拉玛干”一词就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至于围绕它而展开的那一幕幕历史大剧,那一个个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则更令人神往和迷惑不解。卓有建树的罗布泊研究专家奚国金先生,曾将罗布泊之谜归纳为十一条。
其中有关于自然地理的追问。比如,第一条:这个曾经波涛汹涌、仪态万方的罗布泊,它因什么原因出现,它又因什么原因消失。第二条:罗布泊四周这些奇异的雅丹是如何形成的,鬼斧神工吗? 天造地设吗? 第十一条:罗布泊是黄河的源头吗?
当然最多的罗布泊谜题还是关于历史,关于楼兰古国,关于千棺之山,关于丝绸之路,关于东西方民族的攻伐战争与商贸交流。下面我们例举几条:
第六条,李柏文书。啥叫李柏文书? 李柏是前凉王朝的一名将领,是当时的西域长史。所谓李柏文书,是这位西域长史写给当时的焉耆国王龙熙的信的草稿。这些函包括两封相对比较完整的信稿和五块残片。信稿是写在麻纸上的,这是所发掘出的前凉时期表述的内容最完整的文书资料,反验了当时的一些历史史实和出土遗址的情况。
而李柏文书之所以被称为“罗布泊热”中的一个未解之谜,是由于对它的挖掘地点的确认。它是一九〇九年三月,日本一个叫橘瑞超的探险家,只身一人进入楼兰地区,在一座不知名的古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楼兰地区有着许多古城遗址,这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李柏文书》是在哪座城里发现的。楼兰城吗? 或者别的城?
日本的学者,英国的学者,中国的学者(例如王国维),都先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推翻前人的见解,争争吵吵了一百年,但这事现在还没有个定论。
第七条,奇异的死文字。在我们以前的年代里,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多少文化消亡在漫漫时光中呀! 在罗布泊及其附近,人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文字,这种文字叫佉卢文。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时曾为大月氏人在今阿富汗一带建立的贵霜王朝官方文字之一,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四世纪中叶,贵霜王朝为鞑靼人所灭,佉卢文也随之在中亚、印度消失了。然而,在三世纪时,佉卢文却在新疆的于阗、龟兹、楼兰等王国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楼兰王国的官方文字。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这就像一条河流,在奔流中突然潜入地下,然后又从另一处冒出来。
第一个在这一带发现佉卢文的是一个英国人福塞斯。时间是一八七四年。福塞斯在喀什、叶尔羌、和田一带,搜集到大批古物,这些古物中有两枚汉文佉卢文合璧的铜钱。因为钱币正中位置铸有一匹马,又因为是在和田一带发现的,所以这种铜钱被称为和田马钱。马的周围则印有一圈佉卢文字,其汉文译意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
佉卢文的再一次发现者是大名鼎鼎的斯文·赫定,时间已经是二十世纪之初。赫定在罗布洼地的西北侧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在这个遗址中,赫定的发掘获得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也有大批魏晋时期的汉文文书和一件佉卢文木简。尤其珍贵的是,在一位汉文文书的背面也写有几行佉卢文。
时至今日,新疆境内发现的佉卢文木简和文书,总的数量已达到一千多件,尤其是以楼兰、罗布泊地区为多,尼雅地区数量更为可观。木简和文书的内容包括楼兰王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国王下达的各种命令,各地地方官和税吏组织生产、交通运输和收取赋税的报告,公文函件,各种契约,簿籍账历和私人信函,等等。这些文书传达了古代的信息,为研究古于阗国、古鄯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也许那每一个正在腐朽的残片,都会成为一篇小说的题材的。那里透露出古代人在处理各种问题时的思维方法,他们在书写木简时的情感等等。例如在一些来来往往的残片中,就记述了楼兰国王对一个税务官鱼肉百姓的不满、谴责和处罚。
而一枚简牍,则是官衙关于一户农民状告邻居的牛吃了他的庄稼的诉讼判决书。该文书用佉卢文、汉文两两对照写成。
这些佉卢文是如何释读的,它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死文字佉卢文也是经过许多学者的毕生探究,后来由一个叫普林谢普的英国学者破译的。
在印度孔雀王朝著名国王阿育王所立的石柱上也有这种古怪文字。同时,石柱上也刻有另外一种我们现在还可以认识的文字。普林谢普将两种文字两两对照,发现它们是同一个意思。这样,佉卢文便被破译了。
佉卢文在它的母国消失之后,在塔吉克追风少年唱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喀布尔消失之后,怎么又跨越遥远的空间,在罗布泊地区死灰复燃的,这委实是一个大神秘。
第八条,小河流域与千棺之山。在民间传说中,说在罗布淖尔荒原上,有一个去处叫千棺之山。那是沙漠的深处,那里拥拥挤挤的大沙山,一座挨一座,茫茫苍苍,直接天际。而在沙山之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棺材。棺材里躺着高贵的武士、美丽的少女。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了,但是这些勇士少女们仍面容姣好,栩栩如生。据说在有月光的夜晚,他们会从棺木中走出,歌唱和欢舞。而在太阳出来之前,又重新回到棺木里,安静地躺下。
据说每一个棺木的旁边,都立着一根高高的胡杨树干。从而令这一处地面像一座死亡了的胡杨林。而那雪白的树干,苗条、高耸,像一群踮起脚尖跳舞的美女。
据说,在这疑团四布的土地上,如果你有意识地要寻找这千棺之山的话,根本无法找到它。那些亡灵拒绝任何的来访者。而见过这千棺之山的人,都是些在迷路的时候,在追猎的时候,在无意之中,与它邂逅的。而这以后,当你存心要专程寻找它的时候,它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在斯文·赫定的三十年中亚探险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罗布人奥尔得克。这个举止诙谐、行踪不定的卑微的人,曾许多次充当过赫定的向导。楼兰古城的发现,就是这位罗布奇人在充当向导的途中,一次刮大风迷路后,偶然发现的。仅就这一点来说,奥尔得克的卑微的身影,就已深深地嵌入近代罗布泊探险史中了。
奥尔得克给人说他见过这千棺之山。他说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他追赶几峰野骆驼,结果误入了这像桅杆高耸的引魂幡,像船只一样排列有序的千棺之山。奥尔得克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可是眼前的这一片恐怖奇特的景象依然叫他惊骇。同时,奥尔得克又是个信口雌黄、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因此,他的关于千棺之山的惊人阅历,听众们对此也只是信疑参半而已。
如果我当时有幸成为奥尔得克的听众,那么我会相信他的话的。因为我也有过与奥尔得克相似的经历。我曾在中苏边界服役,那位置在距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一百公里左右的额尔齐斯河边,也就是中国那雄鸡一样的版图的鸡屁股的位置。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那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我单人单骑,顺着额尔齐斯河往下走。河岸上一片连绵起伏的沙包子挡住了我的去路,于是我只好离开河岸。后来,在一片沙丘的下面,平坦的草场上,我看见了黑黝黝的一片坟墓。这坟墓上的标志,不是像奥尔得克的千棺之山一样,树一根高高的树木,而是用圆木堆积成金字塔般的形状。这些圆木是成长方形形状堆砌而起的,牙口咬着牙口,底下宽些,罩住整个坟墓,越往上,则慢慢收口,直到上面,收成一个顶尖。在这干旱的地方,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木头发黑,发干,黑碜碜的十分怕人。这些木质金字塔的高矮,刚好是我骑在马上的高度。
当我骑着马在这些坟墓中穿过时,不独我,就连我的马也惊骇不已,全身战栗,打着响鼻。这坟墓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属于谁的,哈萨克人的吗? 突厥人的吗? 曾经路过这里的匈奴人的吗? 或者是哪一个西北古族的吗? 我不得而知。我不知道这坟墓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距离一个叫哈巴库尔干的地方大约西北五十公里。但是后来,当我和朋友们再去寻找它,试图做进一步踏勘的时候,茫茫荒原上,哪有它的影踪。
在赫定最后一次探险罗布泊的时候,当他和他的船队,乘着双独木舟沿着孔雀河顺流而下时,船工突然指着水流的远方,高喊一声野鸭子飞来了! 奥尔得克就是罗布语野鸭子的意思,据说罗布人在孩子出生后,将孩子眼中看到第一件东西便叫成他的名字,奥尔得克出生时天空大约正有一群野鸭聒噪着飞过吧! 赫定听到船工的喊声,最初还以为是野鸭子飞来了,接着看到,奥尔得克驾着船向他荡来。这样,奥尔得克又一次成为这个瑞典探险家的向导。
赫定对奥尔得克谈到的这个千棺之山很感兴趣,他敏锐地感到那个神秘所在一定会给他带来许多收获。由于赫定此行的目的是重访楼兰古城,于是在一个叫小河的分岔口,赫定与中国学者陈宗器继续前行,而请和他一道来的一个叫贝格曼的人,由奥尔得克带路,去寻找千棺之山。
这条名叫小河的小河,因为此次踏访,亦成为楼兰近代探险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所在。
因为根据奥尔得克的记忆,他就是沿着这条干涸的、向东南而流的小河故道,遇到千棺之山的。所以,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一行的这次寻找千棺之山之行,也就是沿着这小河故道的。
他们走了许多天的路程,都未能找到这千棺之山。而路途中奥尔得克的信口雌黄,也使贝格曼觉得这千棺之山之说也许只是奥尔得克的虚构和想象而已。甚至到了后来,连奥尔得克本人也对自己的经历产生了怀疑。
然而有一天,正当所有人的信心和耐心被折磨得丧失殆尽的时候,远方的沙丘之上,突然出现一片高耸的标志。奥尔得克指着那个方向,喊道:我没有骗你,朋友!瞧,那里就是千棺之山。
探险队一阵欢呼。驼铃叮咚,载着他们向千棺之山奔去。走到古墓群中,贝格曼跪下来,向亡灵们致敬,请他们原谅这不速之客打扰了他们的安宁。继而,他打开就近的一具棺木,于是,看到一位楼兰美女向他微笑。
小河遗址后来被贝格曼称为奥尔得克的古墓群,共有一百二十具棺材,周围标记了一百多根直立的木标。因罗布沙漠极端干旱,墓葬中的木乃伊令人吃惊地完好。一具女性木乃伊,有高贵的衣着,神圣的表情,永远无法令人忘怀。戴着一顶饰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并为后人留下永恒的微笑。
贝格曼推算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六百年至一千年,在那时,小河地区有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贝格曼的许多独到的分析与见解。都收到他的不朽著作《新疆考古记》中去了。
这个神秘的小河流域,这个海市蜃楼般的千棺之山,自从在罗布奇人奥尔得克一九三四年带领探险家们拜谒过它以后,它便神秘地从地表上消失了。后来的许多贪婪的盗宝人,寻根究底的探险者,都试图找到它,但是都无功而返。直至现在,受这个神秘故事的诱惑,还有人在寻找它,但是它好像已经从地表上消失了一样,无影无踪。如果不是因为有当时贝格曼所拍摄的几张照片,我们甚至会怀疑上面所述的一切只是一个东方的天方夜谭而已。
神秘的小河流域,海市蜃楼般的千棺之山,也许会是揭开这楼兰文明、西域文明的一把钥匙。楼兰文明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消亡之谜,也许就隐藏在这一块秘境中。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有待于后人揭开。而要揭开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小河流域愿意为你重新开放,千棺之山愿意为你重新闪现身姿。
二十三年前我从鄯善县城离开二一〇国道,沿着被斯文·赫定称为“凶险的鲁克沁小道”的路,翻越库鲁塔格山,进入罗布泊古湖盆时,在最后一个有人烟的地方,那个叫“迪坎儿”的小村子,村口,奥尔得克的孙子,拿着奥尔得克与斯文·赫定的合照,并有一幅复制的斯文·赫定为奥尔得克所画的肖像,正在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
而贝格曼在“千棺之山”所发现的楼兰美女木乃伊,她现在则静静地躺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里。她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光洁的前额,马脸一样的面部轮廓,典型的北欧白人特征。碳十四测年测定该木乃伊距现在两千三百多年。专家据此推测,在我们已知的楼兰国历史之前,还有一个“前楼兰”时期。
(本文摘自《丝绸之路千问千答》,高建群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定价:1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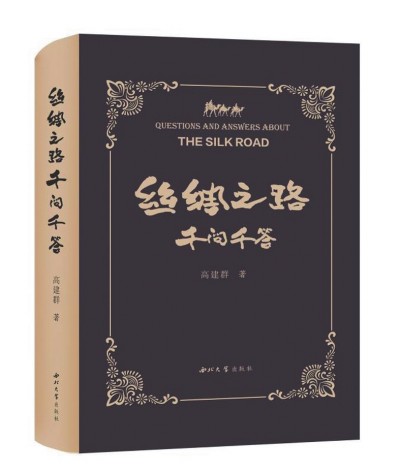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