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研究在中国,从金岳霖先生抗战时期写就《知识论》算起,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了。据金先生自述,给他带来最大名气的是《逻辑》,最能代表自己思想的是《论道》,但写得最困难、出版最波折的则是《知识论》。此书的正式出版要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先生的《知识论》以休谟与罗素为基础,是对上个世纪分析哲学早期知识论的总结和发展。
知识论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既包括自柏拉图以降关于知识定义的争论、笛卡尔所肇始的怀疑论、20世纪基础主义与融贯论之争、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等等,也包括最近兴起的德性知识论、女性主义知识论、社会认识论等等。最近一些年,知识论研究在国内逐渐升温,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李麒麟的《知识归属的语境敏感性》研究认知语境主义的基本架构、主要立场和理论限度。认知语境主义是当代知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基本观点是,“知道”这个动词是语境敏感的。具体来说,当我们说某人“知道”一个命题,这个人就满足我们对语境所设定的一些证据标准,而且这些标准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与之相反,认知恒定主义主张关于知识标准,不应该随着语境而变化,而是确定不变的。柏拉图、笛卡尔都可以算作认知恒定主义的代表。可以说认知语境主义与认知恒定主义之争是知识论的核心议题。
关于认知语境主义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语境类型的区分。一般而言,语境敏感是一个语言现象。例如“我”“你”“这儿”“明天”都是语境敏感词,随着说话者或者说出的时间、地点而发生改变。虽然说话者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敏感是语词本身的敏感所导致的。“知道”所涉及的语境敏感有所不同,和认知主体本身的认知背景、认知状态都有关系。认知语境主义者如科恩不认为语义学本身的敏感性和“知道”的语境敏感的差异对知识论有什么影响,因此对语境敏感不做进一步的类型区分。第二,关于从语境到知识归属的跨越。从“知道”一词的语境敏感性能否顺利过渡到知识的形而上学性质。认知语境主义者如鲍曼(Baumann,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ADefense,Oxford2016)认为需要为从“知道”的语义学过渡到“知道”的形而上学提供一个辩护。认知语境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其基本理论预设。
李麒麟的研究就建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方面,他和科恩一样认为一般交流场景的语境敏感与认知场景的语境敏感之间并不存实质性的差异。另一方面,与鲍曼不同,他认为从“知道”的语义学性质过渡到“知道”的形而上学性质面临内在困难。对于后者,李麒麟主要诉诸关于知道的语言事实的一些标准,否定从语言到知识的过渡,其论证借助了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成果,因此该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哲学和知识论的结合。另外,由于其论证强调了具体场景中关于语言事实的判断,因此也体现了语言学、实验哲学等跨学科方法和成果的运用。该书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第一,介绍了两种主流的认知语境主义立场,并分别进行了批判。第二,选取了知识论中三个重要问题,即怀疑论、封闭原则和可错论,通过考察认知语境主义对三者的解释效力,来展示其根本局限。
根据如何理解“知道”,认知语境主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二元关系的认知语境主义,代表人物有刘易斯(David Lewis)等。他们认为知识是认知主体和目标命题之间的二元关系,该关系对认知归属的语境具有敏感性。“知道”一词的语境敏感性功能类似于“高”“平”等语境敏感的词项,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索引词理论。第二类是基于三元关系的认知语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谢弗(Jona⁃thanSchaffer),他主张知识是认知主体、目标命题和其它(语义)参数之间的三元关系;其中的相关语义参数可以是知识归属标准、替代选项等,这些相关语义参数反映了语境的相关特征。例如“摩尔知道他有一双手”,是因为摩尔知道“他没有残肢”。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对比论。就这一立场本身而言,李麒麟认为认知语境主义者对“知道”所假定的语境敏感机制缺乏合理的语言层面解释。因此,缺乏一个可靠的框架来设定知识归属的语境敏感。仅仅基于关于“知道”的语言事实,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关于知识归属的语境主义。如果对知识取语境解释就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反例。我们通过一些认为基本的案例出发来抽象出或构造出一种知识理论,再用这种知识理论去解释更为普遍的知识事实。但问题在于,似乎并不存在关于“知道”的一般性语境理论。
通常认为,认知语境主义认为对当代知识论有三大贡献:第一、认知语境主义可以为知识的怀疑论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既能解释与怀疑论相关的直觉,亦能保留我们的日常直觉。第二、认知语境主义解释了认知封闭原则。第三、认知语境主义为知识的可错论主张提供了辩护。李麒麟认为上述贡献言过其实,分三章依次进行反驳(第4章“语境主义与怀疑主义”、第5章“语境主义与认知封闭原则”、第6章“语境主义与可错主义”)。不妨把第2章和第3章看作对认知语境论本身的引介和批评,而把第4-6章看作认知语境论解释知识现象所产生的批评。
知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怀疑论。在近代,笛卡尔指出认知者无法区分现实场景和做梦场景,从而无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在当代,普特南构造了缸中之脑,表明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我们自己不是缸中之脑,从而无法有效地拒斥怀疑论。怀疑论对任何版本的知识论都构成了挑战。语境论者主张区分知识归属的怀疑论语境和日常语境,我们不能在日常语境中使用和怀疑论语境同样的知识原则,因此拒斥了全面的怀疑论。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怀疑论的直觉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遍的怀疑,从而表明认知语境论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否认怀疑论的直觉,只关心知识的日常语境,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接受认知语境论,从而表明认知语境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认知语境论并不能很好的处理经典的怀疑论问题。
如果说怀疑论是从证据入手挑战人们能够具有真正的知识这一素朴看法,那么认知封闭原则就是从认知命题之间的关系入手挑战人类获得知识的能力。虽然知识的封闭性原则本身是合理的、可行的,而且对怀疑论的拒斥并不影响封闭原则。但问题在于,认知语境主义并不能为封闭原则提供合理的框架,从而不能为几种主流的封闭原则提供满意的辩护。在解释封闭性原则这一条上,认知语境主义者可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上述两个问题都聚焦于认知主体的能力、证据和标准。知识的可错性却是聚焦于知识本身的特性。关于知识,人们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知识是可错的。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物理学到牛顿时期的物理学到21世纪的物理学,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需要承认以前的认识是错误的。知识的可错性,就反映了知识尤其科学知识的本性。解释知识的可错性也是对任何一种知识论立场的要求。语境论者认为语境主义和可错主义关系密切,甚至可错就意味着以接受语境主义为条件。但是,李麒麟指出,可错主义知识不过是对人类知识本质的一种真实表述,它不需要回应怀疑论。认知语境论从是否能解决怀疑论去批评可错主义是错误的。因此语境主义并非是接纳知识可错主义观念的最佳理论框架。
认知语境主义者希望表明认知语境主义比其他理论在解决上述典型的知识情景中更合适。但李麒麟的研究表明,这一主张是错误的。与认知恒定主义相比——认知语境主义没有明显的、实质的理论优势。语境主义仅仅帮我们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所知为真,在什么情况下所知为假,但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知识的本质。我们不能从“知道”的语义学自然过渡到“知道”的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可以算作是对鲍曼(2016)辩护认知语境主义的一个回应。
李麒麟博士的工作主旨在于系统指出认知语境主义的基本错误,和国际前沿研究进行了实质深入的对话。《知识归属的语境敏感性》是一部结构清晰、论证严密、思想敏锐的知识论专著。李麒麟以自己扎实的研究表明,知识论研究应该有新的方向。默会知识论、德性认识论、知识优先论、社会认识论等等都在国内有了新的研究。从金岳霖先生80年前的《知识论》(1943)到李麒麟《知识归属的语境敏感性》(2021),中国学者的知识论研究正在走向成熟、走向自主,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原创性研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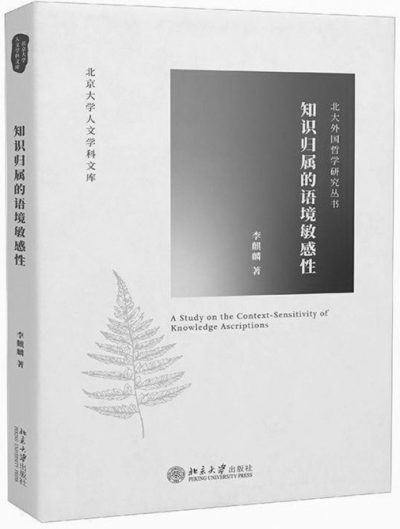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