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澳门诗社召开“诗学与国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聚首澳门,共同研讨诗学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澳门大学荣休教授、澳门诗社社长施议对先生、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仲谋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惠国先生,三人协力展开“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学术对话,回顾了百年词学发展,就二十一世纪词学的未来走向提出若干建议。
施议对:
二十一世纪词学,这是词学之作为一种特定事物的一个特定概念,不同于一般时间概念,不能以一般时间概念的断限为断限,即其起点并非2000年,而是1995年。这是我依据词学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物世代传承及事件推演变换所作断限。今天的讲题,亦以此为断限。自1995至2020,二十五年,既代表二十一世纪词学的现状,亦展示二十一世纪词学的未来。“三人谈”就构成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两大要素,讨论二十一世纪词学的现状及未来,将以1995年为立足点,对于词学本体研究、词学学科建设以及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等问题渐次加以推进。现在开始我们的话题。
张仲谋:
首先,新世纪以来,词学发展最明显的表征,就是词学由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领域,成长为一个较为发达的学科,可用“六艺附庸,蔚为大国”来形容。比如在1995年之前,我参加过两次词学会议,一个会议是1994年秋天在襄樊由王兆鹏先生召集的“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研讨会,应该说研究词学的大部分人都出席了。另一个会议是1995年春天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词学研讨会”,我印象中台湾学者来了十来个人,大陆词学家大概二十几个人,施先生当时刚到香港,没能参加这个会,他们说词学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到了。这就是当时的词学研究规模。
这几年和施先生、朱教授一起参加词学的会议,我印象中还不能说完全到齐了,一般都在二百人以上。主办方印制会议的论文集,要厚厚的五六册。词学研究的人,跟过去相比规模壮大了许多。当然不光是人多的问题,是薪火相传形成了词学研究的梯队。包括1924年出生的叶嘉莹先生、马兴荣先生,1930年代出生的谢桃坊先生。当年吴熊和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环太湖文化区”,就是说过去写词的人,一直到现代研究词的人,主要是江南地区的,江浙沪尤其多。现在则是各地都有研究词学的人,包括比较偏远的地方,词学研究者的队伍扩大了。
其次,新世纪词学内在的一个大变化是词学观念的进步,是从研究理念直到技术方法的一个改变。2003年在杭州大学召开宋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当时我非常有幸跟施先生在一个组主持讨论,施先生在会议中间非常感慨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有些论文,散文和韵文都没有分清,不管什么文体,都是一种分析方法,那怎么行!确实那时候还存在这种现象。比如写词学论文,论辛稼轩,论文的结构就是“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样的三段式。而且谈到艺术特色也是谈用典、比喻等修辞手法,就是说这种方法放到散文上可以,放到诗上也可以,放到别的文体上都可以。作为一篇词学论文,要把词当词来读,比如谈选声、择调,分析词的义脉、过片等等,必须要结合词内在的文体个性来解读。而现在不同了,我们看到现在词学会议的论文,包括很年轻的学者,都具有比较专业的眼光。这是一种新气象,一种词学观念到技术层面的进步。
朱惠国:
关于二十世纪的词学,胡明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梳理。其实在1976年前后,中国的词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确切地讲,二十一世纪词学,是在之前二十年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当然这个发展也是有变化的。施先生讲事件和人物,从事件上来讲,变化非常大,也非常明显。我们不妨先对前二十年作个简单的回顾。
从1976年到1995年,实际上是全面复兴的二十年。这一时期词学研究推进较快。其中有两点给人印象比较深:一是关于宋词风格问题的讨论。施议对先生的老师吴世昌先生,以及施蛰存先生、万云骏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比较大。因为历史的原因,以往对豪放派作了过度褒扬,豪放派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度褒扬,对其他的词学流派就不太客观了。这项纠偏工作在那个时候是必须要完成的,他们这代人把这个工作做了,是对历史的贡献。二是词学理论研究比较发达,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词学批评史著作。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四位老师的《中国词学批评史》,谢桃坊先生的《中国词学史》,都是有影响的词学理论著作,有一定的开创性。
此外,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一些新方法、新理念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词学界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词。按施先生划定的时间,1976年到1995年,我觉得上述两点是比较明显的,当然那个时候文献考订工作也在做。
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词学继续在发展,有什么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觉得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是清代词学研究的比重显著增加。之前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唐宋词,到了这一代,再去补充完善甚至重新开拓,难度在不断增加。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关注不够的清词开始进入大家的研究视野。最近十多年不仅是清代,已经开始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词以前是较少引人关注的,这两年渐成热点,但是真正研究到位其实也不容易。这方面施先生起步比较早,从《当代词综》开始,到后来出版的《今词七家说略》,都是此中的优秀成果。我觉得这是二十五年来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我现在在编《词学》,对这一点是有直观感受的,从十年前开始,尤其到这两年,清代和民国的文章明显增加。
其次是词的文献研究推进较快,取得的成果较多。施先生刚才也讲到考订的问题,其实和考订密切相关的就是文献资料。这二十几年,词学研究推进比较快的大概就是词学文献的收集与考订了。从词的总集来讲,《全唐五代词》是这二十五年间完成的,《全宋词》虽然没有什么变动,但全宋词的补充、作者的考订工作还是有人在做,而且这几年步履加速。最近有人提出,是不是要重编《全宋词》?重编《全宋词》这个工作其实很困难,会面临一些挑战。《全金元词》也是唐圭璋先生编的一部重要的词总集,金词目前还没有太多人关注。《全元词》已经重编了,收词数量比之前有增加,但杨镰先生重编的《全元词》还能不能补充?其实还是能够补充的,因为文献总是在不断的补充修订当中。最近《词学》收到一篇文章,就是补充《全元词》的,有几十首,马上会刊发出来。《全明词》也是之前就有的,到了这二十五年,恐怕不久就会有新的《全明词》出来。饶宗颐、张璋先生的《全明词》有开创之功,但是编出来不久就有人增补,补了厚厚两大册。现在周明初等先生在做重编的工作,可能对版本的选择,收词的范围都有一些新的考虑。相信新的《全明词》出来以后,对明词的研究会有一个推进。这方面张仲谋先生是专家,可以谈得更深入一些。《全清词》的编纂工作也是在前面二十年开始的,是程千帆先生做起来的,但是主要工作是这二十五年完成的。从顺康卷、雍乾卷一路编过来,主要就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张宏生先生在主持。张先生人在浸会大学,但这项工作是属于南京大学的。编纂词总集方面的工作这几年很有成效,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到,可说是词学研究方面很明显的推进。
总集之外,编订词别集的工作也取得明显的进展。编订词别集的工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很发达了,比如说王鹏运编《四印斋所刻词》、朱强村编《强村丛书》,也正是他们的工作,为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文献总是不断发现,不断修订,不断补充的,这样才能够发展。最近十来年,一些比较重要的词集,如柳永的《乐章集》、周邦彦的《清真词》、吴文英的《梦窗词》、张炎的《山中白云》等等,都有新的校注、校笺本出来,有的还出了不止一种,我们讲后出转精,这也是必然的。所以不管是从总集的角度,还是从别集的角度,词学文献工作在这二十五年里,可以说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施议对:
当下词界,张仲谋、朱惠国作为二十一世纪第一代词学传人,都在词学第一线。张教授做明代词学研究,既注重词史之学,亦兼顾图谱之学。朱教授承担词集专题及词调词律研究课题,艳科与声学并重。二位对于词学这一专门学科均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听过二位讲了之后,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词学,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应该怎样定性,比如叫什么时期,或者阶段?当下状况如何?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就目前学界看,对于这二十五年当如何论定,还没提出讨论。
张仲谋:
刚才朱教授讲了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我也想再梳理一下这二十五年的变化,我想是否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一个是从刚才讲的“六艺附庸,蔚成大国”体现了研究队伍规模的拓展。
第二是词学研究、词学批评方法,有点“词学自觉”的意味。以前大家把词和其他文体都是一锅烩的。按施先生的观点,就是要把词当词来读,把词当词来研究,这就是词学的自觉。
第三是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二十多年确实成就比较突出。包括总集、尤其是唐宋别集的整理,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工夫。还有一个就是词学理论的资料整理,当然是狭义的不含创作的词学,这方面的资料整理成果更明显一些,体现为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的续补之作,包括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葛渭君编纂《词话丛编补编》、屈兴国编纂《词话丛编二编》、孙克强编《民国词话》等等,再扩展一下包括《论词绝句二千首》,还有论词书札、论词词等,都有人专门在做。当然总集还有《全明词》《全清词》,最近看到施先生已经给张宏生主编的《全清词·嘉道卷》写书评了。
第四是从词学的断代研究来看,明清词及民国词研究推进得比较快。当时我写《明词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具备条件的。那时手头上还没有《全明词》,只有一个《明词汇刊》。后来见到傅璇琮先生,问到《全明词》书稿,据说在中华书局,傅先生讲什么时候出版还很难说,你可以到中华书局来,拿稿子给你看,当然不能借出。明词到现在发展非常快,已经都很难再找题目了。余意教授写了一个《明代词史》,是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非常不容易。我先出了《明词史》,他的《明代词史》后期资助项目能通过,说明确实有新东西。还有浙江大学的叶晔,非常年轻而且研究势头非常好。吴熊和先生当年出了《唐宋词通论》,然后吴先生的弟子陶然出了《金元词通论》,叶晔现在要做的就是《明词通论》,大概明后年可以出版,他一直坚持做了这么多年,肯定会有新面貌。还有这几年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词学入选的几本著作全在明清和民国,包括我的《明代词学通论》、彭玉平的《王国维词学及其学缘研究》,陈水云教授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曹辛华教授的《民国词史考论》。
第五就是词的音韵谱律之学,确实这几年发展速度比较快。2012年田玉琪教授《词调史研究》出版,谢桃坊先生给他写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词的谱律之学,是我们当代词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环节。当然老一辈词学家,像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都做过相关的工作,但是没有这样成规模的集群式的推进,如谢桃坊先生的《唐宋词谱校正》,田玉琪教授的《词调史研究》和《北宋词谱》,还有朱惠国教授、蔡国强教授目前正在进行的词谱叙录与校证等等。我印象中这五、六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课题,每年都有关于词谱词律方面的课题。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间,有关词谱词律的研究还会推出一批重要成果。
朱惠国:
确实,这二十五年的变化很大,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前二十年,刚才张教授总结的五个方面都是比较客观的。其实从学术风气上看,这二十五年与前二十年也有些不同:前二十年思想相对活跃一些,对宏观的问题考虑比较多;这二十五年则更加重视文献数据的收集与利用,比较多地采用文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注重文献和考据,诗史互证,要求实事求是等等,本来就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回归。这种踏实的学风对词学研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将词学研究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系统工程,那么还原历史事实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很重要,却还不是最终目标,我们还是要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探索一些文学发展的规律。学术界这几年提出反对碎屑的考证,提倡有思想的学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此,这两种学风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都是需要的,关键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
总起来看,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1976年,一个是1995年,对词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前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和社会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容易被察觉;后一个则是词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身发生的变化,不易被察觉。如果要对前二十年和后二十五年作定性分析,目前还有一些困难,因为后二十五年的词学研究还在继续推进,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是能看出来的,相对而言,前二十年比较侧重于反思与探索,后二十五年则在探索中更加注重学科自身的基础性建设。
施议对:
刚才朱教授讲述1976年以来的词学发展。1976年,这是个重要年份。在这之前十年,词学研究基本停顿。再往前推移,即自1949年至1965年,这是一般所说的十七年,这段时间的词学应当怎么评价?张教授刚才所说词学论文结构的三段式,可以概括为:时代背景、生平事迹+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地位与影响。这是十七年间普遍流行的公式。1976年之后,二十年间,经过另外两个阶段,再评价阶段及反思探索阶段,词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有些项目被推上日程。例如朱教授所说宋词风格问题的讨论以及词学理论著作的出版。从整体上看,这二十年是对于之前十七年批判继承的重新评价及思考。但这二十年,世纪词学尚未因1976年的纠偏而步入正途。真正回归本位,应自1995年开始。这就是当下这二十五年的词学开拓及创造。例如,二位教授所说词学本体研究及词学声学研究,就是这段时间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所以,讨论现状,对于这二十五年,应当有个准确的论定。
正如二位教授所说,二十一世纪词学,自1995年以来,二十五年间,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出现不少新成果。这二十五年,在二十一世纪词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开拓期步入创造期,这一时间段担负两个不同的历史使命。开拓期的词学,在于实现由变到正的转换;创造期的词学,在于开辟带有新时代特色的学科理论及布局。前者针对二十世纪词学蜕变所进行的一种批判或否定,着眼点在于破;后者针对二十一世纪词学学科建设的一种创造与发明,着眼点在于立。从开拓期的破,到创造期的立,二十一世纪词学即从蜕变期注重艳科、废弃声学,以外部研究替代内部研究,脱离本位,转而返归词学之正。两个时期的运转,表示二十一世纪词学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正如张教授所说,这是词学本体研究时代,也是词学自觉时代,这就是二十一世纪词学的现状。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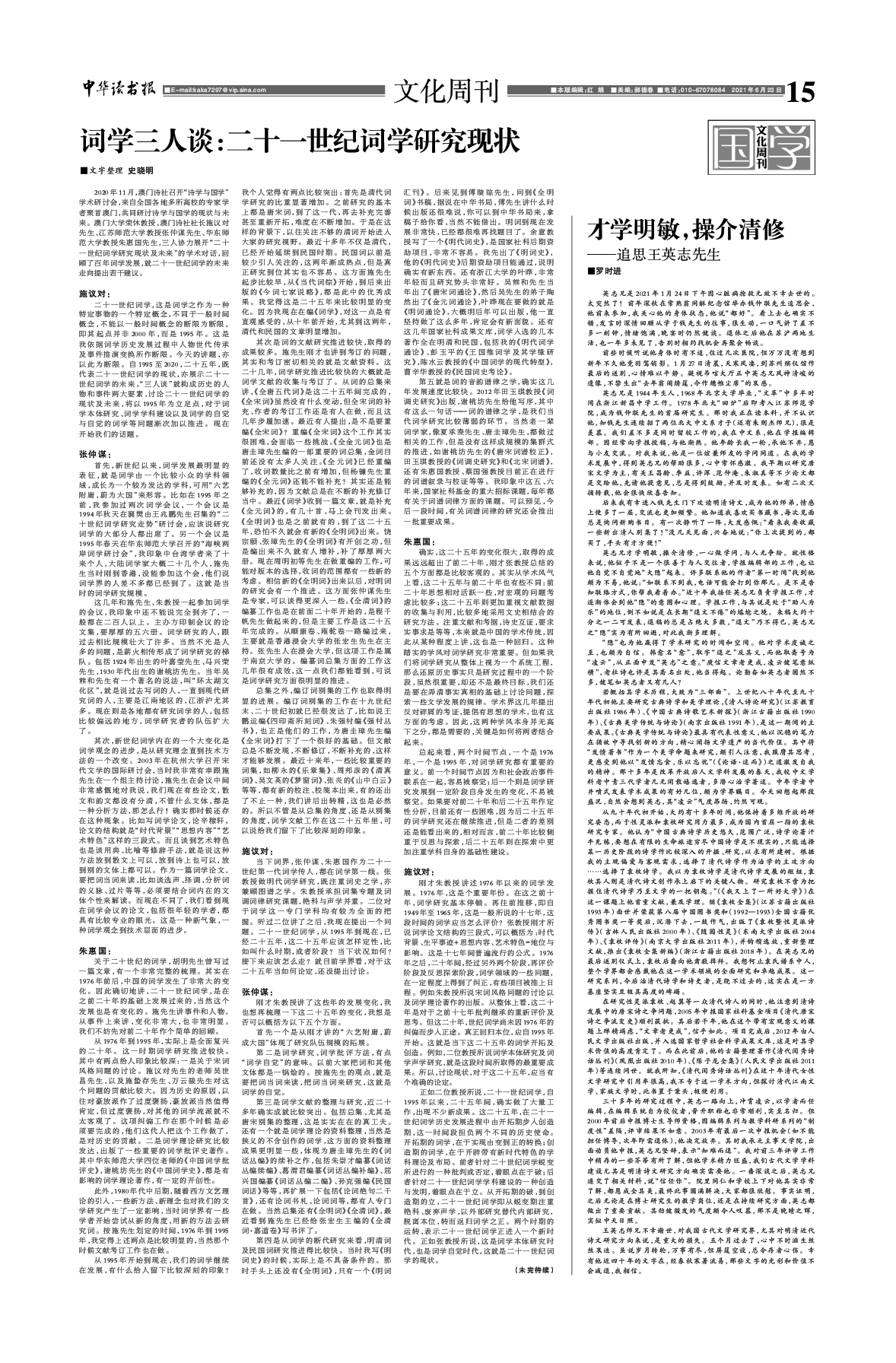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