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喜剧?喜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应该说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不同时代,身处不同的现实生活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肯定存在着一些差别。小说写了两代人在半个多世纪中对喜剧理解的变化和不同的艺术探索。
丑角为戏之有戏、出戏、出彩,作了太多太大的贡献。从古希腊到中国的宋元杂剧,再到莎士比亚、汤显祖、洪升、孔尚任,直到今天的各类舞台剧,他们都是重要的作料、味精,有的甚至是失之即味同嚼蜡的提吊高汤。陈彦的新书《喜剧》的主角,便是小丑。
作为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喜剧》与《装台》《主角》一样,仍记录了戏曲舞台内外中心人物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喜剧》既关涉到戏与人生与生活世界之相互影响、互相成就之复杂关系,亦涉及喜剧之精魂、境界、气魄,要妙之传承与创化。《喜剧》以剧团父子三个唱丑演员的几十年唱戏生涯,展开了一段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
小小舞台,其实永远都牵绊着无尽的社会生活投影。眼见他搭高台,眼见他台塌了。在喜剧演员身上,尤其能显示出这种极具倒错性的殊异况味。小说中的贺氏父子从最传统的秦腔舞台上退下来,融入到了这场欢天喜地的喜剧热潮中。尽管“老戏母子”火烧天希望持守住一点“丑角之道”,但终是抵不过台下对喜剧“笑点”“爆款”的深切期盼,他们的“贺氏喜剧坊”,也进入了无尽的升腾跳跃与“跌打损伤”中。
中华读书报:看到您在后记里说,《喜剧》原名《小丑》,写写停停多年,什么原因?
陈彦:主要还是思考的成熟度问题。这里面的人物、故事我都非常熟悉,2012年就有了动念,初名叫《小丑》。此后多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一部分,但始终感到没有找到能够“提纲挈领”的类似“诗眼”的东西。可能是长期从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原因,无论写戏还是小说,我都希望能有可以“统摄”“点亮”故事和人物的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是一个唱段,像《大树西迁》中“天地做广厦,日月做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那里就是家”;也可以是一个意象,像《装台》中的“蚂蚁”。有了这个可以“点题”的东西,所有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好像瞬间就有了“灵魂”,有了能够聚拢在一起的“精”“气”“神”。断断续续写了多年,就是在“寻找”或者说是“等待”一个可以点题的东西,借它“照亮”和“统摄”整个故事。
中华读书报:疫情中重写这部作品,是从哪里找到了突破口?能谈谈您的经验吗?
陈彦:一部小说,写的虽然是某一类人,某一个群体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但作家总还是想借此表达更丰富复杂的人类经验,所以促使作家动念写作一部作品,形成一种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他生活在其中的现实。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具体的现实境况。在“禁足”期间,我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的疫情,每天都要看大量的相关报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的生活状况,也促使自己思考一些以前可能没有注意过的问题。某一天突然想到多年前动笔的这部作品,发觉自己已经找到了可以“点题”的内容。那就是我为小说写的题记:“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当喜剧开幕时,悲剧就诡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它随时都会冲上台,把正火爆的喜剧场面搞得哭笑不得……”这里面包含着一些对“喜剧”和“悲剧”的辩证思考。有了这个思考,围绕贺加贝的情感和生活故事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那些多年间萦绕于心的故事和种种人物瞬间就鲜活起来。再动笔去写,就有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顺畅感。
中华读书报:书名是《喜剧》,其实是悲剧。贺加贝奋斗的一生全为着梦中情人万大莲,对和万大莲长相酷似的妻子潘银莲很不公平,却难免令人感动,在感情速朽的当下,还有这么专一执着的感情。这是您的理想吧?您的本意是想表达什么?
陈彦:任何时候,专一执着的感情都让人动容,像《牡丹亭》《红楼梦》,历经数百年影响力不衰,这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贺加贝对万大莲的感情,却可能是一种“执念”,一种类似“心魔”的东西,是一种“求不得”的痛苦。出现在贺加贝生活中的这两个女性,潘银莲和万大莲,长相酷似,但脾气、秉性,精神境界差距甚大。万大莲形象虽好,艺术水平也不错,但骨子里却是个贪图富贵、爱慕虚荣的人。她和几个男性的分分合合,似乎也不是出自纯正的感情,而是掺杂着现实的利益考量。潘银莲形象虽与她大致相同,但精神、操行等等,却几乎都和万大莲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不是有意的“设置”,但我还是希望读者能从这两个人物的对照中,思考一些更深刻的东西。贺加贝这样的人,只有远离了对万大莲的“颠倒梦想”,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对这一点,火烧天、贺火炬,包括史托芬都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但贺加贝只有经历了巨大的挫折,才可能领悟到这一点。只可惜他一直“执迷不悟”,演了多年喜剧,最后自己却活成了悲剧。
中华读书报:小说通过喜剧的
发展折射了中国戏曲发展的曲折经历,包括现代元素的融入,让人在阅读中也不免思考中国传统继承还是创新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您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陈彦:小说写的既然是喜剧人物的生命故事,自然就少不了表现喜剧和传统、现实等等重要问题的关系。这也是火烧天、贺加贝、贺火炬,甚至包括南大寿、镇上柏树、王廉举、史托芬等人都在思考的重要问题。什么是好的喜剧?喜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应该说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不同时代,身处不同的现实生活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肯定存在着一些差别。小说写了火烧天、贺加贝、贺火炬父子两代人在半个多世纪中对喜剧理解的变化和不同的艺术探索。这里面自然涉及到继承和创新的问题。秦腔发展到现在,数百年清晰的历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形成了基本的传统。但在数百年间,无论剧作还是表演方式,其实都在变化。每一代的创作者,都有基于自己时代经验的独特的艺术创造。秦腔丰富的传统,也正是这样层层累积变得底蕴深厚的。当然,“变”中还必须有“常”,是守“常”以应“变”。继承传统,扎根现实并指向未来,这是处理继承和创新的最值得认真思考的路径。正因为理解到了这一点,贺火炬才能开出一条喜剧创作的“新路”。
中华读书报:贺火炬是新成长起来的戏曲界的知识分子,他的出走、回归,以及对于艺术的思考、包括他的名字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您在他身上寄托了重振戏曲之风的希望?
陈彦:贺火炬和其兄贺加贝的师承、基本的生活经验是大致相同的,不同的是,随着演出和生命经验的不断丰富,他开始有了对喜剧,对自身的反思。这种反思使得他不满意于贺加贝一味迎合观众而持续“下滑”的表演方式。所以他选择了去大学深造的道路,也因此经历了种种挫折,对喜剧甚至戏曲艺术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逐渐也就明白了如何另起炉灶,将喜剧艺术发扬光大。他最后选择的是和贺加贝不同的路,是一种重新“回归”传统,回到喜剧“正途”的路。不难预料,随着贺加贝的“砸锅倒灶”,贺火炬可能会取得成功。他的选择,其实就是守“常”以应“变”的道路。喜剧艺术的贞下起元,当然也就有了希望。其实每一代的创作者,都可能会有如贺加贝、贺火炬这样选择的差别。个人的选择也必须契合时代的精神,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人承担着“试错”的功能。如果没有贺加贝的反衬和参照,贺火炬可能也不会很快意识到回归“正途”的重要。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复杂的东西,是一种奇正相生的状态。
中华读书报:《主角》中的忆秦娥也在《喜剧》中“真实”地存在,似乎说明戏迷认可的还是角,还是经典剧目。此书与《装台》《主角》有何内在联系?我想在大的宏观方面也体现了您的某些思想吧?
陈彦:不光是《装台》中的刁顺子,《主角》中的忆秦娥,包括《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也都出现在了《喜剧》的世界中。这多少和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发有些关系,是一种“人物再现法”。这样处理,是希望这几部作品之间能够相互照应,共同呈现复杂、广阔的时代生活内容。虽说这几部作品中的人物,职业、生活境遇并不相同,但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比如他们都努力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沉沦下僚”,都秉持着个人之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感。不同群体,不同人物生命状态的共通性,也更能体现一部作品人世观察的更普遍的意义。所以这几部作品故事、人物虽然不同,但却有相互照应与支撑的内部焊接点。一个作家一生其实都在写着一棵树,无论什么题材、体裁,小说还是戏剧、诗歌、散文,都是这棵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读书报:从南大寿、镇上柏树、王廉举等编剧的沉浮,写了编剧的才华和饱读古今中外诗书,也写了编剧与市场、与观众的博弈。您也是编剧,您怎么看待编剧这一角色?
陈彦:其实做编剧和写小说、演戏一样,都需要处理和传统、现实的关系,只是演戏和编剧,可能对观众的喜好,市场等等会有更多的直接的考虑,但其中的艺术规律是相同的,一样要密切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努力学习古今中西的思想和艺术经验,以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优秀作品。就像我在好几个场合说到过的,也是“长安画派”的艺术经验,那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是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无论编剧还是写小说,道理都是如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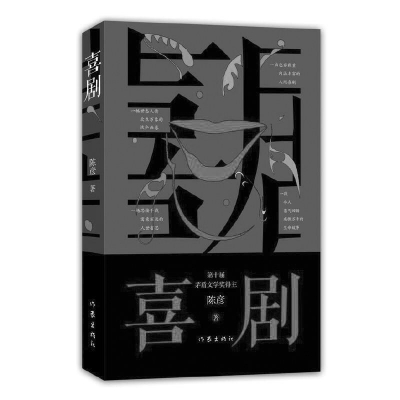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