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命运让我“失语”三年,来到异国他乡,一片荒山野岭,在这里遇见兰波。具体说来,这是在太平洋以东,旧金山背后;这里举目无亲,除了山谷里的野草和黑牛——很奇怪,一只羊也没有——还有在树间上蹿下跳的松鼠,从门前经过,偶尔驻足的梅花鹿;梅花鹿看我一眼,仿佛默默询问:“幽事欲论谁共?”呵呵,这里没有白鹤,梅花鹿似可,何况还有兰波——是的,除了森林、群山,花草、动物,逝去的先人也会从某时某地归来,与你共论“幽事”。而奇特的是,长年在喧嚣的都市生活,常常感觉自己是陌生人、异乡人;但来到这片荒野,这荒凉山谷,我第一次感觉这里并不陌生,初来乍到,就好像从前来过,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受,仿佛被山谷收留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看见”《山谷睡人》开始的——
在这座青青山谷,欢唱的小河
将破碎的银光挂上草尖;
……
一位年轻的士兵,张着嘴,露着脑袋,
脖颈浸在清鲜的蓝色水芥里……
这是从前译过的兰波的诗,诗中的“真实场景”浮现眼前——是的,你“看见”了,在山谷中;而读过兰波的诗歌,领会到levoyant(“通灵者”)的含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兰波在其《文字炼金术》中曾说:“我习惯于单纯的幻觉:我真切地看见一座清真寺出现在工厂的位置上,一支天使组成的击鼓队,天路上行驶的一辆辆马车,一间湖底客厅;妖魔鬼怪,神神秘秘;一部滑稽剧的标题在我眼里现出恐怖的景象。”于是,我愈发珍惜这种“看见”,我以为,这种“看见”背后,其实隐藏一种“相遇”;而这种“相遇”背后,又藏着“可巧”二字,就像“红楼”中“冷香丸”的制作;是的,“冷香丸”或可化解心中的“热毒”。
言归正传。作为一名译者,我以为与原文作者,从本质上是一种“相遇”:就像朱生豪“遇见”莎士比亚,傅雷“遇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从表面看,是一种选择,但各个时代的那么多英、法作者,为何“碰巧”选了他们,我想,在所谓“理性”和“逻辑”背后,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与“感应”。作为一名小小的诗人,卑微的译者,我不敢与了不起的前辈相比,但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亦未尝不可。我想,水平高低是一回事;而心灵相通,又是另一回事。比如,命运将我“流放”至荒野,在这里“遇见”兰波,这对我而言是真实的;而确切地说,是与兰波“重逢”——
自从1986年,在北大金丝燕老师的课堂里与兰波初次相识,到后来,2000年“初译”并出版《兰波作品全集》;之后大约十年再版;而一转眼又过了十年,各种机缘巧合,促使我抛开一切,在异国他乡这片陌生而熟悉的荒野,开始重译兰波——眼看着“重译”顺利进展,已接近尾声,加上友人邀约,我不妨提前“剧透”我的若干新发现。——先说句“题外话”:对于自己“旧译”中的错误和遗憾怎么办?我以为,如果你爱作者、作品胜过爱自己和自己的译文,爱真理胜过爱虚名,尊重读者,胜于自恋,就应当不惜一切,改过自新。当然翻译问题并不简单,不仅是一个黑白对错的问题,这里不细论,单说此次与兰波“重逢”之新发现——
一、“孤儿”的“母亲”与“亲人”
兰波的处女作《孤儿的新年礼物》描写了两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四岁孤儿”,躲在冰冷的大房间,瑟瑟颤抖的“白窗帘”后面——
卧室布满阴影;人们隐约听见
两个孩子温柔伤心的低语,
他们歪着脑袋,还沉浸在梦里,长长的白窗帘瑟瑟颤抖、飘扬
——窗外受冻的鸟儿正互相贴近;它们的翅膀已在灰暗的天空冻僵;新年正随着一场晨雾降临,
拖着她雪白的裙褶,
哭泣着微笑,颤栗着歌吟……
这里说一个小细节:以上倒数第二句原文为:trainerlesplisdesarobeneigeuse,我原先的译文是“展开她雪白的纱裙”,——看着挺美,其实并不准确:plis本身是一个阳性名词:指(裙)褶,褶痕。按原意细想:清晨,风吹雪地,一道道雪痕恰似“雪白的裙褶”。在今天看来,我以为这样译虽“牺牲了”押韵(“纱裙”与上下文押韵),但更准确,也更有诗意。
而“随后,卧室结满冰霜——人们看见床边,丧服散落一地……”——
这时人们才发觉,屋里似乎缺了什么,——这两个孩子没了母亲,没有了甜甜微笑,为他们而自豪的母亲?
在《兰波作品全集》的各种版本中,开篇都是《孤儿的新年礼物》,这首诗歌描述了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的凄凉,并与母亲在世时的幸福作了对比,强烈的反差刺痛人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兰波并没有失去母亲,相反,对母亲的严厉管教产生了强烈抗拒,这一切,也反映在诗歌中:
母亲合上作业本,满意地走了,很为儿子感到骄傲,却没看见她的孩子,
高额头下,一双蓝眼睛里,充满厌恶的灵魂。
这是《七岁诗人》的开篇,短短四句,就出现了两个双关语:一是lelivredudevoir,指学生作业本,或《圣经》。因为devoir的本义是“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作业”。在这首自画像式的诗歌中,诗人所要反抗的,是一切强加于自己头上的“作业”“责任”与宗教“义务”。再者,lefrontpleind’eminences,字面意思是“布满山丘的额头”,这里指隆起、凸出的额头,即高额头;而另一重意思是“高贵的额头”,因为阴性名词eminence也包含“高贵”“杰出”的意思。重译兰波,发现了诸多双关语、一词多义,包括反语和文字游戏,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兰波的精髓:“文字炼金术”的组成部分。比如在《初领圣体》中:“她的灵魂因啜饮胜利(者)而感到平静祥和”。字面意思如此,而vainqueur,“胜利者”一词,发音与vincoeur相同,意思是“酒心”或“心酒”,所以潜台词是“她的灵魂因啜饮心酒而感到欣慰。”又如:在《与诗人谈花》中,“在我们这个西米时代”,原文sa⁃gou,为阳性名词,“西米”,是棕榈树产生的一种淀粉状的物质。近似sagouin,阳性名词,狨猴,引申为“肮脏的人”“粗鲁的人”。
而对于现实中,逼迫、控制他的“母亲”,兰波坚决抗拒——当“七岁诗人”对街上的苦孩子产生“不洁的怜悯”,并将他们当作“亲人”——
母亲便心生恐惧,
为孩子深深的柔情而震惊不已。这很好。她有一双会撒谎的蓝眼睛!
在兰波精神深处,同时存在着两位“母亲”:一位是有着“甜甜微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的母亲——她本该“在夜晚独自俯身,拨开熄灭的灰烬,生一堆火”,本该给孩子们“盖上毛毯和鸭绒被”,本该“把冬天的寒风关在门外边”,然而,她“忘了”!而且“临别之前”,甚至没说一声“对不起”——“她或许没想到清晨会这么冷……”原来诗人从小(“四岁”)就是一名“孤儿”,心中渴求的母爱,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母亲”已经离开人世,“没有了”。家,或人世间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没有羽毛,没有温暖的巢”,“苦涩的寒风中,一个冰雪封冻的巢……而在现实中的“母亲”——“她有一双会撒谎的蓝眼睛!”
“孤儿”失去了“母亲”,“他的亲人”(sesfamiliers)又在哪里?——
唯有这些孩子是他的亲人:
他们光着脑袋,身体孱弱,目光暗淡,
用枯瘦的小黑手捂住眼睛,
在集市上身着气味难闻的老旧衣衫,
谈话中带着痴痴的温柔!
这里familiers(复数)一词,也是指“知交”,精神与情感上“最亲近的人”,“七岁诗人”有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而这位“七岁诗人”——
他不爱上帝,却在昏黄的傍晚,凝视着那些身着黑色工装的人群返回小镇,
听差役敲着三通鼓,大声宣读公告,
人群抱怨着,发出阵阵笑声
……
而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惊呆的孩子”——“孤儿”的亲人还是孤儿,还是这样的“苦孩子”,他们在冬日寒风里,茫茫雪雾中,撅着屁股,“眼巴巴望着面包师,正做着金黄的大面包”,“一张张粉红的小嘴/紧贴着铁网,/对着网眼,轻声吟唱着什
么……”直到——
用力过猛,他们挣裂了短裤,——贴身的白衬衣在冬日寒风里,瑟瑟颤动。
值得一提的是,兰波的父亲弗雷德里克·兰波(FrédéricRimbaud)是一名法国步兵军官,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撒丁岛战。而父亲在兰波的生活与诗歌中,始终“缺席”——兰波在给魏尔伦的信中,称自己的母亲为“寡妇”,其实当时他的父亲还活着,只是一直不在家里。而除了“孤儿”“母亲”“兄弟”“姐妹”这些称谓,“寡妇”一词在兰波的诗歌中也反复出现,比如在《布鲁塞尔》一诗中:“正如阳光中的玫瑰与冷杉/这小寡妇的巢穴”(Cagedelapetiteveuve)……/这是怎样的鸟群……”这里的“小寡妇”原来是指下文的“鸟群”——在兰波眼里,这些鸟儿和他一样流落异乡(布鲁塞尔),失去伴侣,仿佛“小寡妇”一般孤独。而在《高塔之歌》中又感叹:“啊!可怜成千的孤魂,鳏寡孤独”(Milleveuvagesdelasipau⁃vreame),其中veuvage为阳性名词,意指“鳏居”“孀居”,同样是指灵魂失去伴侣,如鳏夫、寡妇一般悲伤、孤苦。
简言之,通常在人们心目中,一提兰波就是“反抗”,是的,没错,但反抗精神之底色,竟然是“孤儿”“寡妇”一般的孤独,对于“亲人”“深深的柔情”与“不洁的怜悯”。而所有这些,兰波从不挂在嘴边,或用“反语”(如“不洁的怜悯”),或通过具体场景呈现。
二、黑色幽默:“精致优雅,/让我失去生命。”
1995年11月,由阿格涅斯卡·霍兰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关于兰波和魏尔兰的传记电影《全蚀狂爱》在美国上映,轰动一时,尤其是莱昂纳多扮演的兰波给人印象深刻:处处风流倜傥,桀骜不驯。但我总感觉貌合神离,其原因是出于对兰波的误解——兰波是怎样的人,不是谁说了算的,也不能凭空想象、猜测。而想要真正了解诗人的性格及内心,除了研究其自传,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研读他的诗歌本身。而细读兰波的诗歌,不难发现,其实兰波分明是个细腻、敏感,甚至腼腆、害羞的少年;只是为了掩饰着一切,才故意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传奇故事》“十七岁的年龄,什么都不在乎”)。而这种“掩饰”却不过是“欲盖弥彰”——诗歌正是这样一种悖论。而此次重译兰波,最让我震惊的,还是《高塔之歌》的开篇第一节:
闲散的青春,饱受奴役,精致优雅让我失去生命。
兰波原本“精致优雅”,然而诗人对此大为不满,每每自嘲,让自己陷入尴尬、可笑的境地。然而尽管如此,我以为真实的兰波,与莱昂纳多演绎的那个“狂野”少年大相径庭——不是说兰波不“狂野”,而是他同时包含着狂野的反面:内敛、含蓄,温柔、腼腆。诗人的内心从来不是单一的,充满矛盾、冲突且浑然如一。而仔细研究原文pardélica⁃tesse,又有新发现:这个词通常是褒义,指精神气质的精致、优雅,对外界事物及他人的敏感。但也包含贬义,指对自己的过度要求,造成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过分看重自己的名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过分在意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在兰波的诗歌中,显然是指后者。从兰波的诗歌总体来看,各种对立的情感相克相生:一方面有诸如《铁匠》《巴黎战歌》《巴黎狂欢节或人口剧增》《米歇尔与克利斯蒂娜》《让娜-玛利之手》这样的革命诗歌,充满铁血与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如前面提到的《孤儿的新年礼物》《惊呆的孩子》,还有《奥菲利亚》《山谷睡人》,画面凄美,充满柔情。而这里我想探寻的是,同一首诗歌或作品中的自嘲和自我颠覆,造成的一种非常超前的“黑色幽默”——如兰波在《地狱一季》中所说的:“必须绝对现代。”——回头看,兰波诗歌和精神气质中的“黑色幽默”,绝对超前。
比如《在乐曲声中》的“我”,出现在奏乐的广场,花草树木,“一切都那样规规矩矩”,“花园中央,军乐队摇晃着圆筒军帽,/和着短笛华尔兹的节拍……”
——我呢,像个大学生衣冠不整;
绿色的栗树下,一群机警的女孩
早已发现,她们笑着朝我转过身来,
大眼睛里,流露出妩媚的神情。
我一言不发:痴痴地望着她们白皙的脖颈,披着疯狂的发绺,潜入她们的短上衣和清凉装束,从圆润的肩膀,滑入神圣的背后。
迅速脱去靴子、短袜;
——激情似火,燃遍我全身。她们觉得我很可笑,并悄悄议论;——我感到阵阵亲吻正靠近我的双唇。
这里,“她们觉得我很可笑”;在描述“自画像”时,兰波从不忘记自嘲。
又比如在《七岁诗人》中有这样一节:
七岁,他开始写小说,
写大漠自由放浪的生活,森林、太阳、河岸、草原!
——他开始翻阅带插图的小报,红着脸
看那些嬉笑的西班牙女郎和意大利姑娘。
当邻居工人的女儿走过来,她八岁,
栗色眼睛,身穿印第安布裙,这个野姑娘从一个角落,
一下跳骑到他的背上,甩着小辫子,他在她下面,猛咬一口她的屁股,是的,那个女孩从来不穿长裤;被她一顿拳打脚踢之后,
带着她皮肉的滋味回到小屋。
可见,“七岁诗人”在此遇见了“小冤家”,他们的爱恨情仇或被以往的专家学者所忽略。呵呵,开个玩笑,我以为,这一节绝对是“黑色幽默”的典范,也是对“精致优雅”的颠覆与嘲讽。
1966年,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曾编辑出版过一部《黑色幽默文集》(Anthologiedel'humournoir,但愿有识之士能够找来翻译),其中就收录了兰波的唯一一篇日记体短篇小说《圣袍下的心》(片段),小说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名十八岁的修士的初恋,开篇即是“噢,蒂莫狄娜·拉比奈特!今天,我又穿上了圣袍,我于是再度感受到往日的激情,如今它已在我的僧袍下冷却并沉睡,而一年前,它曾激荡着一颗青年修士的心!”——通篇“精致优雅”,文辞华丽,感情炽烈,且圣洁、虔诚;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铺垫”,到头来,闹出一个大笑话:修士被姑娘拒绝,陷入丢人现眼的尴尬境地——“从今往后,我将用诗歌抚慰我的伤痛;十八岁的爱情的殉道者……今天,人们又给我披上了圣袍……对于我珍藏心底的这份残酷而又亲切的真情,我将忠贞不渝……况且,我生来便是为爱情与信仰存活!——或许有一天,我会回到这个村落,说不定我还能有幸向我亲爱的蒂莫狄娜忏悔?告诉她,我至今保存着那段甜蜜的回忆:她给我的那双袜子,一年来,我始终没有碰过……那双袜子,我的上帝啊!我会穿在脚上,直至走进您的天堂!”——而所有这一切,依然是“铺垫”,若问这位神蒂莫狄娜为何要送他袜子?因为他原先的袜子“有味儿”,味道太难闻了,在情人家里做客时,让人家忍无可忍。所以,满篇的“抒情”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类似的“黑色幽默”,反复出现在兰波的诗歌中,比如:
流浪(幻想)
拳头揣在破衣兜里,我走了,外套看起来很神气;在天空下旅行,缪斯!我忠于你;哎呀呀,我也曾梦想过光辉的爱情!
我唯一的短裤破了个大洞,——
正如梦中的小拇指,
我一路挥洒诗韵,
我的客栈是大熊星,星辰在天空
窸窸窣窣传来回音。
坐在路旁,我凝神谛听,九月的静夜,露珠滴湿我的额头,如浓烈的美酒。
我在幻影中吟诵,拉紧破靴上的皮筋,像弹奏竖琴,一只脚贴近我的心!
这里的“神气”“缪斯”“梦中的小拇指”和“破衣兜”“唯一的短裤破了个大洞”“破靴上的皮筋”放在一起,“相得益彰”,别具一格。又如《妮娜的妙答》,前面洋洋洒洒,做了大段充满诗情画意的“铺垫”,诸如:“爱上乡村,/你四处撒种,/有如香槟泡沫,/你狂笑不已……”这里“爱上乡村”,原文Amoureusedelacampagne,同时也是“乡村的情人”;而“撒种”,原文Semant,为动词的现在分词,发音如同s'aimant,“彼此相爱”。兰波的诗歌,随处暗藏玄机。而随后继续“铺垫”——
夜晚?……我们重返白色小路;小路四处游荡,像一头吃草的动物……
直到全诗末尾一句,妮娜只开口说了一句,画龙点睛:“我的办公桌呢?”
时至今日,我甚至将会不会自嘲,是否懂得“黑色幽默”看作判断一个诗人真伪的标准。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有没有点儿“黑色幽默”精神,不仅关乎一个诗人的真伪,甚至关乎一个人能否活下去。呵呵,“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三、从隐藏的“告别”,到荒野“失语”
此次重译兰波,一不小心,已投入半年,人还在深山荒野,翻译还在进行中,逐字逐句,温故而知新——原来译诗和读诗一样,不仅可以认识诗人,还可以反观自身。而我这才发现,兰波在之前的诗歌中,已流露出“心生去意”。比如《高塔之歌》第二节——
我暗自思忖:你就这样,
从公众视野消失:
并不许诺
无上欢愉。
什么也不能阻止
你庄严隐退。
在《地狱一季》的《永别》中,诗人叹道:“已是秋天!——但何必怀念那永恒的骄阳,既然我们已决心发掘神圣之光,——远离死于季节轮回的人群。/秋天。我们的船行驶在静止的迷雾中,转向苦难之港,火焰与污泥点染着那座大都市的天空。”然而,最终,大都市(指伦敦)的幻象消失,眼前只见“腐烂的衣衫、淋湿的面包、酩酊大醉……”诗人最终幻灭,感觉自己走投无路,于是远离了故乡,连同“欧洲文明世界”,连同“将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万种柔情”,走进荒野,而于此同时,不到20岁的诗人兰波,就此放弃了文学,结束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诗人生涯”。
从兰波日后的书信(地址)来看,兰波的足迹大约如此:16岁离家出走,从故乡小城夏尔维勒(Charleville)来到巴黎,之后随魏尔伦一起去了伦敦、布鲁塞尔流浪。1873年7月10日,在布鲁塞尔,魏尔伦醉酒发狂,开枪打伤了兰波,之后兰波回到故乡夏尔维勒。随后再出发,越走越荒凉:从塞浦路斯,到非洲的亚丁;从亚丁到哈勒尔,直到最终得了绝症,膝关节恶性肿瘤,“右腿肿得像个大南瓜”,不得不截肢,而最终也未能挽回诗人年轻的生命——兰波1891年在归国途中,死于马赛港,年仅37岁。
这些日子,我在荒野“遇见”兰波,从字里行间,跟随他的足迹远行,并从一些影像资料中进一步了解到:兰波在茫茫非洲荒漠,漫长艰苦的旅途中,跟当地游牧民族学回了隐忍:学会了不说话,喝最少的水(旅途中严重缺水),在荒凉与寂静的包围中,学会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交流。然而,也正是在荒凉深处,诗人开始取悦自我,而不必取悦他人;只需看天色,不必看人脸色。在当时或外人看来,兰波是个失败者,而且一败涂地,直到生命结束,然后,后世的人们却一代又一代,跟随着他的文字,他的足迹,寻找诗歌与生命的真谛。
兰波生前之孤独,身后却“涌来”无数追随者。这便是诗人的宿命。而作为译者,我有幸在荒野“遇见”兰波,才发现当人们心底荒凉,就想去荒凉深处,“更向荒唐演大荒”。然而,荒凉并不荒唐,而恰恰相反,践行了诗人当初的预言或梦想:“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感觉》),或者说一语成谶,如兰波在《地狱一季》中说:“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我进入了含的子孙的真正王国。”而这里所说的“含”(Cham),正是《旧约》中黑人的祖先,挪亚的第二个儿子,因不尊敬父亲而受到诅咒。兰波也是如此,饱受命运的摧残。然而,他流浪的心思并没有改变,正如1885年1月15日,兰波在非洲亚丁给家人的信中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别指望我性情中的流浪气质会有所减损,恰恰相反,如果我有办法旅行,而不必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工作,以维持生计,人们就不会看见我在同一处住超过两个月。世界很大,充满了神奇的地域,人就是有一千次生命也来不及一一寻访。我想存个几千法郎,每年去两三个不同的地方,过着简朴的生活,做一点小生意维持开销。然而总是住在同一个地方,我总感觉到非常不幸。总之,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去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他们的生死都与其愿望相悖,也不指望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诗人就是这样,“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而这“毒药”也包括绝尘而去,终身自我流放,远离故土,远离文明世界,啜饮荒凉,直到失群失语,不再用文字而以生命,不再用声音而以沉默,回应世俗喧嚣,探寻人生真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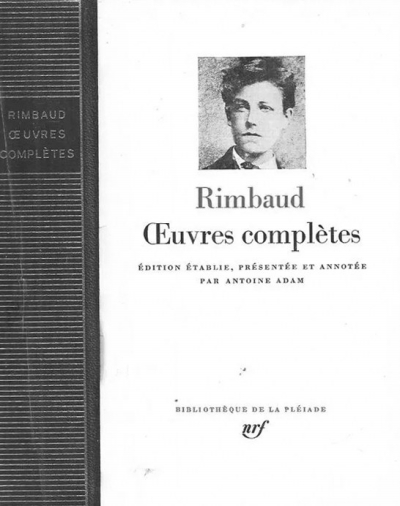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