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字的相遇,突然召唤起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那些穿透《时空之间》的光,照亮、揭示、打开每一个时刻和世界:无论是天空透过水滴的色彩,还是静夜中令人陶醉的花朵芬芳。
与非凡的事物相遇,往往会被它照亮,正如此刻——我读到人文地理学者、诗人叶超的随笔集《时空之间》序曲。在作品中,我们发现艺术本身的一种自我揭示,打开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遇到了超越作品的东西——这种自我揭示照亮了作品所处的世界,也照亮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光芒带来的体验转折一直是诗歌的目标。与文字的相遇,突然召唤起我们自身存在的意识,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纯真之歌》:“从一粒沙看到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天堂,从手掌看到无限,从一小时看到永恒。”那些穿透《时空之间》的光,照亮、揭示、打开每一个时刻和世界:无论是天空透过水滴的色彩,还是一口酝酿味道的酒,还是静夜中令人陶醉的花朵芬芳。一棵树、一座山、一座房子、一声鸟鸣都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冷漠,而拥有倔强的生命原力。
这种光芒,继续折射在第二章“人文与地理”的交相辉映中:认识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态和复杂的,强调人类经验和意义在理解人们与地方、景观、自然和建筑世界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段先生一样,《时空之间》彰显了“现象学”“诠释学”“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但是他避开了概念性标签,而是直接走向具体的、现实世界。因为我们已经在生命世界之中,我们与它同在,无论是否“被抛入”:天空与云彩、风与雨、大地与岩石、动物与植物、朋友与陌生人也同在。我们已经属于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了对世界的关怀和照料之中。因此,正如哲学产生于生存的释放,光芒是承诺和参与的象征——我们对生命的承诺和参与,产生了求知欲;而只有拥有沉思的自由时,光芒才会出现。
《时空之间》的第三、四、五章就是这种承诺和参与,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诗歌作为空间实践的艺术——拉近人与大地。在“时间与空间”中,在“历史与世界”中,在“写作与生活”中,我被感动了,被影响了,被生命的原力打开了。它不需要我犹豫,不需要我的决定,是生命直接进入视觉,是生命简单而又亲近地“在那里”。我已经在光芒中摇曳,和生命的原力合二为一。它不需要庄严的态度和玄奥的博学,也不需要罕见的情境和特殊的方法;它是简单的醒悟,在任何可能的时空之间;它产生于生命的惊讶和奇妙,所需要的只是一束光照亮林中地。
然而,在批评者看来,这似乎充满了玄虚、神秘和主观臆断。人文主义地理学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辉煌之后,逐渐转入低潮。相反,一系列新的、“后的”概念正在涌现,这些自由、流动、难以预测的空间结构产生了分散的网络,更多的强调“地方、思想、人”之间的变异,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时空限制和在地性。甚至,人文主义的长期盟友——现象学,也逐渐放弃了古典的浪漫,走向了后现象学和批判现象学:人文主义在本体论上是欠缺的,因为它没有建立地方的主体性,只是把客观空间的一部分与主观的、想象的、情感的概念结合起来。
作为生活、思考、体验的生命,我们是什么,是与我们生活的地方密不可分的:生活充斥着与地方交织在一起的活动、事物和他者;地方仍然是人类生活的锚定,它能存续生命,提供空间秩序和环境认同。只要生命还没有变成一段代码,只要生活世界还没有成为虚拟的、非物质的和二手体验的,人的身体总是地方性的,总是在时空之间,与他人一起过着特定的生活。在地存有,人性才变得真实;也正是通过我们的参与,地方才形成了自己的意义,仍然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文精神的呐喊“人类所有的思考和渴望都是为了让世界更接近自己”;我们要照料自己的生活,关怀生活的地方。
最后,就在你回头的那一刻,那地方,就是归宿。这是最后一章“归宿”的最后一句。我合上书,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然后安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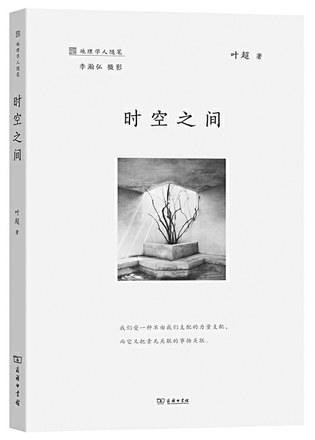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