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夏末,一篇震惊大西洋两岸文坛的雄文——《拜伦夫人的生活真相》(“ThetruestoryofLa⁃dyByron’slife”)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和英国《麦克米兰杂志》同时发表:文章指控英国诗人拜伦与其同父异母之姊奥古丝塔·利(AugustaLeigh)曾发生乱伦关系。文章的作者是以《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享誉世界文坛的斯托夫人(HarrietBeech⁃erStowe)。
斯托夫人声称,《拜伦夫人的生活真相》一文创作动机源于拜伦情妇特雷莎·圭乔利伯爵夫人(Count⁃essTeresaGuiccioli)此前一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回忆录《回忆拜伦勋爵》。书中将拜伦夫妇半个世纪前沸沸扬扬的“分居事件”归咎于拜伦夫人“冷酷无情”,并指斥拜伦夫人“是女性中的异类,是道德败坏的余孽”。由于拜伦夫人(1792-1860)生前对个人隐私一直保持缄默,斯托夫人决定将19世纪50年代与拜伦夫人的谈话公之于世——她要为生前饱受耻辱、身后横遭诋毁的拜伦夫人充当“文学代理人”。
此时斯托夫人在美国文坛的处境相当微妙。早在19世纪40年代,家学渊源的斯托夫人便以一部描绘清教场景的《五月花》(1843)蜚声文坛。受友人邀约,《汤姆叔叔的小屋》最初以副标题《不被当人看的人》(TheManThatWasaThing)在报刊连载,1852年以《汤姆叔叔的小屋,或卑贱者的生活》(UncleTom’sCabin;or,LifeAmongtheLowly)为题由约翰·P.朱厄特公司正式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她赢得世界性声誉,但在南方,此书却遭到恶意抨击和普遍抵制。如南方小说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Simms)创作反《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品《剑与拉线棒》(TheSwordandtheDis⁃taf,f1853),以此驳斥斯托夫人对南方的污蔑,并指斥斯托夫人是“虚伪成性的北方人的化身”。同时,小说也被许多人“误读”,如当时尚未成名的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一些具有施虐-受虐倾向的病人极有可能受到书中鞭打奴隶场景刻画的影响。
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宣称斯托夫人书中情节尽是“编造”:斯托夫人本人压根就没有到过南方,更没有亲眼见过南方种植园;而且,斯托夫人并非是在她辛辛那提府上(此处距离蓄奴州肯塔基不过一河之隔)而是在新英格兰家中——主要基于一本逃亡黑奴的笔记——完成这部著作。更为严重的是,关于1862年林肯总统称她是“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妇人”(Sothisisthelittleladywhostartedthisgreatwar)的传闻,原本出自斯托夫人儿子的回忆,但是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发现:斯托夫人在会见林肯数小时后写给丈夫的书信,并未提及总统的这句名言;史料中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佐证支持这一说法。为了回应公众质疑,斯托夫人于1853年发表《〈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AKeytoUncleTom’sCabin),引用报刊文章、私人信件乃至庭审记录等大量材料,证明小说所揭露的事实并非虚构,由此力驳“臆造”之说。尽管《题解》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在市场大获成功,但仍有明眼人洞察:其中若干资料乃是小说完成之后添加,因此作伪之嫌疑犹未洗脱。
1856年,斯托夫人应邀访问英国。此行除了洽谈代理版权和商务合作,她也借机与英国名流尤其是妇女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社会学家哈利特·马蒂诺,以及拜伦夫人。拜伦夫人(闺名安·米尔班克)出身名门,自幼天生聪慧,父母为其延请剑桥教授精心培养。她在数理方面造诣惊人,婚前被拜伦戏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二人所生之女埃达(Ada)日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1980年代美国军方制作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即以她命名)。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拜伦夫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立身严谨,与放荡不羁的诗人恰成对比——1812年,拜伦出版成名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一时间声名大噪——文学史上至今流传他志得意满的金句:“一夜梦醒,天下扬名。”
由于琴瑟不调,拜伦在婚后一段时间陷入抑郁,并被夫人断定为精神失常:他的神经似乎永远处于躁动之中,鸦片和酗酒是缓解焦躁的方法,但客观上却加剧了情绪的恶化。拜伦夫人在女儿出生未久便搬离纽斯特德(Newstead)庄园,并提议二人分居。分居事件在上流社会引发震动。拜伦一怒之下,决意远离英伦:一方面逃避舆论压力,一方面去追寻向往的自由。诗人将分居协议条款商洽之事委托友人、《论德国》作者斯塔尔夫人代劳。1819年,拜伦游历意大利期间,结识特雷莎·圭乔利伯爵夫人(芳龄十八),二人一见倾心。根据意大利习俗,伯爵夫人在征得父亲及丈夫同意后,正式成为拜伦情妇(诗人则甘作她的“贴身骑士”)。据说直至拜伦逝世之后,伯爵在社交圈的开场白通常都是:“这是我太太。她曾是拜伦的情妇。”
根据斯托夫人的记载,拜伦夫人在谈话中证实早在夫妇二人结婚之前,拜伦与奥古丝塔·利便有私情,并育有一女,名为梅朵拉(Me⁃dora)。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拜伦的婚事乃是利一力促成,其目的在于掩盖丑闻。而拜伦夫人之所以下定决心与诗人分居,正是由于她无意中窥破了这一秘密。这一秘密在她心底埋藏若干年,因此她也希望斯托夫人能信守诺言,绝不外泄。
斯托夫人坦承对于公开发表与拜伦夫人的私人谈话内容深表遗憾,但同时又指出,作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知识女性,她有义务为友人打抱不平,何况这也是为所有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伸张正义。遗憾的是,斯托夫人正义满满的道德文章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认为斯托夫人文中所述多系道听途说,不足为信——如竭力促成拜伦婚事的并非奥古丝塔·利,而是社交名媛墨尔本勋爵夫人,此乃人所共知的事实。艾略特指责斯托夫人文章“侵犯拜伦家族隐私”,并公开宣布与之划清界限。与此同时,英国媒体对斯托夫人更是大肆讥讽,因为她不仅“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而且恶诋死者(“拜伦名声的暗杀者”)——居心何其险恶。
在美国,约一万五千名订户愤然取消订阅刊载过斯托夫人这篇文章的《大西洋月刊》以示抗议,可见其已触犯众怒。为迎合观众需求,纽约坦马尼(Tammany)剧场在每场原定演出之前加演一段文坛“公案”,而每一次斯托夫人扮演者粉墨登场,台下必定嘘声四起。更有好事者作《拜伦的答辩》(“LordByron’sDefence”),用《唐璜》韵步作答——讥讽斯托夫人穿凿附会。最滑稽的是报刊登载的“高仿文”,题为《莎士比亚夫人的生活真相》(“ThetruestoryofMrs.Shakespeare’slife”),借莎翁夫人之口,指控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一系列谋杀案的“真凶”——包括残忍杀害其竞争对手、同时代著名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娄。文章作者模仿斯托夫人从拜伦诗中找证据的手法,从《麦克白》《理查三世》等历史剧中“发现”若干与谋杀相关的描述。该文考据论证煞有介事,讽刺也入木三分,一时广为流传。
当然,所有反对派中杀伤力最强的还是“阴谋论”者:他们不单单指控斯托夫人发覆隐私、哗众取宠,更指斥此举“纯粹出于商业动机”——《拜伦夫人的生活真相》一文单篇稿酬高达250英镑,令人咋舌——日后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宣称斯托夫人“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美国文学作品选集》评价她“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在与出版商讨价还价方面,远比库珀、梅尔维尔和欧文更为成功”,足见所言不虚。阴谋论者的论据极为简单粗暴:因为同时代女作家范尼·费恩新近推出纪实小说(romanàclef)《露丝·霍尔》(RuthHall)——靠自曝家丑(攻击其兄长、纽约著名报人N.P.威利斯)赢得市场,斯托夫人一定也想凭借“猎奇”来吸引眼球。
为反击各方对她的恶言相诋,经过大半年时间搜罗查证,斯托夫人于次年推出《为拜伦夫人辩护》一书,厚达480余页——其卷首语宣称:“既然默认等同于犯罪,就让我代替拜伦夫人向世人揭示真相”(...since silenceisthe crime,IthoughtIwould tell the worldthatLadyByronhadspoken)。该书表面是为拜伦夫人辩护,实则自辩。书中广泛引用(直引加间引)书信、日记、访谈乃至法律文书,内容不可谓不丰瞻,但总体“松散、不连贯”,既缺乏逻辑条理,更缺乏文采。整部作品无非是资料的罗列和堆砌,平铺直叙,有违亨利·詹姆斯所谓“作品的生命在于戏剧性张力”这一文学原理,难以卒读。当然书中也采用了若干修辞手法,试图诉诸情感,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二十年后以纽约著名新闻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Riis)《另一半怎样生活》(HowtheOtherHalfLives,1890)为代表的美国新闻纪实主义笔法一度相当走红,然而在斯托夫人生活的年代,这一手法尚未大行于世。比如文中反复使用“你,我的姐妹,怎么能忍受我们的女儿受此侮辱?”之类呼语及反诘句,可惜读者并不领情,相反益发坚信作者乃是“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因为她辜负了拜伦夫人临终所托。
照美国人向来的看法,私房话或私人信函之类“隐私”,本不该用于公开发表出版,更何况其中还掺杂若干“掠夺式”的强制阐释:断章取义以及大量推测臆断严重削弱了文本的可信度。甚至书中为增强客观性而使用的法律语言也遭到诟病:斯托夫人声称“我承认并证实”,亲朋好友成为“证人”,私下言谈成为“证词”(其实属于不告而取或“非法取证”)——显然有违朋友之道。尽管斯托夫人宣称她只是“文学代理人”(因为拜伦夫人未能留下回忆录),她本人亦自称中立者(本书的客观公正,“只有上帝知道”),事实上她也的确希望能够两全其美:通过冷静的叙述和严密的推论晓之以理,再加以文学性的描述动之以情,但孰料读者群中颇多浪漫派诗歌的狂热粉丝(aficionado),义愤填膺欲为“偶像”拜伦打抱不平,而斯托夫人之“辩护”,乃陷于越描越黑的境地。与此同时,评论界也推波助澜,将《生活真相》一文讥讽为小说家“最后的罗曼司”,而将《辩护》称为女作家平生最后一出“道德大戏”——到剧终落幕之时,斯托夫人的文学声望已“难以修复”。
当然,为斯托夫人辩护者也不乏其人。如女权运动先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赞同《辩护》,并且坚信当下婚姻制度对女性不公(婚姻无异于“合法的卖淫”),必须进行改革。与斯托夫人一道强烈主张废奴的著名女作家莉迪亚·蔡尔德也相信拜伦夫人遭受冤屈,必须为之伸张正义。此外,斯托夫人家族的亲朋故旧亦纷纷撰文,抗议报刊媒体对一位蜚声海外的美国作家进行“围剿”,可惜这样零星的抗议淹没在一片讨伐声中,并未能平息事态。
与美国评论界的道德评判相比,英国评论界更多从经济利益角度评判:先是《每日电讯报》含糊其辞地暗示,斯托夫人之辩护乃是出于“寻利”(profit-seeking)之目的。伦敦《回声报》(Echo)旋即爆料她的稿酬收入,进一步坐实其写作乃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久负盛名的《泰晤士报》指责她炫耀与上流社会的密切关系(友谊),目的无非是自抬身价——真正的名门淑女根本不愿与闻此事(乱伦),更不会当众讨论。这场舆论围剿战役的高潮是1869年9月英国著名杂志《谐趣》(Fun)刊载的一幅漫画:画中面目狰狞的老妇人攀爬拜伦雕像,在洁白的大理石底座及像身留下肮脏脚印,并试图用手中雨伞勾搭诗人肩膀(隐喻欲与诗人试比高)——漫画下方有一行醒目大字:“喂,老东西,你想出名,最好换个地方,不要在此留下肮脏的爪印!”漫画的标题是《住手!》(Stoweit!)——其双关意味不言而喻(斯托夫人的姓氏Stowe与英文单词stow发音相同,stow意为“储存、封闭或制止”)。
或许因为心绪不宁的缘故,再加上时间仓促,《辩护》被讥为“廉价小说”,因为文中瑕疵所在皆是,大失名家水准:比如斯托夫人就拜伦夫妇分居事件绘制的时间轴(timeline)很有说服力,可惜拜伦与夫人共同生活仅有一年,而书中误作两年,令人顿生疑窦;再如拜伦夫人闺名米尔班克(Milbanke),书中竟误作密尔班科(Millbank)——诸如此类低级错误,使得可信度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书中截取拜伦夫人与奥古丝塔·利的书信以证明二人“交恶”,然而查证全文不难发现其实二人关系一直保持良好——拜伦夫人即便在与拜伦分居后,对奥古丝塔·利依然言辞恳切、情谊殷殷——与斯托夫人“代言”的乱伦指控迥不相侔。更有拜伦传记作者声称,乱伦之说乃诗人本人生前故意编造,目的在于自毁形象——他一向志在表现得“比别人想象的更坏”(make people think himworseeventhanhewas)——以此显示独立不羁,同时也以此报复社会(照鹤见祐辅《拜伦传》的说法,拜伦是以“伪恶”的姿态对抗人类社会的“伪善”)。此说在朋友圈不过是一段笑料(好友雪莱曾半开玩笑地说,“乱伦,于道德不合,但极富诗意,是强烈情感的极端表达”),拜伦夫人也未必信以为真——当日对斯托夫人再三叮嘱此说不得外传,正说明名门大家出身的拜伦夫人立身之谨严。
据知情者透露,拜伦分居事件真正的缘由,乃是夫人在夫妇骂战中嘲讽诗人跛足是“上天的惩罚”。跛足为拜伦终身憾事,在朋辈亲友中属于禁忌讳言,夫人有意无意逢彼之怒,遂造成覆水难收的局面。事实上,夫人日后对此亦不无悔意,奈何双方皆为心高气傲之人,故再无回旋余地。夫人自后一直缄默不言,或正以此中有“难言之隐”。这也是英国评论界对斯托夫人代言极为“反感”的主要原因:拜伦夫人文采出众,曾引朗费罗译《神曲·炼狱篇》斥责拜伦薄情寡义,亦娴熟希腊罗马经典,倘欲著笔,根本“无须代言”。更何况,对拜伦夫人境况怀抱恻隐之心的英国文化名人非止一二,如苏格兰名诗人托马斯·坎贝尔,以及著名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拜伦夫人果欲发起一场笔墨官司,或法庭诉讼,何必要待斯托夫人而后动?
斯托夫人本意为拜伦夫人辩护,结果却演变为对诗人拜伦的人身攻击,甚为不智。尤其是书中若干曲解和影射,穿凿附会,明显有违文学伦理。如书中引《听闻拜伦夫人生病而作》(“LinesonhearingLadyByronisill”)一诗——诗中拜伦将妻子比作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王》中王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由此斯托夫人指责拜伦故意丑化夫人(神话中王后与奸夫合谋绞杀阿伽门农王)。然而熟读全诗后不难看出,诗作的主旨是海外游子对妻女的深切思念——尤其是女儿埃达——拜伦称呼她为“迈锡尼的公主厄勒克特拉”。这本是寻常的文学性修辞,也是诗家惯用伎俩,身为小说家的斯托夫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她却一再指控“他(拜伦)是语言的暴君,翻云覆雨,掌控一切,犹如拿破仑。”“玩弄(bewitched)摩尔、默里等人于股掌之中……先辱骂沃尔特·司各特,后又讨好他。”——文中所指托马斯·摩尔为拜伦密友,也是拜伦传记作者,极负文名;约翰·默里是伦敦著名出版商;司各特为历史小说名家,在英美两国享有盛誉。此外,斯托夫人书中对笛福、班扬等英国文化名人也缺乏应有尊重——语气咄咄逼人,打击面太广,严重伤害了英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辩护》在英国遭受冷遇,可谓咎由自取。
此外,斯托夫人对奥古丝塔·利的指控亦不得人心。众所周知,拜伦幼年丧父,与母亲关系紧张,家中唯有奥古丝塔·利与之友善。拜伦每遇艰难苦恨之时,她总是义无反顾地伸出救援之手,给予信任和温暖。这种亲人加朋友的情谊对愤世嫉俗的拜伦而言可谓弥足珍贵。1816年拜伦被迫永远离开英国之前,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便是献给奥古丝塔·利。尽管拜伦与奥古丝塔·利的情谊使得诗人生前付出惨重代价,死后亦倍受诽谤攻击,但拜伦一生从无悔意。直到1819年,他在给奥古丝塔·利的信中仍深情地写道:“我从未停止过,也决不会停止(哪怕是片刻)那种无瑕的、无限的深情。这种深情过去将我同你连在一起,现在也将我同你连在一起,使我完全不能再真正地去爱其他任何人,因为在你之后,她们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拜伦去世后,他的骨灰运抵英国,安葬于纽斯特德附近的小教堂墓地,铭刻在墓碑上的那篇传诸后世的著名碑文即为奥古丝塔·利拟就——“即使我的肉体即将消亡,我的意志永远都不会被时光和苦难磨灭”。事实上,即便在拜伦亲友圈内,奥古丝塔·利与拜伦夫人(及其女)的情谊也是尽人皆知;斯托夫人的爆料虽然轰动一时,但终究难以成立,犹如一出闹剧。
不仅于此,由于证据匮乏,斯托夫人贬毁拜伦情妇特雷莎·圭乔利伯爵夫人亦未能达到目的。照拜伦书信的描述,伯爵夫人“诗趣横溢,像柔和的春风”,与数学家气质的拜伦夫人恰成鲜明对比。在与伯爵夫人同居的美好日子里,拜伦诗兴勃发,写出著名的政治抒情诗《哀希腊》(《唐璜》第三章)以及《但丁的预言》,并创作反抗暴君专制的诗剧《该隐》和《天与地》。事实上,从诗剧《该隐》和历史剧《萨达纳巴勒斯》中两位美丽动人的女性(阿达和米拉)形象上,人们不难辨认出诗人心中恋人的倩影。当然,伯爵夫人给予拜伦的影响远不仅于此。作为一名热情的革命者,她不但积极引导拜伦创作唤起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诗歌作品,同时还引导诗人投身于这一正义而伟大的事业。伯爵夫人在晚年(时年66岁)出版的回忆录,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读者中赢得广泛同情(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拜伦”一节也为伯爵夫人鸣不平——认为法国名诗人缪塞对她的指责有欠“公允”)。由此看来,斯托夫人对她的攻讦显然“极不明智”。
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在《文学是什么?》一书中所说,遭遇生活打击的斯托夫人(长子内战中受伤,后失踪;幼子上大学期间溺水而亡;女儿患有精神性疾病,后病故)晚年极有可能“迷失神智”:她在本书中对拜伦一方面崇拜得五体投地,一方面又义正辞严予以贬斥,前后乖违,难以自洽——《为拜伦夫人辩护》市场仅售8000册,抵不上鼎盛时期的一个零头,可见“文学伤感主义的式微”(随后迅速被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与之同步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销量此后也陷于停滞——很明显,1865年后的美国不再需要这一类激发南北双方矛盾冲突的小说——“它必须小心翼翼地遮盖或遗忘双方各自的伤痕和相互的仇恨,因此它更愿倾听沃尔特·惠特曼的歌声”。
《文学是什么?》一书副标题是“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在书中莱斯利·费德勒通过对斯托夫人以及马克·吐温小说的解读,揭示“废奴小说”“伤感小说”或“历险记”等类型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市场的产物,文本自身存在瑕疵,与霍桑、梭罗等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相比差距明显——它们仅仅是大众通俗文学的成功之作,很难真正进入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的行列。正如萨克文·伯科维奇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言,爱伦·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作品销售远不及斯托夫人,然而,“销售数字本身无法造就(文学)传统。”20世纪美国著名黑人评论家詹姆斯·鲍德温将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排除在“美国文学经典”之外——尽管两部作品主题皆与废奴有关——显然基于同样的理由。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正如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言,这一现象乃是源于文学风尚的变化:19世纪流行的浪漫派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实用的批评”,它具体表现在注重作家(诗人)生平,强调道德教谕。而随后兴起的新批评派则注重文学文本,讲求艺术性,主张文本与道德无涉——用伦敦《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主编约翰·莫利(JohnMorley)的话说,“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就是它自身的保证”。这位主编同时倡导从人性(humanity)的角度出发,对包括弥尔顿、彭斯以及拜伦这样的文学天才应当给予“宽容”——毕竟,传诸后世的是他们的作品,而非其生平(或私德)。这一种时代风尚的变迁可视为千百年来文学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的一个明证。
作为19世纪英美文坛瞩目的一桩文学公案,斯托夫人一手炮制的“拜伦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便身为名作家,一旦昧于大势,固执己见,则文学声望必定大受影响,以致呈现“断崖式”下降,一如斯托夫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阶段性成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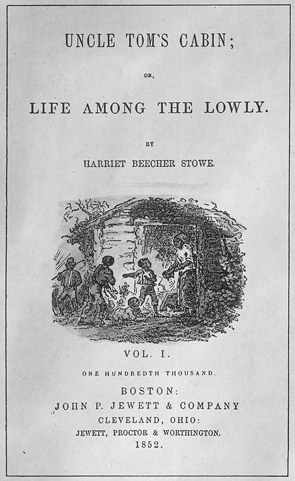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