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689-740)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截取其前四句,题“洞庭湖作”,不署作者。宋蜀本《孟浩然集》题“临洞庭”。《文苑英华》卷二五○、卷三二○孟浩然名下并见收录,题“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全唐诗》卷一六○孟浩然下题“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此诗借山水以达志,所表达的虽是干谒情怀、功名之愿,但化世俗之情于雄浑壮伟的山水之中,却不失其艺术价值,故为历代读者所推赏。其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句,气概横绝,意境雄阔,历来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并称为咏洞庭之千古名句。据元初学者方回记载,此诗与杜甫《登岳阳楼》被写在岳阳楼毬门左右壁,“后人不复敢题”(《瀛奎律髓》卷一)。在当代学者王兆鹏《唐诗排行榜》所选的一百首中,它高居第七名。
其诗题中的“张丞相”指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指张说,一说指张九龄。由于二人都曾官居相位,遇贬外调,又都先后任职荆州刺史。更重要的是,二张对浩然都有知遇之恩,都有往还唱和之作。孟先后写给二张的八首诗中,题目都有“张丞相”或“张相公”的字样。于是,这个“张丞相”到底所指何人,长期纷争,悬而来决,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千古疑案。
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数十种出自名家之手的唐诗、孟诗选注本,以及相关论著,不难发现,主张孟诗题中的“张丞相”指张九龄的,占了绝大多数。举其要者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85年版),施蜇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陈新璋《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启兴主编《王维孟浩然诗歌名篇欣赏》(巴蜀书社1999年版),霍松林《唐诗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成纲《你应该知道的中国古典诗词》(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陈耀南《唐诗新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罗时进《山水诗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陶金雁《唐诗三百首详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邓荫柯《中华诗词名篇解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韩兆琦《唐诗精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徐中玉《唐宋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李定广《中国诗词名篇名句赏析》(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余党绪《古典诗歌的生命情怀》(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尽管作者(或选注者)不同,出版日期有异,但对孟浩然诗题中“张丞相”所指何人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是张九龄。此外,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对孟诗的写作、投赠时间,大都语焉不详。其中,只有少数人明确提及。比如,刘逸生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金性尧、陶金雁也持类似观点。刘学锴说:“张丞相指张九龄,开元二十一(733)年至二十四年为相。诗约作于二十四年诗人游湘、赣时。”施蜇存也推断孟诗的写作日期为“开元二十四年”。
相对来说,认为孟浩然诗题中的“张丞相”是指张说的例证,要少得多。不过其所申述的理据却似乎更为令人信服。比如,周啸天《隋唐五代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这是一首干谒之作。所干之人,一说为张九龄,一说为张说。于关系而言,浩然于九龄较深,但九龄并未作过岳州一带地方官;张说开元中曾罢相,四年(716)坐事贬为岳州刺史,所以就事迹言,则投献张说的可能性为大。”陈晋《唐风宋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说:“张丞相,指当时担任岳州刺史的前宰相张说。”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载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二卷)一文考证,孟浩然此诗是投赠张说的,时在开元三至六年(715-718)。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在《临洞庭》一诗的注释中提到:“此诗《英华》载题中有‘张丞相’字样,据诗后四句,有望人举荐意,张丞相应为张说,开元四年至五年任岳州刺史,考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岳州下,此诗亦当作于此时。”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说:“张丞相,当为张说。”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年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云:
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 二十八岁
秋八月,孟浩然由襄阳南下岳州。
作《临洞庭》一诗投刺张说,希求汲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几种比较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在相关章节都论及孟浩然这首诗,但对诗题中的“张丞相”所指何人,意见也不一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认为,孟诗中的“张丞相”是指张九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评介此诗时,选取《望洞庭》的诗题,只说“这首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洞庭湖的自然伟力在诗里得到含蓄而有力的表现”,而对“张丞相”是谁则只字不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孟诗中的“张丞相”指谁,也是略而不谈。而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则独抒己见,明确指出“这首诗是赠张说的”,它“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达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特别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数十年来一直在学界并存流行,令不少读者既深感困惑,又无所适从。到底孰是孰非?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同一问题,答案可能有多种,但是最合理、最可信、最接近于问题实质的答案,只能有一种。那么,《望洞庭湖上张丞相》的“张丞相”是谁?正确的答案也只能有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我们只要弄清孟浩然最初与二张交往的时间、地点,其诗中的张丞相究竟指谁的疑案,也就不难破解了。
张说(667-731),据两《唐书》本传,景云二年(711)为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三年(715)四月除岳州刺史,开元五年二月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史传称张说“喜延纳后进,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名士以佐王化”;又雅擅词翰,时称“大手笔”。士子以诗文送呈达官贵人以求引荐,称为“行卷”,是唐世流行的风气。孟浩然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颇以诗名,但并不甘于隐遁,开元四年(716),孟二十八岁。这年秋天,当他获知张说谪守岳州,并“每与才士登楼赋诗”的消息之后(据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评传》考证,向孟提供这一信息的,当是他的同乡好友,时任荆府参军的张勰),即毅然告别父母,离开家乡,经由汉水至江夏,然后溯江而上,直奔岳州而去。这是孟浩然首次离开襄阳,首次接触襄阳以外的世界。当他到了岳阳后,即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遥望着烟水一天、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写下了一首平仄协调、对仗工整的五言律诗《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投谒京都来的大官和比自己大22岁的文学前辈张说。洞庭湖乃岳州胜概,该诗以洞庭之雄大气象发兴(隐比张丞相胸襟博大),然后过渡到欲济无舟,希望有以援引。措词极委婉得体,所谓“不露干乞之痕”(纪昀语),切合一个有修养的文学青年初见达官的口吻。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张说对此诗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致使孟浩然“有声于江楚间”,并“信”为“诗伯矣”(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引陶翰《送孟大入蜀序》)。距孟浩然献诗7年之后的开元十一年(723)“三月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据《旧唐书·玄宗纪》)。按唐朝惯例,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新唐书·百官志》),张说是时大权在握,完全具备了“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的条件,于是向明皇荐举了孟浩然。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孟浩然》有载:
明皇以张说之荐召见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因是故弃。
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唐诗
纪事》的记述是可信的。据此可知,“气蒸云梦泽”一联诗在浩然应召入京前已传闻于世,流播人口,连明皇都能记诵。这就更证明他的《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是早期作品,而不是赴举落第后隐归故里的晚年所作,“张丞相”自然是张说而决非张九龄。
孟浩然何时认识张九龄?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此前,他被襄州刺史宋鼎辟为襄府从事。宋鼎与张九龄交谊深厚。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由中书令(丞相)贬为荆州长史。宋鼎自襄州转牧汉阳。五月,经宋鼎推荐,张九龄辟孟浩然为其荆府从事。对这段史实,王辉斌《孟浩然新论·孟浩然评传》一书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
张九龄(公元678-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两《唐书》有传,曾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为李林甫所忌,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孟浩然与张九龄之交往,主要是在张九龄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期间。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二人相识于开元十七年前后之长安,也即是在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新唐书·孟浩然传》)之际。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极为错误的。这是因为,张九龄开元十五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乃在洪州刺史任上。《四部丛刊》本《曲江集·附录·诰命》有《授洪州刺史制》一文,其结尾处署明时间为“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又《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一文之末,乃署为“开元十八年七月三日”,合勘之,知张九龄开元十五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不在长安,则其不能与孟浩然于是时在长安结“忘形之交”者,也就甚为清楚。又据《曲江集·附录·诰命》之《加朝请大夫敕》《加守中书舍人敕》二文,知在孟浩然奉诏入京的开元十一年冬至十二年七月期间,张九龄虽然任职于长安,但其所官之中书舍人,乃隶属于门下省,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载“诸英华赋诗作会”于“秘省”(即秘书省)者,乃迥不相及。此则表明,当时就职于门下省的张九龄,是不可能到秘书省去参加“赋诗作会”的。因之,二人在此期间之不能结为“忘年之交”,也是可以肯定的,而《孟浩然集》与《曲江集》均无只字及此者,又可为之佐证。所以,孟浩然在为张九龄“辟置”于荆府之前,是不曾与张九龄有过交往关系的。
王辉斌先生是孟浩然研究资深专家,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孟浩然研究,历时三十余年。主编过《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第一辑、第二辑等书;出版过《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新论》等专著。他的上述考证,自觉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原则,抽丝剥茧,烛幽抉微,归综诸说,匡订讹谬,其所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既然孟浩然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才在荆州认识张九龄,那么他向张九龄投诗乞仕则不可能早于这个时段。况且,如果认定《望洞庭湖上张丞相》的“张丞相”是指张九龄(像当代不少研究者所倾向的那样),揆之常理,至少有两点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此诗托兴观湖而寓求荐之意,诗的题目和内容都紧扣洞庭湖。而令人费解的是,诗人在荆州上行卷于张丞相九龄,却搬出毫不相干的“洞庭湖”来作陪衬,这也未免太过做作了吧?
其次,张九龄任荆州长史在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当时孟之年岁已在四十九至五十一间(孟卒于开元二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垂暮之年,再也写不出像《望洞庭湖上张丞相》那样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的诗作了。浩然三十五岁应召入京,被明皇罢黜;四十岁应举,又失手落第。据《旧唐书·孟浩然传》:“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落第后心灰意冷,其《留别王维》诗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怨悱之意,形诸篇什。王维亦有《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安慰之余,劝他回归故乡,不必再在京师为仕进而徒劳奔走。了解孟的这段经历,就不会认同向“张丞相”投谒求荐之作,是他受黜、落第后的晚年所写了。很难想象,一个在人生道路经受一次次重大打击,对仕途早已极为失望的垂暮老人,还能写出那样充满强烈求仕、用世愿望的干谒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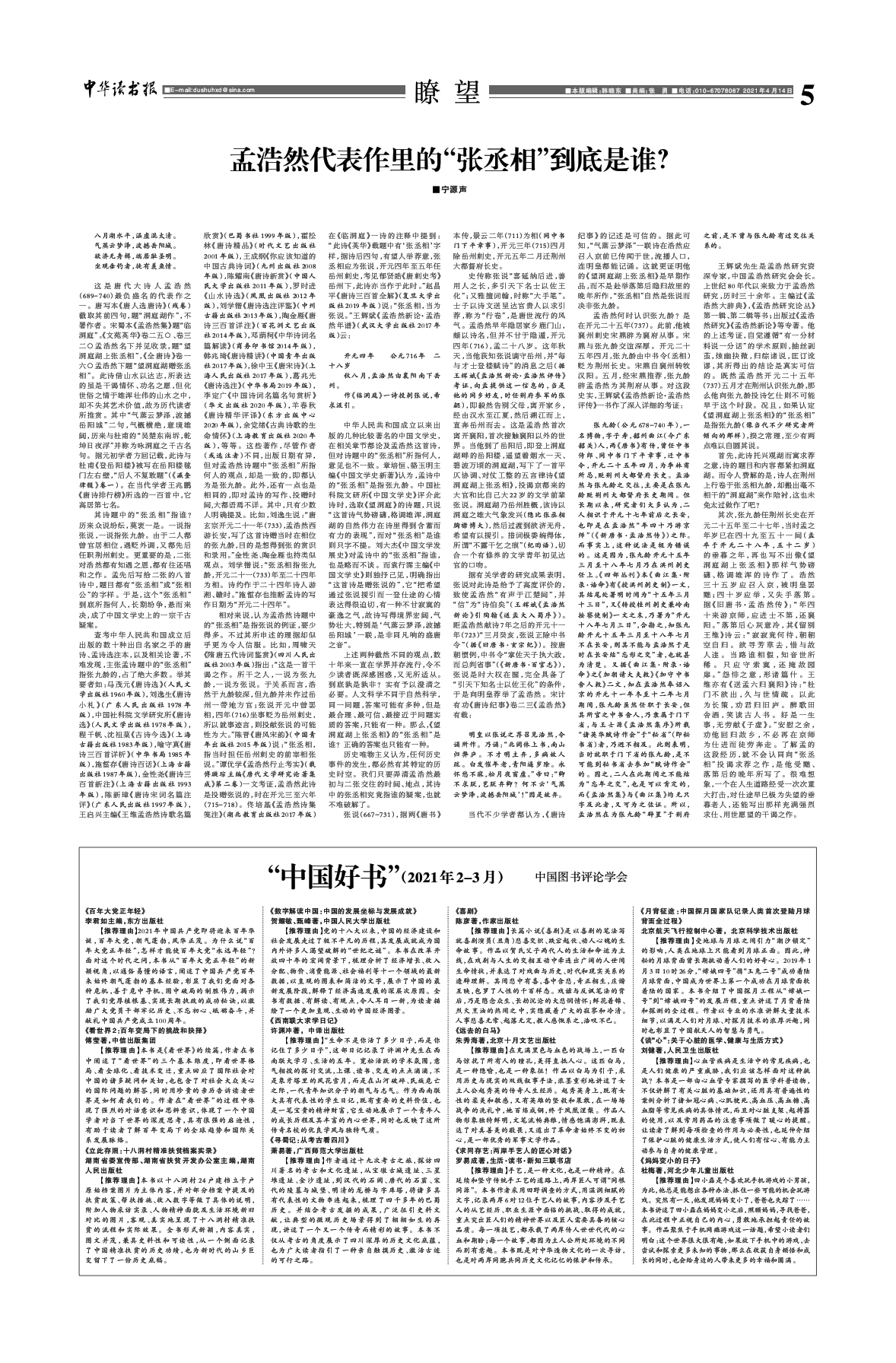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