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大致上可分成三个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时至今日,我们真正能够继承、发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古代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判断、人生理念等。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古代典籍。继承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少数专业研究者的专利,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义务。”
古籍,是承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记载国家文明的标志,更是传播文明的重要方式。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夺目的文明史,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比丰富珍贵的文明文化遗存,集中体现在了历代古籍中。中华古籍及其所载文化结晶的传播,对人类的进步也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可以说,卷帙浩繁、门类广博的文献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更是因为中华精神所聚。这种精神,正是由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观念文化铸就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如果脱离阅读古籍,又如何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拥有丰厚的古书遗存。然而,能历经千年而流传至今的,大多都是古籍中的经典,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性。读古籍,更要读其中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古籍中的深远智慧、价值观念,博大精深,仰之弥高;经典中字词韵味、音律格调、对仗形式和逻辑结构的美感,读来则满口噙香,妙不可言。
当下,让经典“活”起来,让古籍走进大众的时机已到。这个时机,就是新时代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贡献。
学术与普及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高、精、尖的学术类古籍整理图书是后者之本,而接地气、有生气的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是前者之体。自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了夺目的成就。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了3.6万种古籍整理图书。近些年来,古籍图书出版更是量质齐升,每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有近1800种,其中学术类古籍图书800种左右,普及类古籍图书1000种左右。
显然,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在于阐释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之所以要对重要的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以及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最终目的是将经典名著引入千家万户,走进万千大众的日常生活。近年来,在对古籍普及出版工作的扶持和引导方面,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首先,古籍小组注重加强在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工作中对古籍普及图书进行扶持,2016年,对优秀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进行了一次专项资助。遴选经典优质的普及书目,是大众阅读的前提和基础。2013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评审,向全国推荐91种优秀古籍整理出版图书;2015年和2018年,古籍办先后两次举办向全国推荐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的活动,引发了强烈的业界反应和社会反响。
今年3月3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在这首批向全国读者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中,既有具较强典范性、传承性的古代文化典籍,其中包括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核心理念的原典,也涵盖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名家名作。
“这次开展的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遴选出最经典最重要的古籍及其最优最善的普及整理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荐。这不仅是一次对我国古籍普及出版的整体检阅,更是一次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良好契机。”古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可以发现,每部推荐经典,都提供了大约三个层面的版本,一是带有提高性质的注释本,二是全文简明注释本或注释加现代汉语翻译本,三是选注或选译本。这就充分考虑到研究者、中等水平读者、初等水平读者三个读者层面,为经典走向广大的读者人群创造了条件。”推荐书目活动的评委、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介绍。
尤其是,此次的经典古籍书目推荐活动志在长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发布推荐书目的公告中明确指出,“形成分批分次推荐的长效工作机制,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将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推向深入”。
书目为要
朱自清先生曾在《经典常谈》的序文中开宗明义地谈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目的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可以看到,世界上各民族都有核心经典,对核心经典的阅读和感知,是国民的一种“义务”(朱自清语)。
此次公布的推荐书目,是从传世典籍中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工作,在中国历代几乎都做,那就是推荐书目。儒家的“六经”《周易》《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就是孔子从当时许多书当中选拔出来,推荐给自己学生的。唐朝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五部经书变成了《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也是一种选拔工作。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又是具有特色的选拔推荐工作。清代光绪年间张之洞做四川学政,为初学者指导读书的门径,开出了经史子集各方面的重要书目,成为《书目答问》,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认为自己做学问也是以《书目答问》为指导的。所以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选拔,是历代都重视的。
“今天推荐经典书目,既不能抛开历史上的共识,也不能照搬历史上的选拔结果,应当体现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认识和研究水平。”杜泽逊介绍,此次入选的图书包括各个方面,尤其是古典小说,体现了这几十年研究的新理念。至于推荐的版本,大都是这几十年注释、校勘、标点、翻译、选译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体现了新时代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达到的新水平、新高度。所以说,推荐书目,既是历代成果的继承,又体现了新时代对历史的超越。
确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代典籍浩如烟海,哪些书是传统文化“最要之书”,哪些版本是“最善之本”,是每一位学习传统文化的读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最重要的典籍,对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国历代都有学者开列推荐书目的传统,但如何在新时代为广大人民群众推荐代表国家水平、符合时代要求、满足群众需要的书目,是古籍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也是时代赋予古籍工作者的新任务。显然,此次古籍办开展的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既遴选经典古籍,也遴选整理版本,将为下一步做好新中国古籍整理“书目答问”摸索经验,奠定基础。
通过此次推荐工作,推出一批具有典范价值的优秀古籍普及图书,在学术界、出版业界及广大读者中树立起古籍普及精品图书的样板和标杆,也正是此次推荐活动的题中之义。其功在于,从读者层面看,可引导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优秀的古籍整理版本,读好书,用好书;从出版层面看,可树立正确的学风、行风,抵制粗制滥造的歪风邪气,扭转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的不良风气。
客观来看,由于古籍整理出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完备评价体系的建立难以一蹴而就,特别是普及古籍图书的评价机制较为欠缺。显然,一次又一次推荐工作的实践,能够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集整理、出版、规划、资助、人才培养等多环节为一体。其体系化的特征,需要上下游互动,进一步加强读者、学者和出版者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而此次的经典古籍版本推荐工作,正是旨在促进各环节的沟通,形成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宣传推广相衔接的长效机制,为古籍整理出版阅读事业发展,提供不竭的推动力。
“最要之书”“最善之本”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爱书、敬书、读书的民族。尽管因为各种天灾人祸,历代典籍遗留至今的十不存一,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仍有约20万种。40种经典古籍的选择推荐,可说是万中挑其一二。为选出传统文化“最要之书”和“最善之本”,此次的经典古籍及其优秀整理版本的评选和推荐耗时日久,主办方和评委会成员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据介绍,这次推荐工作是首批推荐。为确保推荐质量,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本次评选采取了梳理书目、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个阶段为梳理书目。形成的书目既反映了学术界的意见,也体现了出版界的共识;既吸收了专家从学术层次上的推荐书目,也通过销售数量、图书排行榜反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取向;让书目的形成拥有了坚实的质量和阅读基础。
第二个阶段为专家评审。评审专家对评审的原则标准、书目的遴选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评议和讨论。经评审专家审读样书并审核后,形成了专家推荐书目。
第三个阶段是复核质检。为确保推荐质量,部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知名专家对推荐书目进行复核,请他们从专业角度再把关,各自独立提出审核意见。还根据专家意见,对推荐图书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最终形成了拟推荐的40种古籍、179个古籍整理版本。
梳理此次推荐的古籍书目,可以发现,其标准一是强调传承性,推荐的古籍能够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核心理念,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价值;二是强调典范性,重点推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能够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批推荐的40种古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行为规范和美学追求,注重满足广大读者对古籍经典的关注和需求,特别是列入了一些古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首批推荐的这些古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不是传统古籍的概念,而是采用“李白集”“杜甫集”这样类的概念,主要是考虑方便大众读者的选择和阅读。
首批推荐40种后,古籍办还将继续推荐经典古籍,为读者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古籍阅读基本书目。
而从179种优质整理版本的推荐目录来看,其标准主要是突出权威性和普及性。一是所据底本要精善,所据底本尤以渊源自古,流传有序,校勘审慎,文字精良者为先。二是编著、整理者要权威,遵循学术规范,坚决杜绝东拼西凑、胡抄乱写。三是出版单位要专业,遵循出版规范,坚决杜绝跟风炒作、盲目出版。四是内容质量要上乘,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标杆和范本。五是读者层次要兼顾,考虑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以普及类读物为主,适当兼顾偏普及的学术类整理著作。
专家在此次评审时,注重把握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关系,以古籍普及读物为主,适当兼顾偏普及的学术类整理图书,推荐图书既要能科学、正确地反映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做到内容通俗易懂,形式新颖灵活,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对于内容过于专业、读者面太窄的图书一般不予推荐。同时,专家还注重把握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推荐的整理版本要契合新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要明确每个推荐整理版本的读者群体、适用范围以及意义和价值,使推荐活动有的放矢,取得更好的效果。尤其是,专家为每种古籍及其整理版本都撰写了推荐语,方便读者根据需要选书。
仅以推荐书目中的《尚书》为例。专家认为,《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是儒家“五经”之一。《尚书》是研究虞、夏、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一些专门学科或学说的源头性典籍。例如,历史地理学尊奉《禹贡》,五行学说尊奉《洪范》。《尚书》还是我国“政治学”的要典,书中的政治学说十分丰富,可以称之为“帝王之学”“君臣之学”。《尧典》提出的“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政治方略,在历史上长期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观念,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特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专家推荐的五种整理版本中,包括《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中华书局)、《尚书今注今译》(屈万里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尚书(国学基本丛书)》(周秉钧注译,岳麓书社)等。
《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早在上世纪20年代,顾先生便已提出了整理《尚书十书》的宏大规划。刘先生则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与顾先生合作,专心投入《尚书》的研读与整理,积三十八年之功,终克有成,他们关于《尚书》的几乎所有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这本《尚书校释译论》中。“《尚书校释译论》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它既是《尚书》原文的校勘与注释,又是《尚书》学的专题考述,其体例设计完善、缜密,每一篇都设有题解、校释、今译、讨论几部分,各司其职,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并且互相起到补充的作用。”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如是评价。
《尚书今注今译》则系我国现代经史研究大家屈万里先生所著,是其“尚书学”系列著作之一。屈先生深于小学、经学和甲骨卜辞,结合出土文献诠释《周易》《尚书》《诗经》,成绩斐然。其先行出版的《尚书释义》经反复修订成《尚书集释》,已成为经典读本。但对想了解《尚书》大意的广大读者来说,“往往不克但凭注语既能详悉经文之意义”,因复著此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万里在荐语中写道:“注语力求简洁,避免繁琐引证;译文力求保持经文原意,尽量做到信达雅。全书注译精当,使读者通读一过,即可略知《尚书》大意,是欲窥经典门径者不可不读之书。”
“《尚书》以典、诰、誓、命等四种体式记载了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反映了上古华夏文化的各个侧面,是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文献。但因其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后世常称为难读,现代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更是望而生畏。周秉钧先生是现代训诂学大家,这本《尚书(国学基本丛书)》于今古文各篇皆有收录,针对原文有详尽精当的注释及文意准确的白话译文,浅显易懂,有助于一般读者更好地认识并理解这部古代国学经典。”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钱宗武如是语。
大众也应读经典
为什么要读古书,读经典?如何理解当下阅读中华经典古籍的价值和意义?很多时候,坊间在谈及古籍阅读的时候,往往认为这是专业研究者的阅读研究行为。那么,大众读者如何也能读通、读懂古籍,甚至活用古籍?让经典古籍走进大众阅读或大众日常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放到世界文明的范围来看,中华文明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历史悠久,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二是四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超过20万种存世典籍,没有一个民族可比。流传至今的中国典籍,既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贡献。
而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是过去五千年文明历史最贴近现场的遗存、最完备准确的载体,伴随着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伴随着文明的每一次升华,为中华民族战胜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因此,“我们说经典不只是在经典产生的时代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经典在传承传播的漫长过程中,继续不断汲取、不断光大,指引未来的方向。经典是过去的,更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中华书局党委书记徐俊感慨道。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大致上可分成三个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时至今日,我们真正能够继承、发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古代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判断、人生理念等。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古代典籍。“所以,继承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少数专业研究者的专利,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义务。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典籍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莫砺锋如是说。
当然,对于多数大众读者来说,直接阅读艰深的典籍尚有困难,或者具体条件不允许他们像专业研究者那样皓首穷经,这就需要对经典古籍进行普及性的介绍、导读与讲解。
“专业研究者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对典籍进行严格的文献整理以及精深的学术研究,然后要做好认真负责的普及工作,两者不可偏废。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学术基础,后者是前者发挥社会效益的必要传播载体。”这是莫砺锋一直以来秉持的鲜明观点。多年来,莫砺锋本人即躬耕于传统文化学术领域,造诣精深,更身体力行,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也就是说,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虽然应有坚持坐冷板凳的精神,但学者的目光也应穿透学术象牙塔的壁垒,进入整个现代社会。我们固然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古籍整理成果,也要向社会贡献更多更好的古代经典的普及读物。每一个专业研究者都热爱其研究对象,既然经典古籍这么美好,为什么不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呢?为了让经典古籍走进大众阅读与大众生活,专业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
从另一层面而言,读者也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提高对古籍的阅读理解水平,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要层层提高,使我们的读者具备更高的阅读古代优秀典籍的能力。
原典阅读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已经在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层面酿就了醇厚的文化认同、家国认同。当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而来的消费主义时代下的娱乐阅读风潮,吹淡了这种醇厚感。近年来,传统文化出版风潮的兴起,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的热播,又让经典阅读重新映入大众的视野。碎片阅读、浅阅读和娱乐阅读,固然也是阅读的一个部分,但归根到底,阅读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还是在于培养读者的思考能力、思辨精神和价值认同。而对阅读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认同,需要全社会层面的共同引导。
“只有多角度多层面共同努力,才能真正让经典走向大众读者。”杜泽逊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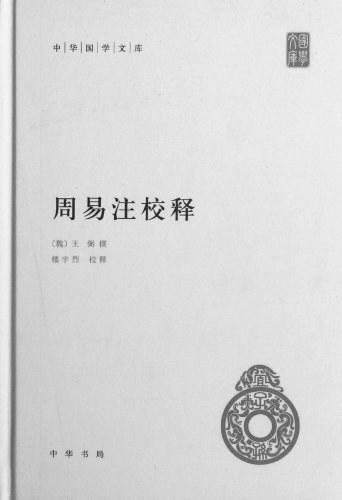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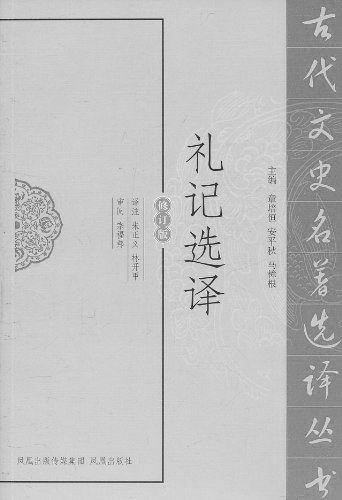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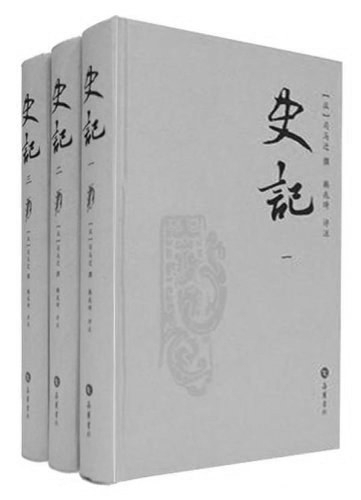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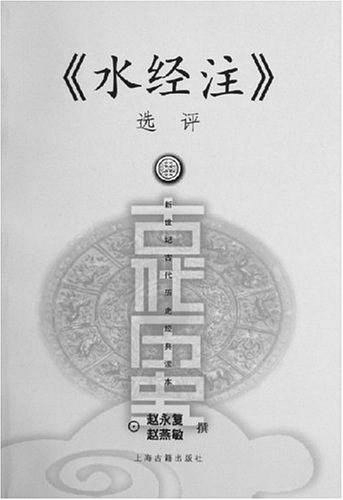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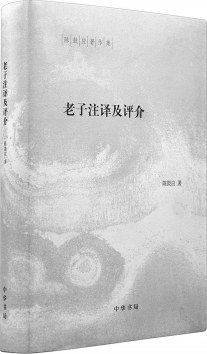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