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施家彰(ArthurSze,亚瑟·施)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华裔诗人、译者,现任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美国印第安艺术学院(In-stituteofAmericanIndianArts)荣誉教授,是圣达菲的首位桂冠诗人。施家彰目前已出版诗集十余部,获奖众多,并在2019年凭借其新作《视线》(SightLines)荣获第7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NationalBookAward)最佳诗歌作品奖。中国佛、道教所倡导的美学和世界观,对自然世界的关怀和对消费主义幻象的批判等都构成了施家彰作品的底色。
盛钰:中国出版过一本您的诗歌作品自选集《猪西天客栈》(Pig’sHeavenInn),其中您对自然的描绘令人印象深刻。
施家彰:自然(nature)与精微(preci⁃sion)在我的诗歌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诗词尤其重视对自然与精微的表达。我对自然的亲近,一部分源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与诗学传统。写诗是一种将自己置身于某一个时空,清晰地观看和体验的方式;而想象,在创作的过程中,成为了一面镜子,一个镜头,又或者一种类似于转换器般的存在。当你凝视自然之时,你会学着仔细地观看;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够更加认清自己——重新理解自己。此外,除了变成一面镜子,思维/想象也可以是一扇窗,透过它们你能看清、体验这个世界。你也可以将这种对自然的利用视作一种超越“无限”的方式。所以,若你能够关注自然细节的本身,并置身于其中去洞察它,那么,那些具体的事物,那些殊相(theparticular)便能够透过诗歌创造共相(theuniversal)。
盛钰: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古典诗词,据说您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翻译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的作品了。
施家彰:是的。透过翻译中国古诗词,我学习到了属于我的诗学技巧。现在,翻译对我而言依旧很重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和这些古诗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唐诗对于创作早期的我而言意义非凡,它们教会了我如何凝练字词,如何更好地将想象力和情感集中起来。这些古典诗词非常简练:一首五言绝句只有20个字,而七言绝句的四行也仅有28个字;对于我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言,开始时我会写同样凝练的抒情诗,但是后来进入到新的阶段,那些诗歌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唐诗的词汇——像是“月亮”“河流”“酒”“星星”这些意象,总是无限地重复——我开始感觉到
它们的束缚,要知道我们的世界是那么多样与广阔。因此,后来的我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中,若将一首短诗喻为一个制作精良的陶罐,我发现我不得不将那个罐子拿起来,丢在地上,摔碎它——为的是将事物打开,并在其中发现新的可能性。
盛钰:在《猪西天客栈》的前言中您还指出,只有当诗歌尽可能地简单,而同时又尽可能地复杂之时,它或许才会最为动人。这种诗歌的境界是否和佛教的“空观”有些类似的含义?
施家彰:是的,“简单”可以和佛教对于“空”的理解相联系,我相信诗歌能在“强度”中得到“简化”:当想象力和情感的能量被聚集,事物反而会变得简单。但是一首诗通常是复杂的,包含着多层的意义和情感的回响。诗歌中的词语可能看起来十分简单,但事实上其中蕴含的强烈体验和情感共鸣则常常颇有深意。这就是我说的试图找寻尽可能简单,同时又尽可能复杂的诗歌,如此这般,一个简单词语的全部意义才得以呈现并在人们心中产生共鸣。在一首诗被“充电”和赋予多元意义的过程中,
宇宙便在其间展开,而后合上。这很像佛教洞察事物的三阶段——那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盛钰:简单的诗句中蕴涵着超越宇宙的深意。说到复杂与简单,现阶段很多的当代诗歌,比如一些视觉诗,用词相对简单,并常常配合碎片化的词句罗列和一些看似高级的处理技巧。这些诗歌符合您对好诗的标准吗?
施家彰:应当视情况而定。很多高度碎片化的诗歌,其危险之处在于创作相对武断与表层,或表现为一种炫技,它们将更多的创作重心放在了技巧本身。倘若不存在缜密并潜藏其中的想象力与情感,它对读者而言就只是逐渐衰减的回响,最终人们会对它失去兴趣。而另一种情况则不然,或许读者在阅读之初并未能体会到原初作品的完整力量,但其中总会有一些东西在一直吸引着读者重新回到诗歌里——可能是一个充满音乐韵律的词组,抑或一个萦绕心间的意象。根据我的经验,一些伟大的诗歌——例如叶芝晚期的一些作品——可能我并不理解其中的一些文化/历史所指,也不清楚他的“螺旋”是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契合进他对于历史的想象之中;但是,他的语言就是有着魔幻般的力量,牵引我不断重回其中,并在时过境迁后向我展露出“本来面目”,我深信这种诗意形成的过程。相反那些站不住脚的诗歌却总是会让人感觉到牵强与造作;它们不具备岁月沉淀过后显现出的决定性能量。
盛钰: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施家彰:作为一个站在中国当代诗歌之外观望的人,我认为中国诗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国当代诗人们已经向西方学习得足够多了,有些诗人也在尝试一些早期的资源,使现在和过去相融合。诗人们也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创新者”(in⁃novator),创新实际上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那可能会导致很多肤浅的创作,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些碎片诗,它们无法长久流传。因此对于中国的诗人来说,或许可以,也是时候回归——回归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内在的必要性。
盛钰:您曾经将诗歌的诗行类比为时间线,希望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施家彰:我认为诗行是在时间中展开自己的,例如一首“一行的俳句”(one-linehaiku)。在日本俳句翻译家佐藤宏章(Hi⁃roakiSato,1942—)看来,俳句在被译成英文时,无需完全按照五言、七言、五言的音节被译成三行。取而代之的,我们可以将一首俳句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有推进力的瞬间和效力:它是转瞬即逝的一个闪光,是一种“顿悟”(satori)。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种单行的诗句充满力量。如果我在写诗,我会清楚地感知到这行诗被创造出来所经历的时间,同时我也十分清楚阅读一行诗如何占据时间流中的一个瞬间。“空”与“留白”的围绕创造出诗句自己的世界,如同照进黑暗中的一束光。很多西方人都错误地理解了佛教的“空观”,认为那是一种“虚无”,他们没办法将其理解为“气”——对我们而言必不可少的呼吸,在它的空间里洋溢着的能量和潜力,是使一切事物发生的基础。因此,我想赋予每一个诗行这样的体验和时间感知力,从而改变一首诗的整体经验。大多数的西方读者只想像读散文一样阅读诗歌,但当他们遇到这样的留白之时便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这是什么,正是那个瞬间,即人们并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就是诗歌意义展现的关键时刻。它是一个供读者参与和体验的“喘息空间”(breathingroom)。
盛钰:您的诗句充满不同意象的组合,阅读这些诗句使我想到了以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意象派、客体派的诗歌。比如您的诗作《树叶的形状》(TheShapesofLeaves),第一句就将深刻的情感赋予多种叶子的意象,我在阅读之时感觉这些树叶仿佛就在眼前飘动,这样的视觉效果让我感到奇妙。
施家彰:我很喜欢威廉斯诗歌的一个特征——他擅长透过对意象和具体细节的把握来使读者能够看到、体验到。威廉斯在诗歌《在墙之间》(BetweenWalls)里描绘了他在停车场看到一个碎玻璃瓶的场景,生活中我们可能并不会注意这个瓶子,但是在他的诗歌里,玻璃有着锋利的边缘,承受着太阳光线的击打。因此,当你能停下脚步观察、创作出一些能让读者看到和体验到的事物细节,诗句便会充满力量。这是我觉得自己和他所共有的特征——渴望利用微小细节,你可以从佛教思想的视角去理解它,将这些细节视为通往觉悟之路的便车。我会有意识地尝试使用视觉力量和细节描绘——透过诗歌的隐喻,情感就是树叶,倘若一片叶子改变了形状,那么它所对应的情感形状将会如何变化?若仔细地观看,你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模糊的感情;它们包含着细微的差别,有不同种类的快乐、痛苦和悲伤,还有兴高采烈和激动彷徨。因此,我尝试赋予那片叶子的边缘以情感,我也尝试使用一些其他物质的边缘来表达“空寂”的张力,那里便是“发现”之所在。
盛钰:面对这些意象、诗组、虚无和圆满,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在阅读您的诗歌时,我看到了东方美学思想、中国宗教思想、深厚情感和当代写作技法的绝佳融合。
施家彰: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我不会局限于此。就像是两条大河融会贯通。因为我不会用中文写作,我的诗歌离那种古典的传统还很遥远。我出生在美国并用英文写作,因此我和传统之间有着足够的距离和空间。要是我在中国生长的话,事情就会很不一样了,我可能会更加感受到被诗歌传统和历史所占据。因为我处于一种语言、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状态,这些距离给了我更多的创作自由,使我能够在文字间灵活游戏。
盛钰:您觉得不同的感觉和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情感对您的诗歌写作而言重要吗?
施家彰:我认为是重要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美国评论家海伦·范德勒(HelenHennessyVendler,1933—)曾经提到过一个诗人需要两样东西:想象力和对语言的掌控;此外,我认为在写作中还需要添加情感(emotion):诗人需要充盈的情感,因为想象力和深刻的情感会帮助语言塑形为必要的、合适的形态。一首诗需要这样的深层情感,倘若没有,你便只是得到了一首聪明的、有着创新语言的、碎片化的诗歌。用禅宗佛教的石头花园来打个比方,花园中的石头来自地表之下,而在地下还有着更多这样的岩石;而在一首诗中,一种潜藏在表象之下的力量使语言跃然纸上。一首有力量的诗歌能让你感受到文字深处所存在着的某种更强大的东西。
盛钰:您曾在演讲中介绍过生态诗歌对于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您尤其强调佛教思想与道教、老子思想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影响。您能分析一下东方宗教信仰对当今美国诗人的影响以及在美国当代诗人中的呈现状态吗?
施家彰:我的生命浸润在佛教之中,假如你阅读我的诗歌作品,佛教的影响清晰可见,但是我不认为我必须去参加一些每个周末固定的佛教仪式来证明我是一个佛
教徒。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一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是佛教徒,一个修行中的佛教徒”,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是我会稍稍和它保持一些距离的原因。我住在圣达菲,新墨西哥州,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我记得有些人跑来跟我说他会写中国书法,还能教中国书法;但事实证明,他才学了六个月的书法。与其说他是个老师,还不如说是个半吊子。佛教的修行和这个是一样的,我认为那是一件你需要花一生时间去学习的事情。佛教在美国广受欢迎,但是我质疑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进行了深层次的修习。或许是因为禅宗佛教在冥想中对时间和空间的优先考量,给予了人们内心的和谐性(innerharmonization)以足够的时间来对抗美国的消费文化,禅宗所创造的独特空间尤其吸引作家们,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富有安全感的空间(safespace),在其间他们能够进行语言和诗歌的游戏与实验。
盛钰:您在最新的诗集《光线》中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些诗歌带给我一种透过万花筒观看这个世界的感觉,您的诗句就好像是里边的多面镜,把每天生活的不同碎面投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例如在《地书》(WaterCalligraphy)这首诗中,多元的意象总是在不经意间穿越时空的边界,意外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直击我们的心灵。您会有意地记录下生活中的片段吗?
施家彰:《地书》这首诗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之时所观察到的日常场景,我很喜欢利用每天的日常生活去创造更广阔的、万花筒般的诗歌效果。
盛钰:我尤其好奇您在诗句中对“删除线”(strike-throughline)的运用,让我读来有些费解,但却微妙、感伤,您让我看到创作过程成为了艺术品本身。
施家彰:这些删除线一方面隐含着(被划去的)文字有被表达出来的必要性,而这些文字被删掉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准确。这种方法在法语中叫做SousRature(“在删除中”),马丁·海德格尔曾将删除线开发为一种哲学话语,他指出:“因为词语是必须的,它们保证了可读性;因为词语是不准确的,它们被删去。”我认为深邃的诗歌拥有着能将读者一遍又一遍拉回来的能力,这样,诗歌的体验便不会走远,并在情感和想象力的作用下变得更强烈、更深远。
盛钰:我在翻译您的这本诗集时体验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位置”(place)似乎在这些诗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您还会经常使用类似“弧线”“点”“线条”等几何词汇;透过在东西方世界的穿梭,您将不同的空间组合在一起,建构了属于您的空间诗学。此外,中文和英文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也在《视线》这本书中不断出现,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我将它们也视为您空间诗学中的重要组成。
施家彰:是的,中文和英文就好像是我的两个磁极,我经常在两者之间移动。我对于空间的使用是多层且共时的,在我的作品中,位置(place)总是在不停地被建构——就像一些人所理解的,位置不是静止的!
盛钰:下一个问题有关《视线》这本书的实验性特征。您将主题诗《视线》拆分成许多一行诗,并别出心裁地将其安排于全书的各个角落,偶然间的空白页伴随着突然出现的诗行,使读者在翻阅整本书时获得间接性的时间和空间,来思索、品味、停歇,从先前的诗歌中跳出来,这就像是心跳的起伏,给予整本书独特的阅读节奏。此外,您在书中对标点符号的戏剧性使用也独具特色,您对破折号所进行的节奏型修辞处理赋予了诗行以生命;在《盐之歌》中,您甚至将所有标点都省略,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长的句子。
施家彰:按照英语语法规则,当需要一个突然的转折或跳跃的时候,会用到破折号。在这本书中,破折号被推向了一个极端,抛开等级观念,我将形态各异的视角、观点和水平线交汇融合其间。而《盐之歌》这首诗是用“盐”的声音来模拟人类说话,因此说话的形式、语言以及节奏的把握都和别的诗歌有所不同,为此我去除掉了所有的标点符号。
盛钰:包含这本书在内,这些年您在诗歌和艺术的创作中进行了许多实验性的尝试,我很喜欢您在2014年和雕塑家苏珊·约克(SusanYork)的艺术合作,还有您之前和华裔音乐家谭盾进行的精彩合作。作为一位当代诗人,您认为跨学科的合作交流对诗歌而言意味着什么?此外,我很喜欢您诗集的封面设计,像是1998年《红移之网》所选用的水墨画,还有这本《视线》的封面——一幅禅宗圆相(Ensocircle)图。在您接下来的作
品中还会有哪些实验性的尝试?
施家彰:你提及的这两次尝试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1985年,我遇到了作曲家谭盾;1988年,当谭盾搬到纽约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了诗歌音乐项目“丝绸之路”;并在1989年4月1号和2号在圣达菲当代艺术中心进行了首次公演。这次合作让我思考了许多关于音调的变化、戏剧性的张力以及叙述的断裂的问题(详见《布鲁克林铁路》杂志2019年10月对诗人的专访)。通过观察作曲人如何创作音乐,雕塑艺术家如何处理戏剧,我在诗歌语言的使用中发掘出全新的可能性。我在2021年最新的英文诗集《玻璃星座》(TheGlassConstella⁃tion)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性尝试,例如我对传统的日本诗歌形式“俳文”(haibun)进行了修改(另一种日本诗歌的经典形式是短歌[tanka],一种按照5-7-5-7-7音节安排的五句体歌体)。在日语中俳文有着比俳句本身更长的散文主体,我的英文俳文表现为俳句形式的散文诗,每首诗四个小节,利用7-7个英文音节相连接的方式。放弃冗长的诗篇,这些诗歌表现为俳句以及英文短歌的互相嵌套模式,在其间,散文诗便可以展开其叙事的一面。
盛钰:随着全球性的疫情爆发,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1919—)在2006年出版的《盖娅的复仇》(TheRevengeofGaia)一书中所指出的,因为人类对化石燃料的贪婪的开采,我们的“盖娅”——地球正在面临生态环境、气候的极度恶化,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她会惩罚我们,将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您也曾在国家图书奖的获奖致辞中说:我们现在比任何时间都需要诗歌,面对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和人类中心主义带给自然的伤害,诗歌,尤其是生态主题的诗歌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觉得生态诗歌需要充盈着佛教哲理中所强调的对世界的悲悯之心。对您而言,生态诗歌的核心精神和全新的任务是什么?
施家彰:我喜欢你对于生态诗歌应该践行怜悯和慈悲的观点。的确如此,就生态诗歌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人类关系体系的重新评估而言,悲悯之心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我的诗歌和生态诗歌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尽管我个人并不相信所谓的诗歌运动)。我在创作时常常破坏“位置”和“线性时间”的稳定性,而那样的主题对于生态诗学而言意义非凡。此外,我会经常性地改变人称代词的写作方式,这也破坏了无数西方诗歌所依赖的“我”(I)的坚固地位,透过这些观察视角和观点的改变,我试图在诗歌中重新定义“自我”(self)。
盛钰:作为一位优秀的美国当代诗人,您的诗歌中拥有沿袭自惠特曼、庞德、威廉斯等诗人的宇宙意识,并实现着和更广阔的自然世界的连通,我能够在众多的中国古代的诗人们身上找寻到您的这种意识。您会给热爱诗歌写作的中国学生和年轻诗人们什么样的意见?您对于中国读者的期待是什么?
施家彰:作为一位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我可能无法给中国的学生和年轻诗人以足够的意见,但正如德国诗人莱纳·里尔克(RainerRilke,1875—1926)曾经说的那样,一首诗歌作品是好的,只要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倘若一个人想要成为诗人,他/她必须要根据诗歌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这些对于初学者是很重要的。对于阅读我的作品的中国读者们,我会简单地期待他们——任何一位读者——用自己的方式,透过心灵,勇敢阐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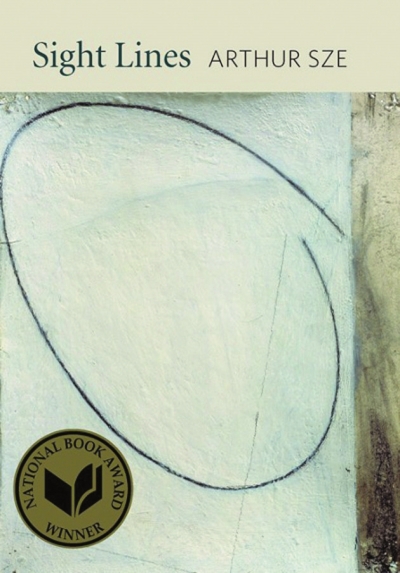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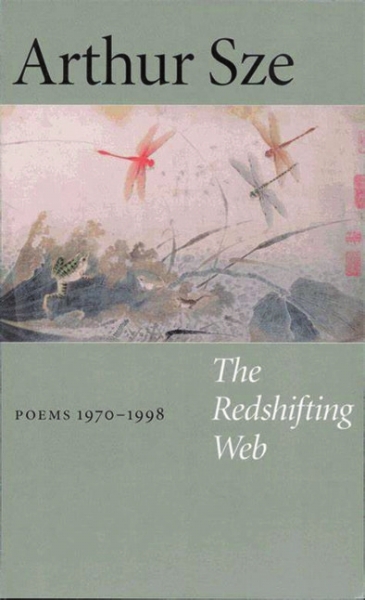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