绫、罗、绸、缎、丝、帛、锦、绢,中国织造技术的成就不胜枚举。自先秦时《考工记》到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在千百年来演变的女红中,尤以缂丝最受尊贵,自唐出现以来便迅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两宋时的缂丝以完美再现甚至超越原作的特点成为最接近于书画艺术的丝织物。“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中产生的缂丝也成为了中国丝织技艺的巅峰。都说一寸缂丝一寸金,到底缂丝好在哪里? 我唯一的印象就是“贵”。
一直觉得丝绸、刺绣之类的东西,男人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不是大事,况且之前对缂丝的印象只是“贵”,被拍卖会成交的天文数字吓到,一堆零,从个位开始数吧,反复确认,剩下唯一的印象就是:怎么这么贵?
一寸缂丝一寸金,话都这么说,可到底缂丝贵在哪里? 真不知道。
这就埋下了一个坑。不出意料,第一次看到缂丝的时候,有点蒙,巨幅《缂丝无量寿尊佛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保存也相当完美。好比是一个人自幼在山里修行,没见过姑娘,下山去,遇见的第一个就是绝世大美女,倾国倾城,你说吓不吓人? 可自己还一点都不稀罕,也不觉得走运,随随便便就放了手。关键是一开始的起点太高,今后遇到的其他姑娘都不觉得怎样了,等想起来再找第一个,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这才叫痛苦。
《缂丝无量寿尊佛像》、兽面纹三牺尊、乾隆版《大藏经》,还有阅古楼石刻拓片,都一起出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园说”大展里,这是北京市属公园馆藏文物的首次大集结,颐和园、天坛、北海里的很多宝贝都是第一次“出宫”。机会难得,算是不能不看的一个展,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巨幅的《缂丝无量寿尊佛像》。
当年,乾隆皇帝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六十大寿修建了清漪园——也就是今天颐和园的前身,而眼前这幅缂丝展现的就是他设想的天仙、罗汉、天王通通来祝寿的场面。“无量寿”的意思是“寿无量”,乾隆顺便也cosplay了一把,自己也入画,里面头戴斗笠、身穿红袍、双手合十的人,就是扮作罗汉的乾隆皇帝。
乾隆的事情太多了,还是先说缂丝吧。
所谓“缂丝”,宋元时期也叫过“刻丝”“剋丝”“克丝”,源头指向的是古埃及,西汉时这种技术通过丝路东传到西域。缂丝因为独特的“通经断纬”技法,算是目前唯一没法用电脑排版批量生产的丝织物,无法工业化,这就是贵的首因。
拿刺绣来对比一下。刺绣是在现成的料子上穿针引线绣出图案,而缂丝是在纺织的同时就织出图案,料子和花纹图案是一体成形,一气呵成。织机上,本色丝为“经线”,各颜色的丝为“纬线”,一个是“竖”,一个是“横”。
这个过程真让人着迷。一幅牡丹花丛,各种色彩,不同颜色花瓣,不同程度深浅,缂丝都得照稿样一点点地织出来,本色生丝挣在木机上,小梭子牵引着各色纬线,按照稿样的色彩一截一截穿梭,两只脚踩着织机踏板,经线随着上下错落,一堆小梭子放在一旁,按照颜色长短穿经线而过,织工手里拿着的篦子再把织上的纬线贴紧,慢慢累积而成。
对粗枝大叶的人来说,想想整个过程,都觉得要疯掉,好比是让人用绣花针去挖井,没想到最后变成了“肖申克的救赎”。所以,下次碰到好的刺绣和缂丝一定要大大地赞美一下。
明白了这种“通经断纬”技术,再兜回头说说这种技术的源头。主流的观点是,3000年以前,埃及出现了以麻做纬线的“缂麻”,后来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叙利亚人又从埃及人那里改良了一下,用羊毛为原料做了“缂毛”,张骞凿空西域后,缂毛的地毯和衣服就自西向东而来,我们就地取材用蚕丝为原料做了“缂丝”。
但凡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艺术形式,总是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宋徽宗。我关注的文博公众号里,每次出现转发过万的软文,总跟他老人家有关。受这位入错行的伟大艺术家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宋朝基本定了型。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时期设立了少府监,下辖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其中文思院四十三作坊之一的“克丝作”,就是专门装裱缂织书画用的。宣和时期的缂丝工艺发展得真是大步流星,从日常穿衣打扮到书画装裱无一不精,尤其是以定州的缂丝最为著名,宋人庄绰的《鸡肋编》中有描述: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丝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
南宋时期,政治南迁,大宋仅存的一口气,仰仗的是长三角贸易,从那时候开始江浙就已经是全中国的CBD,有钱人扎堆,关键还有了点品位,知道东西好坏。缂丝作为一种丝织与绘画相结合的高级艺术品,不仅迎合上流社会的艺术需要,也自上而下在富庶的民间有了市场,一时让朱克柔、沈子蕃这些名匠的作品变得炙手可热。
朱克柔,一个生活在江南烟雨之地的女子。真不知道她父母怎么起的名字,原名一个“强”,字“刚”,自称“克柔”,能这么叫自己的上海姑娘,怕也是“绝望主妇”的人设。据说宋徽宗赵佶曾在朱克柔的佳作《碧桃蝶雀图》上题诗:
雀踏花枝出素纨,曾闻人说刻丝难。
要知应是宣和物,莫作寻常黹(zhǐ)绣看。
“要知应是宣和物”,这话说得很豪,够自信,不过那时候也有骄傲的资本。只可惜,靖康年一到,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徽钦二宗被掠到东北。随着浩浩荡荡的俘虏队伍北上的,还有数百位御用工匠,加之金人的虎狼之师南下搜山检海,别说《碧桃蝶雀图》失传了,包括朱克柔在内的大宋姑娘们如何经历这场劫难的,谁知道呢?又有谁关心呢?
还好,在一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作品《山茶蛱蝶图》里,引出了这位奇女子生平的唯一线索,题跋上,文徵明的曾孙、明代画家文彦可写道:
朱克柔,云间人。宋思陵时,以女红行世。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尤成罕购。此尺幅古澹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至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工”而名留青史的奇女子,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就有“三绝”,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14岁就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字仅粟粒之大,点画分明;还有明代韩希孟的顾绣、清末民初的沈寿……
再说另一位缂丝大师沈子蕃,性别男,籍贯河北定州。靖康之后,42岁的他开始到南方收徒传艺,1165年去世,享年79岁。沈子蕃一生完成了几十件缂丝艺术品,有的未标作者,标有作者的只有五件,《梅鹊图》《青碧山水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另三件《缂丝山水图》《缂丝秋山诗意图》《缂丝桃花双鸟立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想分辨朱、沈两位大师的作品并不难。
朱克柔的作品似于工笔,善局部,颜色鲜艳,对比强烈;沈子蕃则善写意,山水作品大,重和谐,清远优雅。这个区别好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两位大艺术家男女有别,一个生在北方,一个生在南方,北方的一路南下见过大山大河,而南方的养在深闺足不出户。宋朝时候的女人已经开始缠足了,别说跋山涉水,出趟远门也有难度,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交网络,一辈子见到的人和景,还不如人们今天一天的量。
南宋亡于元,元代缂丝一反南宋细腻柔美之风,简练豪放。而且在西域织金技术的影响下,在缂丝里面掺了金丝,用作皇帝像和佛像,也就是“织御容”,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明暗对比,胡须发毛,还都要通过一根根丝线表现出来。这个真难,不过这技术后面清朝的工匠们用得更精,我在颐和园德和园戏楼的“福寿文物展”上见过,是一种奢侈的漂亮。
明初倡节俭,朱元璋的出身决定了缂丝绝对属于“淫巧”范围,除了敕制和诰命,其余基本就不用了。一直到了宣德年有了内造司,也赶上明中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缂丝的需求这才上来。到了清,江南三织造成为丝织业中心,缂丝在乾隆年间才开始再度繁荣。
清代藏传佛教备受推崇,大概在清朝的所有皇帝中,最尊崇藏传佛教的,就是运气好到没谁的乾隆帝了,他就曾命令画师为自己绘制了一大批佛装画。按佛教的教义:
若有众生于佛灭后,造立形象,幡花众香持用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除却千劫极重恶业。
佛造像,就是古今中外佛教僧众们供奉诸佛的功德。所以,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缂丝佛造像就成为乾隆的必选项目。想办成这事,不动用国家机器根本不可能,展览里的《缂丝无量寿尊佛像》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看着眼前的缂丝,觉得很伟大,但也有些遗憾,就是太大了,大得让我无法体会到赵孟頫的四个字:尽其妙也。只觉得乾隆爷豪横。
想起来,跟皇家沾亲带故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有一段描写缂丝的段落“晴雯病补雀金裘”。晴雯所补的“雀金裘”,就是把孔雀翎毛上的羽绒与丝绒拈合后缂织而成。
若没有江南织造的家底出身,见都不可能见过,曹雪芹也绝不可能写出这段文字。
时至晚清,大清国气数已尽,皇子龙孙们断了花销进项,只能变卖祖宗家产。老恭亲王奕的嫡孙爱新觉罗·溥伟无法面对现实,一气之下躲进了青岛德租界,而府里的珍藏也悉数被拍,包括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在内,一捆捆丝绣就夹杂在成堆的书画中,辗转被一位懂行的人收藏了。巧了,他和朱克柔一样,也姓朱。
朱启钤,真是个神人,用曹聚仁先生的话说就是“会做官”。警察总监、交通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登极大典筹备处处长、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等,都没耽误。朱家是举人出身,家世好,见过世面。据说童年时,他母亲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荷包,而祖父书画的包头用的就是缂丝。1928年,退出政坛的朱启钤在北京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当时的胸襟抱负也够大的:
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那时候的朱先生已经57岁,退休抱孙子了都还这么雄心勃勃,让人佩服。可第二年,营造学社就出了问题,没钱了。
拒绝过日本人大仓喜八郎的百万银圆收购,也下定了坚持将国宝留在国内的决心,无奈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女亲家“东北王”张作霖。朱启钤的六女儿朱洛筠嫁给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于是,同在营造学社里的张学良就用20万银圆的价格将这批国宝接手。
谁能想到,江南的织女们的一缕缕丝线,900年后,却支持了营造学社的学术项目,梁思成、林徽因开始勘探考察古建遗址,走遍了中国各地。
最后,话还得说回去,如果现在你问缂丝好吗,好在哪里? 很奇怪,我的第一反应还是贵。这主要是因为自己活得太粗糙了,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得过且过,与这么精致的东西无缘。当然,还有个理由,就是见过的好东西还是不够多,实在没法比。
也有一阵没听到缂丝在拍卖会上再创新高的消息了。一次饭局上听圈内大佬说:这不是因为价格便宜了,而是缂丝的老东西越来越少,拍一件少一件,市面上都没得见了。
开始说什么来着,才刚刚琢磨出些缂丝的妙来,可惜就再也看不到了。财富的多寡会决定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我,只能尊重现有的生活。纳博科夫说过,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向别人解释作品好在哪里。所以别再问缂丝好不好了。
(本文摘自《慢慢看:一个人的博物馆》,董彬著,文津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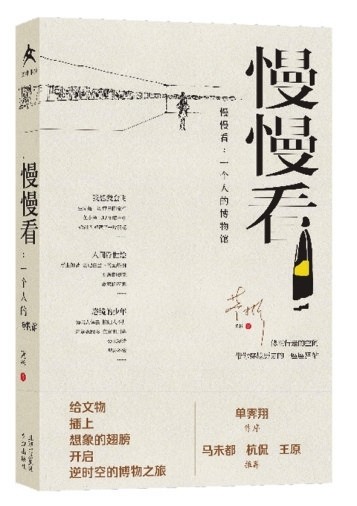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