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九年(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国,决心告别政治,专心从事学术著述。在这一年,他的一部力作便是泽溉数代、影响深广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之撰著,如众所知,其直接缘起是蒋百里为《欧洲文艺复兴史》请序,而远一层因缘则是胡适的建议:
胡 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清代学术概论· 自序》)
这两层是学界所熟知的。在新校本《清代学术概论》的《校订说明》中,校者俞国林先生又抉发出任公撰著《概论》的另外几重“远因”:其一,任公亲历清季民国变局,于清初学术有“异代同符”之感;其二,任公曾于1918年暑期为儿辈讲“学术源流”,梁启勋跋谓此宗讲记“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矣”;其三,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为梁启超、梁启勋诸生讲古今学术源流,任公撰《概论》,其实是远绍当年万木草堂旧事(俞校本《校订说明》,p5-10)。
无论是近因还是远因,皆可看出《概论》一书与作者、学林、世代的丝缕缠绕。实际上,《概论》撰著之时与之后,民国学人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尤其是胡适、蒋百里、顾颉刚等,乃书稿的第一批读者,诸人于《概论》多有订补,其始末详情,俞校本《校订说明·初稿与定稿》一节考之详矣,可以参看。下文拟结合民国时期的书报尺素,钩沉史料,略窥民国学人对《概论》的评骘。
二
在《概论》出版之前数月,也就是1920年10月21日,张元济在日记“编译”条作了如下记述:
访卓如,言著有《有清文学变迁史》一册。原为蒋百里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不料愈作愈长,与蒋书相等,只可分行。(《张元济日记》下)
这则日记,为我们存留了《概论》的早期题名情况。当然,此处“文学”二字,恐是张元济误记,应作“学术”,因为在任公笔下,凡用“文学”处,已经不是文言语境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涵义了。俞校本曾引任公与张东荪函,中谓方撰《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又引1918年任公与仲弟梁启勋函,中谓方为儿辈讲“学术流别”(俞校本《校订说明》,p6-9)。《概论》另有一省称曰《清学概论》,见于梁启超的《自序》。据此可见,《概论》在定名之前,有着多歧的制题。后来,梁启超考虑到此书原为书序,体例有不自惬意之处,“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张元济撰日记的次年,1921年2月,《概论》单行本出版。3月27日,《申报》刊载了一则书讯:
是书为梁先生所著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内分三十三节,将有清一代学术元元本本,阐述靡遗。学者得此,于清代学术之原委,可以洞知其大凡矣。书中句读符号,悉从新式,实为先生最近之著作。
这也是《概论》第一次走进大众的视野。此后,胡适、傅斯年均曾有意撰写书评,可惜最终皆未动笔。不过,此书的影响实际是不胫而走,对并世学人启益颇著。林语堂曾坦陈,《清代学术概论》这小册子是他“摸到清代学术思想门径的好指导”(《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张舜徽也曾回忆,早年“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尤好之不忍释手,读之终卷。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
盖自此始”(《旧学辑存 · 忆往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君劢访问新亚书院时,仍以《清代学术概论》作为讲评文本,并追忆了当年与任公的交游。
柴德赓认为,“近人讲清代学术史,自以梁任公先生为首创”(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 叙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民国学人喜讲清代学术源流与系谱,如罗振玉1931年讲《清代学术源流概略》,章太炎1934年讲《清代学术之系统》,尽管未必可坐实是任公《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刺激下的产物,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在讲清代学术史的时候,心中有任公的著作在。任公《概论》的撰写,是接纳了胡适的建议,而任公此书著成后,在多个层面对胡适产生了正向的激发。在清学史二种之前,任公曾撰写《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惜最终属于未定之稿。尽管如此,此文却提振了胡适的学术志气:“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四十自述》)另外,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脉络与衡鉴,梁启超也对胡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对于晚清诗人,《清代学术概论》仅举郑珍、金和二人,胡适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增刊上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举代表诗人即与《概论》相同。当然,杨洪烈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梁任公遗漏了诗僧苏曼殊,感慨“这天才卓绝的文学家苏曼殊,却始终没有一个位置”(《苏曼殊传》)。
任公此书所创设的“体制”,被钱穆评为“大可取法”。尽管在此书之前,已有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诸文,皆具综合推阐的特点,但皆篇幅不多,难以于尺幅之间见千里之势。唯独《概论》一书,分类
讲述,发凡起例,俱见学术之眼光与胆识。并且,《概论》的学术见解,也有民国学人(如刘太希)认为超过了章太炎《国故论衡》的《清儒》篇(《记梁任公》)。此书中的很多原创性观点,开后世无尽法门,最为学界所称道的是,《概论》三次言及“文献学”,后来的学人奉之为宗祧,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提出者。另外,在《概论》中,梁启超有一段评价乃师康有为的断语说:
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p132)
后世在评价康有为时,多引任公此说,以为“精确不移,诚定论矣”(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三
《概论》出版后,民国的学人也并未因任公晚年的声闻高华而为贤者讳,相反,他们会直率地指出此书的不足,或发于私议,或刊诸报章。在众多学人中,系统予以纠驳者,首推李审言。他曾撰《清代学术概论举正》,在沪上择要刊载,匡订任公论事多乖、引证疏谬之处十几条,可惜此稿全文遗失,无由窥其全豹。又如《概论》的《清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异之点》一节,论乾隆诗人袁、蒋、赵三大家,早期刊本如《改造》本、《合集》本皆以“赵”为赵执信。郑逸梅刊《梅瓣集》,专撰一条纠正,指出“与袁简斋、蒋心余齐名之赵,乃赵瓯北”。蒋大椿为此专门致函章士钊,推介在报刊揭载,“俾任公见之,或能于《清代学术概论》重版时,更正其偶
然之笔误也”(《甲寅通信集》)。今核俞校本校勘记,知任公稿本原作“翼”,墨笔点去,旁写“执信”(俞校本,p167),可知任公于此处并非蒋大椿所说的“偶然笔误”,实际是有所迟疑的;于此也可见知识性的疏漏,虽任公这般大家亦所不免。也许是后来任公读到了郑逸梅的札记,也许是另有他人指出,当《国学》本重刊时,任公便改赵执信为赵翼了。
《概论》有一大主线,那便是对清学“文艺复兴”的阐释。可实际上,无论同时还是稍后,民国学人对本书的这一比附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大约也是并不认同。在梁任公逝世的当年(1929),谢扶雅于《知难》杂志上发表评论,很不客气甚且略显“轻佻”地批评任公《概论》以清代考证学、今文经学类比欧洲“文艺复兴”之不伦:“与其说是客观的定断,毋宁说是主观的希望”(《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第一次对这一比附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辩证。随着国人对西学研究的深入,后世自然更不会认同以清学比附“文艺复兴”了。
任公《概论》中的论断,有着典型的儒家人格观念,故而会斥袁枚曰“无行”,而贬龚自珍曰“不检细行”。李石岑曾为二人鸣冤,认为任公“忽视他们关于人生上的特殊见解,这又是何等可太息的事”(《人生哲学》上卷)。如果对这一公案加以评议的话,可以说李石岑并未细读任公著作,盖任公曾开宗明义地讲到“为学之道,人格在第一层,学问在第二层”,这也是任公在《概论》中缕述的“精神”之深义(俞校本《校订说明》,p6)。
更多的学人,则从增补的角度,指出《概论》之未备,例如袁大韶指出任公此书“成书过速”,故多有遗漏失检:“崔述《考信录》一书,辨析上古史事,最为谨严,其鉴别虚伪精神,影响于近代学风甚巨,
故近人尊为‘科学的古史家’。梁书于清代史学大师均有论及,独于崔东壁一字不提。”(《出版周刊》新89号,1934年)另外,清代以经师名儒而治佛学者,梁氏亦遗漏汪缙、江沅、吴颖芳等。至于学问门类,袁大韶认为此书于目录学家及目录学著述完全失载,亦属大醇小疵。
四
任公为文理性清明,元气淋漓,诚如林语堂的评价,是“学者而能笔下发出光辉”(《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故而其书在初涉学问门径的学生层面尤其具有一种“魔力”。1923年,一位笔名“景”的学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一篇书报介绍,撮述了此书的优长之处,大致能体现出高校学生层面研读此书后的心得与收获。后来,燕京大学曾于1935至1936年刊出四卷本《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近人之作仅有7篇,其中便选录了《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些章节。厥后至今,此书之翻刻,无虑数十种。去岁俞校本《概论》付梓时,上距《概论》初刊,恰已百年,重读一过,对俞国林先生所评“融入了著者生命体验的学术史”(俞校本《校订说明》,p39),不由得增一重亲切有味的体会。掩卷凝思,我们可能也会生出这样的浮想:民国时期的学术史,迄今检视得并不充分,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又会有哪位亲历者力担此任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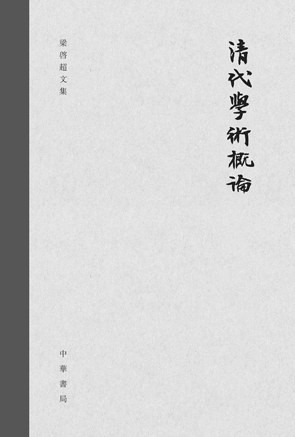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