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先生的儿童文学生涯,广涉创作、翻译、编辑等领域。他在每一个领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一座令人仰望的丰碑。而外国儿童文学译介,无疑是任溶溶在漫长的文学岁月中投入心力最巨,累积成果最丰,介入人们的阅读生活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历史发展十分广袤、深邃的一个部分。
从1946年在《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第一篇翻译作品——土耳其作家萨德里·埃特姆的儿童小说《粘土做的炸肉片》开始,数十年间,任溶溶穿越于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间,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可以说,他的儿童文学译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70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译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和侧影。《克雷洛夫寓言诗选》《伊索寓言精选》《普希金童话(诗歌)》《俄罗斯民间故事》《马雅可夫斯基儿童诗选》《马尔夏克儿童诗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古丽雅的道路》《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小飞侠彼得·潘》《小熊维尼·阿噗》《奥芝国的翡翠城》《寻宝六人组》《杜利特医生》《北风的背后》《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长袜子皮皮》《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好心眼儿巨人》《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女巫》……如果把他所有的儿童文学译作依照翻译出版的时间顺序汇聚在一起,我们几乎就会看到中国读者眼中外国儿童文学世界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脉络和景观,也会看到这些译作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艺术演进及童年阅读生活的巨大投影和深刻影响。
任溶溶先生的翻译作品语种多,数量大,最重要的是,他以其高质量的翻译,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众多经典的译本。我一直认为,文学的翻译从来不只是译义,而必然包含着语言形式的再发明与再创造。因此,优秀的文学翻译必定同时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翻译者本人也必定是同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作家。
就此而言,任溶溶作为儿童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的才华和智慧,既为他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文学资质方面的基底和依托,也在这些译作里留下了鲜明的“任氏”烙印。他翻译的科洛迪、罗大里、林格伦、达尔等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在我眼里都是无可替代的经典译本。《木偶奇遇记》的顽皮幽默,《假话国历险记》的讽刺夸张,《长袜子皮皮》的天真不羁,在他的译笔下尽显生动与神采。我每在课堂上或讲座时分析到这些作品,必定要带的是任溶溶的译本。书中有些片段,因为钟爱的缘故,一读再读,除了感佩作者的才华,每次也都忍不住要为译文的精彩击掌赞叹。
在我看来,故事作品的翻译,最难的常常是对话,但最见功力也是它。简简单单的对白,意思、感情、个性都在里头,你一言我一语的滋味也在里头。读任溶溶翻译的角色对白,常常感到极大的享受。《木偶奇遇记》开头,皮诺乔造出来以前,木匠安东尼奥与皮诺乔后来的爸爸杰佩托之间那场充满孩子气的对话与争吵,看着只是日常交谈与争执的啰里啰嗦、琐琐屑屑,其生动的口吻,鲜活的气息,接应的自然,天真的滑稽,读着读着,不知怎么就有滋有味起来。我有时想,若非任先生那样的译笔,它也很可能真的成为一段十分乏味的啰里啰嗦与琐琐屑屑。还有《长袜子皮皮》里的对话,多是“随口”的胡诌,但难就难在“随口”和“胡诌”的自然而然——表面上一带而过,“其貌不扬”,仔细琢磨,其实增一词则多,减一词则少。
儿童文学翻译的另一难处在儿童诗。儿童诗不能拿语言和修辞的艰深晦涩做文章,其诗意诗境,全在拿日常语言做诗的功夫上。我曾经在《日常生活到一首诗的距离》一文中认为,任溶溶是一位真正用“白话”也即普通的生活语言来写诗的作家。他把日常得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写成了诗,也因此把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他的儿童诗从来不用任何“诗意”的文学字眼,而是以简朴素白同时又充满童趣的口语,如日常说话般地“说”诗,但是很奇怪,他居然就这样“说”出了许多漂亮极了的童诗。他使日常生活与一首诗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微不足道。
任溶溶的儿童诗翻译与他的儿童诗创作,显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其间的关联和奥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课题了。他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马尔夏克的儿童诗,其节奏顿挫、俏皮幽默都融会在平白如话的语言里。他翻译的罗大里的儿童诗《棍子上的屋盖》,“我给你写首诗讲讲下雨/下雨天大家都躲在家哪也不去/我可拿小棍子顶个屋盖/走到东走到西自由自在”,读来简直整首诗里都在滴哩嗒啦地下雨,而那种跟滴哩嗒啦的雨声一样的童言童语,既呼应、渲染、表现着下雨的情境,也点亮了这首诗“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意境。另一首《水城威尼斯》则是静:静静的夜里,水面、石桥与月亮,形与影、实与虚的交织,由至简的语言安排出奇妙的玄机。我既不懂俄文也不懂意大利文,对我来说,任先生的译诗实际上创造了它们在中文世界里的诗意与风格。
熟悉任溶溶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一定知道,这种译笔,也是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典型风格。他的陪伴几代孩子成长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那些简白如话又生趣盎然的儿童诗,其美学的面貌正是如此。所以我说他的翻译是再创作。或许是因为创作个性、趣味与风格上的同声相应,任溶溶先生译林格伦、罗大里、达尔等作家的作品,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他译的达尔的《女巫》和《好心眼儿巨人》,达尔式的欢笑、奇诡尽在其中,却不见任何喧闹的粗声,深藏在底下沉沉的温柔与细致,也都蕴蓄在任溶溶的翻译语言里。
我以为,翻译本身也是创作,并且,深藏着一种精神。那些优秀的译著,耗尽心力把原著的神韵和丰采勾勒、托举出来,译者自己却始终站在文字的背后,沉默地凝视着,声色不露。
我因此对人文领域的一切优秀的译本,充满了敬意。
但优秀的译本是稀有的。对儿童文学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在童书引进出版的热潮里,儿童文学翻译的拓展也十分迅速。但对于操之过急的许多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我也常感到十分无奈。在我读到的许多译文里,充斥着大量未及消化的西语直译表达,在汉语语境中读来,或拖泥带水,或怪异拗口,翻译直接变成了语言障碍的制造者。因为从外语直接译转的缘故,不准确的翻译表达更是常事。这些问题,有时是因为译者不够专业细致,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译者的文学感觉和领悟其实尚未达到文学翻译的要求。因为实在不能“忍受”一些文学翻译的非文学性,我也曾在出版社邀我阅读某些尚未出版的译稿时,忍不住指出其中翻译的问题。在域外文学交流中,翻译不只是通道和媒介,它其实就是文学文本的一部分。翻译的好坏,既有可能“激活”作品,也有可能“毁灭”原著。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同样可怕的或许是,当我们把那些缺乏文学品质的翻译文学作品交到孩子们手上,它们又被当作文学和语言的某种模本接受下来。长此以往,后果堪忧。
关于任溶溶先生的译本,读书界也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例如,如何把握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之间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溶溶先生的整个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课题。如何慎重对待儿童文学的翻译,如何把儿童文学的翻译视作一项重大的文学工程来做,这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必定是充满艰难的。但阅读任溶溶的翻译作品,我们收获的或许也不只是文学翻译的乐趣与启迪,还有为了此生选择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一往无前的单纯的信念和勇气。
《任溶溶译文集》皇皇20巨册,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文集主要收入了任溶溶先生译著中已进入公版领域的作家作品。这是迄今为止任溶溶先生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这不仅是儿童文学译界的一大喜事,也是当代儿童文学译介历史沉淀、文化积累的一件盛事,同时也为广大儿童文学爱好者提供了集中阅读、珍藏任先生译著的宝贵机会。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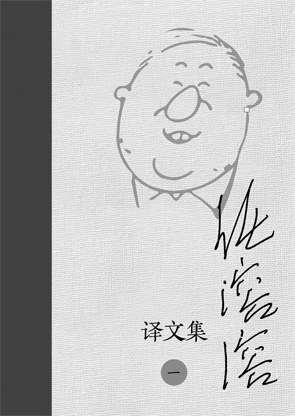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