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史中长期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梳理整合、解释夹在公元前5世纪与希腊化两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之间的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真实地位,一直是古希腊通史撰述中十分棘手、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的难题。
当《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6卷于1994年问世之际,系统重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的任务正当其时。摩根·赫尔曼·汉森的划时代巨著《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制:结构、原则与意识形态》颠覆性地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的轻视态度(可能由于出版时间相隔较近的缘故——汉森著作的英文版出版于1991年,再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未能系统吸收汉森的研究成果)。后殖民主义思潮及由此引发的“东方主义”等话题的讨论为那个时代的古典学家们观察、评价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事业提供了丰富视角。承担本书写作任务的各位学者也确实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艰巨使命,并向读者们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充满创见的答卷。
从世界通史撰写与叙述的宏观视角来看,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世界古代史一直是西方中心论倾向最明显、最顽固的领域之一。除了古代中国、印度的历史文化凭借其深远影响和地理位置而占据着独立章节外,波斯帝国、帕提亚帝国、日耳曼族群、犹太人、北非地区、阿拉伯地区等元素传统上都被视为希腊罗马文明成长壮大与没落衰亡过程中的附属物。希腊罗马史乃至世界通史的作者们往往只在这些帝国、族群与区域同希腊罗马世界产生交集时,才会分配些许笔墨对它们自身历史的来龙去脉略加交代。并且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下,这些元素本身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影响希腊罗马世界——波斯帝国的兴起是为了给希腊民主制提供一个专制、野蛮、虚弱、病态的“他者”;犹太文明存在的价值是为了向罗马帝国输出基督教;日耳曼人和“上帝之鞭”阿提拉麾下的匈人的出现则是为了给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最后一击。这些目的论、神定论色彩明显的陈旧狭隘思想在西方文化界源远流长。由于对这些地中海世界的“边缘”或“外围”元首的观察与记录往往直接来自于希腊罗马作家们的现存著作,而波斯人、日耳曼人等族群对自身历史的全面叙述却因为文献散佚、缺乏史学传统等因素而付之阙如,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在近代西欧兴起后的西方古典学界被不断强化。对这种片面、狭隘、落后的历史观念进行系统批判、修正的任务固然艰巨,但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全球化时代史学研究中已成为当代古典学界不容回避的学术使命。
《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6卷的一大创举是构建了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平行并重的叙述模式。由于剑桥史各卷分工的要求,罗马以及西地中海世界在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进程被留给了第7卷第2分册(其中高卢、迦太基等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沿袭了在它们“遭遇”罗马后予以回溯的传统记述模式)。然而,第6卷的作者们并未将自己处理的题材视为一部希腊史或东地中海地区史。从目录上看,分量很重的第3章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严肃的分析(尽管由于现存史料的限制,这部分的叙述仍以波斯同希腊的外交关系为中心)。而最能体现第6卷作者们架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波斯世界区域整体史决心的则是占据全书近一半篇幅的第8-9章“地区性概论”。第8章的叙述对象为“波斯领土及其联邦”,介绍了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塞浦路斯、腓尼基、埃及等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发展状况。第9章则关注了迦太基、南意大利、凯尔特人、伊利里亚人和西北希腊人、色雷斯人与西徐亚人、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历史,甚至专辟一节讨论了地中海的交通史。本书主编刘易斯在第5章中对西西里地区史的叙述和F.G.迈尔在第8章中对公元前4世纪塞浦路斯与腓尼基历史的分析均写得有声有色,超越了此前同题材著作的视野广度和研究深度。此外,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文化、艺术与科学也正式宣告登堂入室,成为公元前5世纪文化与希腊化文化之间并不仅仅具备承上启下功能的、自身拥有独立价值的精神瑰宝。由奥斯特瓦尔德、约翰·林奇、劳埃德、波利特、阿丽森·伯福德和Y.加朗等学者合作完成的第12章(“希腊的文化与科学”)堪称迄今为止关于该主题最精彩的研究成果之一。
然而,学术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程。《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6卷的内容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不刊之论。在问世以来的20余年里,这部作品的若干缺点与可商榷之处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与直率批评,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如何书写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深入思考。笔者在通读整部译著后认为,全书最具特色、在精神上最为可贵的8-9章恰恰也是最值得加以探讨、思考如何改进的地方。它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尖锐、迫切需要得到解答的学术问题。
首先,后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从希腊罗马作家的视角出发的西方中心论叙述模式?我们从8、9两章的节目录中看到,这两章的作者们试图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系统的希腊-波斯世界区域整体史叙述模式。然而,最后定稿内容中关于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西徐亚人、博斯普鲁斯王国等部分事实上显得过于单薄,缺乏独立成节的理由;并且其中偶然闪现的个别细节也带有以希腊本土作家的关注点为中心的明显史料痕迹。可以说,《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6卷的作者们对这些区域或族群“地方史”的撰述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毋庸置疑的是,留存至今的史料只是历史本身的碎片,其分布既具有一定偶然性,又受到同时代与后世知识精英文化选择性的严重制约。尽管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来看,重视波斯、迦太基、塞浦路斯与犹太等现存史料相对丰富、并且也真正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地区确实是纠正希腊罗马中心论的可贵努力。但强行拔高史料内容贫乏、推断臆测成分较多的伊利里亚、色雷斯、西徐亚、博斯普鲁斯等地区历史的重要性,让这些在希腊中心史观中的“边缘”地区同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几乎平起平坐的处理方式是否也构成了对历史真相的另一种歪曲,并削弱了剑桥史全书内容的充实性呢?
其次,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区域整体史的叙述模式应当如何处理好史料与史观之间的关系,建立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成熟历史叙述模式?众所周知,史料本身并不是史学。历史叙述有赖于历史学家对看似混乱、零散的史料的整合与梳理,这种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的工作必然是在某种史观指导下进行的。笔者认为,在力图消除希腊中心史观影响的过程中,《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6卷的主编与作者们未能建立起一套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史观,致使“地区性概论”中的不少内容被降格为彼此孤立的各区域原始史料的罗列与堆砌。这种史料堆砌很少能够直接说明真正重要的历史问题,也很难帮助读者对地中海各地区的历史地位与相互关系形成清晰、准确的印象。构建与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可操作的整体史观,迄今仍是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们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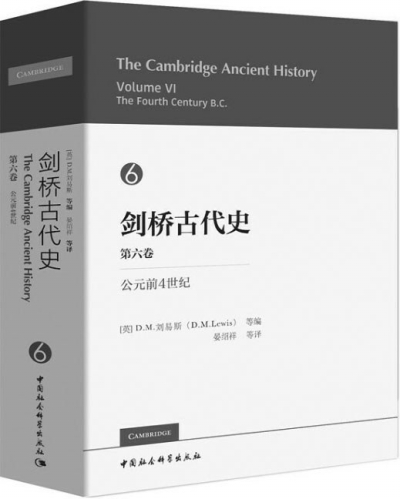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