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批人,他眺望着这个城市、守护着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同在,和它最痛苦、最脆弱的时候同在。他为这个城市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他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复苏、苏醒。
■《战“疫”书简》实际上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不屈服,纪念的是我们武汉人、我们中国人总有办法在最艰难的时刻,重新召回和确立自己的尊严。这样的一种寻找和确定,正是在从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向未来的生活当中,极为重要的力量。
没有什么历史,比书信更有在场感
中华读书报:李修文主席您好,《战“疫”书简》是一本特别的书籍,它是一部特殊时期的书信汇编,也是一部生动的生命读本。新冠疫情暴发后,您第一时间下沉到社区参与抗疫的志愿活动,百忙之中,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接受主编《战“疫”书简》的邀请?
李修文:首先,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场本该早就已经举行的分享会。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在疫情以后特别忙碌,老是在东奔西走,但是今天特别有感触。因为疫情以前,我参加的最后一场文学活动和图书活动就是在这儿(湖北省外文书店),所以今天百感交集。实际上从上一次我们来这儿到现在,每一个武汉人都知道我们到底曾经经历了什么,我们是在多么艰难的状况下没有屈服,就像我在这本书要出版之前,在封面上写的那句话,叫作“致敬从未被苦难驯服的我们”。
当时在经历了几天的封闭以后,我接到下沉社区的任务,湖北省作协要对口援助一个多达1700户人家的小区。因为没有被苦难驯服,所以我在下沉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我已经开始在重新生长。没错,我们是身处苦难之中,但是苦难与此同时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重新展开了塑造。不光是我一个人,吾道不孤,当我那时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来来去去的时候,我明明感受到那些在大街上和我一样在奔走着、货真价实地投入这场抗疫历程中的人,在他们一颗颗不屈服的、跳动的心里,是有呼喊的,他们也在呼喊当中,一次一次地重新确立自己。恰恰书信其实就是我们每一颗心灵的外放和外延。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姚磊的邀请,主编《战“疫”书简》,这也正是我想做的。
老实说我在当时很难去写作,而且每一个人当他决定去投身到抗疫这样一场斗争中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的彰显,以一种下意识的、不屈服的方式。他并没有做什么周全的美学和文学的准备,但他必须也要从他人的存在来感受自己的存在,通过他人的战斗来鼓舞我自己的战斗,通过他人的安定来说服自己的安定。如果说我们有这样一种形式,把它给扩展出去、延展出去,迅速地集结,让还深陷在这样一场苦楚当中的人们,能够感受到,在和你同在的城市里,其他人的内心里的呼喊,以及他此时何为,正在如何重新建设一个自己,我觉得书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所以在相当程度上,不是我受邀来编这样一本书,而是我也需要拿一个文人、作家的作为来投入其中,来做一些可能在当时显示不出特别重大意义的事。
中国人一直有一个传统,我们讲历史总是讲两个字叫“信史”。这个信可能是说“相信”的“信”,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书信,我们构建了一个刚刚过去的,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过去的可以让人确信的历史,我们有这样的基本责任。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叫做“以诗正史”。我们往往在李白和杜甫的诗里,才能见证到唐朝的安史之乱,甚至是国破家亡的时刻。在抗疫的过程中,那么多一直投身在这一场斗争里的一些人,那一颗颗跳动的心的外边,我想没有什么历史,比他们写出来的信更加有在场感,更加能够构成一个真实的、可触的、鼓舞人的历史。这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和起点。
用文化,连接孤岛里的每个人
中华读书报:《战“疫”书简》的编辑过程,也是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最激烈的时刻,在您参与主编《战“疫”书简》的过程中,有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李修文:我觉得没有什么“最深刻”,每一封信都让人受触动。当时我们不能够像现在一样很冷静地坐在这儿开始分享,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在编这本书的过程当中。那时我每天出门,知道当时的状况,可以说风声鹤唳,每一个人都身陷在一种巨大的不自知,或者说是一种迷茫当中。在那个时候,每个人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座孤岛。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用这样的书信去安抚人心。
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不可能像很多人一样真的有条件去投身到真实的抗疫中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挥文化的功用。比如柳棣老师,在疫情中朗读了、留下了大量的声音艺术作品;包括我的好朋友,唱《汉阳门花园》的冯翔,用他的音乐作品鼓舞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或者有这样一个下意识的直觉,只要你是武汉人、是中国人,都会对武汉生出巨大的怜爱、疼爱。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参与到这本书里的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就只能用我们所会的一点点技能,把那些可能会深陷在孤岛里头的人连接起来,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可能现在是孤单的,但是一个声音、一封书信会串联起所有的情感。
我们这本书所有的作品都制作了朗读版,大部分是湖北之声制作的,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作品,是我主动约的,比如著名主持人白燕升的作品《致敬武汉,熬过苦难成英雄》。白燕升每年要来武汉很多次,他给湖北卫视做《戏码头》这个节目,所以他对湖北有非常深的感情。好多人都不知道,他第一时间就给武汉写了一封信,自己又跑到录音棚里头录成声音作品,录完了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决定要捐50万,问是怎么个捐法。因为他不是武汉人,我就来给他找捐款的渠道,他在第一时间个人捐款了50万元。这样一批人,他眺望着这个城市、守护着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同在,和它最痛苦、最脆弱的时候同在,他为这个城市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他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复苏、苏醒。太多的人默默地参与了斗争,让我们今天恢复到了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在疫情当中,接受新闻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作“一个真实的武汉,必将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回到我们的手上”。这就是在当时发自内心的生死与共的呼喊,在这样一个链条、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里,没有哪个谁是最感动的人,哪一件事是最感人的事,只要投身其中,力所能及地动了手、跑了腿,哪怕坐在家里头什么也没有做,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没有趴下,就是为这个城市作了贡献。
今天我们的城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获得了新生,我们重新凝聚成如此团结有力的一个整体。我也觉得今天的武汉人,是新时代的武汉人,这个新时代怎么理解呢?是我们这个城市在苦难当中,和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和城市以外的人,重新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外面的人浇灌过我们、滋养过我们,我们在这种浇灌和滋养当中,也获得了一次新生,也成了一具新的身体,因此可以讲我们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新的武汉,我们也成了一个新的武汉人,所以每个人都可敬。
不衰不灭,书信永在
中华读书报:《战“疫”书简》是一部书信集。书信是一种“老旧”的文体,说它老旧,确实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再用书信来传递信息、分享故事了。我们已经很习惯用智能手机来彼此联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封封战“疫”书简的价值的?
李修文:我不认为书信就落后、老旧了。书信从来就是承载我们民族、国家文化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在过去的时代诞生了很多经典书信,几乎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基本的文化标志。比如说《与妻书》,谁读到“意映卿卿如晤”,不会潸然泪下,不会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会重新感受到被后世定义为英雄的那样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儿女情长?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脐带,书信和我们的唐诗宋词是一样的,承载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们文化的故乡和源头。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它可能不再像过去的传统书信一样具有强烈的文本感,但是书信之所以不衰不灭,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挑选,通过这本书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在读这些信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是落后的、守旧的,反而我觉得它特别及时,它写作的速度特别快,甚至比我们写一篇小说,写一篇通讯报道,写一篇散文,要更加逼近事实真相和我们每个人内心里的下意识的反应。
《战“疫”书简》中有一封信是徐东路水果湖社区的书记张颖洁写的,那是我下沉社区的时候。到社区前我首先加了张书记的微信,她也是一位80后,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图片也用美图秀秀编辑过。第二天我到社区之后,在漫天的风雪当中,看到一位女性穿着非常臃肿的大衣,正在从大卡车上往下搬给居民的菜,我就上去帮忙,搬完了之后才知道她就是我昨天加的社区书记,和我印象中是判若两人的。她也在用美图秀秀,她也在风雪中搬着菜,她也穿得极为臃肿,但是她也有一个时时刻刻向美的心,所以没有什么对立,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一切都是即时的、在场的,没有那么多下意识的精心思考和准备,就是在尽人的基本责任,尽身为一个武汉人的基本责任。所以我就问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她还是个单亲妈妈。我问那你的孩子呢,她说孩子现在都关在家里了。我说你出来之前跟你的孩子写没写过什么,她说给她的孩子在短微信上写了几百字,我们后来就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头。后来在开抗疫表彰大会前,《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还提到了她的这封信,提到了这本书里头的一句话,叫作“从未被苦难驯服过的我们”。通过这些书信,通过书信背后一个个的人,我真实地触摸到了他们、亲近了他们,与此同时又回过头来滋养了我们,浇灌了我们,鼓舞了我们。
文学的标准永远是“力量”
中华读书报:《战“疫”书简》的写信人,并不是一位,而是很多位,他们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导演、主持人等,但更多的是普通人,是在家隔离的人们,是身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受过专门文学训练的作者,您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字、他们的作品的?
李修文:文学训练并不重要,我们实际上也不是在编一本文学书,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著名的主持人和导演,我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就好像有人问我为什么老写小人物一样,我说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我了解小人物,所以灾难当前,在对于灾难的陈述和对抗当中,无论你是干什么的,你已经被打回了原形,你已经在一个人之为人的基本的尺度,甚至是在底线上,在尽人之为人的基本责任。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做什么的并不重要,你用你所会的东西,能够为人类做一点什么,能够继续捍卫你人之为人的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疫情初期我刚刚出门的那几天,在一个医院门口看到几个小伙子,就在医院门口,要往医院送不知道从哪里募集来的口罩、防护服。他们有的还是95后,但是他们聚在一起,我清晰地听到他们喊着“死了算了”,不断地举着拳头鼓舞对方。后来我慢慢地跟他们有相处有交集,有时候在别的场合碰到,还一起吃对方带来的食物。你说他们是谁,我终身都不会想起,但是那样一句“死了算了”,经常在梦里出现。我觉得太多专业的文学上的描述,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迫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它的专业性已经完全不重要了,而且这也不是我们评选的标准,用来决定哪一封信入选这本书,文学性、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入选和评定的标准,真正的标准就是一点——我们能不能从这一封信里感受到力量。
因此凡是进入到本书的66封信,都有它进入的理由,我们尤其要回到当时的现场,回到疫情的处境中再看这些信,有它巨大的价值。因为有些信是我自己约来的,是在疫情中和一些人相处之后对他的文字有了很深的理解,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人在那个时候,在巨大的未知面前,很容易想到万一我回不来了,因为大家当时对病毒没有那么了解,并不知道要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会下意识地要给家人、给孩子留一点什么话。实际上这些信很好找,随便碰到一个人打听一下,都有可能都写过一段两段的话、一段两段的文章,有的人写的可能是日记,有的人写的可能是书信。当时我几乎问到了我接触的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留了一点东西,可能半辈子也不写一点文字的人也都留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写得好不好不重要,到底什么是好?他的信哪怕鼓舞过一个人,拯救过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家人,都不是别人,我认为他已经尽到了对我们人类的最高的责任。所以我是不会从哪一封信,它写得有多好来衡量它,我就是看中它的力量。每一封都好,甚至还有好多没有能够收录进来的,都令我非常感动,都令我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真切的力量,尤其在当时是真的是可以鼓舞人心,让我们去相信隔离、相信等待,相信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对于苦难的斗争和对抗,一定会迎来一个最终的最好的结果。
因为我平常也做影视工作,我在一个影视群里求救,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叫张一白,拍过《将爱情进行到底》,拍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收到我的求救,连夜从黑龙江的五常和内蒙古的阿荣旗,买了9吨米和9吨面,然后4天4夜驱车几千公里,从这两个地方冲州过府。我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在门口等着9吨米和9吨面来的时候,快要泪如雨下。包括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到武汉要开城的那一天,汽车喇叭此起彼伏,我记得晚上在黑夜当中,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感受到了巨大的哽咽,就是这个城市里头的人,为了这个城市的正常和复苏付出了那么多。如果都事与愿违,都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的话,我们该多么冤枉,我们该有多么不值。这个不值得不是说抗争不值得,而是说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所以《战“疫”书简》里头的这些人,我一直讲他们其实就是一颗一颗在这一场抗疫斗争当中不屈服的心。这些心的力量,今天还在伴随着我们。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还是有问题的,包括武汉的经济、生活的复苏,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我相信那样的一颗一颗的心与此同时还跳动;在此时此刻,而且我们还需要这样的跳跃,带领我们去像当时打那样一场战一样,去打好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战,在重新面对未来的日常生活的历程当中,使我们变成更加有新意、更加有生命力的武汉人。
一座纪念碑,确立艰难中的尊严
中华读书报:《战“疫”书简》一发出,被它感动、因它而重新扬起信心的人很多。从疫情爆发到主编《战“疫”书简》,再到我国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今天,您觉得《战“疫”书简》对当今的读者、对经历过疫情考验的中国人民而言,还具有怎样的意义?
李修文:《战“疫”书简》实际上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不屈服,纪念的是我们武汉人、我们中国人总有办法在最艰难的时刻,重新召回和确立自己的尊严。这种尊严感首先是要以对抗苦难打底的。他有巨大的相信,相信自己,相信他人,相信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相信通过我们的对抗,一定能够在苦难里重新确立自己的尊严。而这样的一种历程,这样的一种寻找和确定,正是在从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向未来的生活当中,极为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要把纪念碑摆在那里,想起来的时候就去拜念,我们应该背负着纪念碑继续前行,让那些纪念碑所纪念的形象、情感、责任、伦理永存。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重建过自己的伦理,不能够因为苦难结束了,我们所建立的伦理和责任就分崩离析。我们要相信它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力量,就是我们应该携带那段日子,不要轻易忘记过去,要背负着一座纪念碑继续前进。
(桂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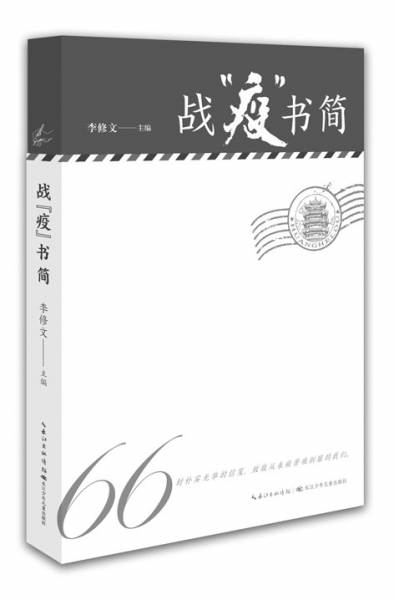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