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都采取了限制入境的政策,在某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本土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对此,众多学者开始忧心全球化进程受挫,新一轮民族主义即将上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接踵而至,等等。
人类每逢重大危机,关于血缘和归属的嗫嚅之声便会渐渐响起,仿佛一旦遭遇困厄,人们便本能般地向内聚拢,宁可相信最原始的“血与土”的逻辑,而非诉诸理性,寄望通力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民族”不再是衣食无忧的西方学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研究的某种来自近现代史或第三世界的概念。“民族主义”这个被英国大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判了死刑的词又再次如幽灵一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游荡。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民族与民族主义引发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情绪,表征倒行逆施的思想,因而与落后、战乱、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让人想起曾在贝尔法斯特、贝尔格莱德、耶路撒冷等地上演的悲剧。种种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事件并未随全球化的大潮偃旗息鼓,诸如此类的想象令人不安。不过,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加拿大学者、政治家叶礼庭(Mi⁃chaelIgnatieff)在《血缘与归属》(BloodandBelonging)一书的结尾写道:“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出在民族主义本身。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一个家,每一个这样的饥饿民族都必须得到抚慰。”他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种族民族主义,一种是公民民族主义。前者相信血的逻辑,后者相信种族、肤色、宗教和信仰不应当是归属的障碍——“这是公民的民族和种族的民族之间的战斗。”
一
《民族》一书动笔时,适逢苏格兰公投、英国脱欧,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讨论不绝于耳。就像书中前言所言:“查阅、思考和写作的一切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不断交叉并轨,它们与真实世界相互映照、若合符节,纸页上或电脑上的文字似乎不再无所附依。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西方世界正在发生某些影响深远的变化。2015年至今,以英国脱欧为序幕,欧洲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特朗普主义崛起,白人至上论甚嚣尘上,新纳粹分子粉墨登场。”
为了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相关度,本书以卡罗尔·安·达菲(CarolAnnDuffy)的一首诗开始,探讨苏格兰与英格兰在历史上的民族纠葛,指出诗中出现的河流、花朵等都被建构为某种象征物,吸纳进民族话语之中。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很少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通往某种更深广的意义,与某一地域、某一人群的生活方式密切相连,在某些情况下自然指向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这让我想起英国18世纪大画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Hog⁃arth)一幅名为《加莱之门》(TheGateofCalais),或称《哦,旧英格兰的烤牛肉》(OtheRoastBeefofOldEngland)的画。
这幅画构图简单,形象鲜明。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个屠夫的帮工,他扛着一扇牛肉经过城门,旁边站着一位垂涎三尺的教士。仅从画面看,这幅画是英国人对天主教的讽刺。他们一边号召信徒清心寡欲,坚定地过信仰生活——有点类似于“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一边又自甘堕落,连一块“路人甲”的牛肉都能引起巴甫洛夫反应。这种反讽当然是题中之意。过去在中世纪绘画中永远占据中心的象征精神、信仰与救赎的耶稣的肉身,在这里却被一块牛肉取而代之。简言之,这幅画表现了灵与肉的对比。这和《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不怀好意地让虔诚的Conmee神父观看肉铺的猪肉是一个道理。
不过,这幅画的寓意远不止这些。熟悉英国历史的人一定都会注意到加莱这个地名。历史上,加莱曾一度归属于英国,它的历史遭遇与英法力量的此消彼长密切关联,并因此被纳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想象之中。荷加斯虽赫赫大名,但以加莱为题的最著名的艺术作品并非他的这幅画,而是法国雕塑家罗丹(AugusteRodin)的《加莱义民》(TheBurghersofCalais)。这件群雕作品创作于19世纪末,表现的是六
个英勇赴义的加莱市民。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围陷加莱,市民缺衣少粮,危在旦夕。经过谈判,英王爱德华三世提出:加莱市选出六个市民代表任由英国人羞辱、处死,以此换取全城的安全。如今,雕像仍伫立在加莱市政厅前,象征着英勇无畏的法兰西民族。
如果说罗丹的雕像以直白显豁的方式表现了法国的民族主义,那么荷加斯的画则采取了一种相对隐晦的方式。加之历史的缘故,画的意义更加隐匿难辨。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幅写实主义的画往往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我们可以透过荷加斯所提供的来自那个社会的种种局部细节,看到其整体。这个整体既包括社会风情,还包括国民心理。如果失去了这层意义,这幅画就变成了一幅纯粹的风情画,其意义也变得贫瘠了。
二
它表现的主题实际上是英法饮食的对比——没错,尽管现在法国人成功实现逆袭,法国美食几乎代表了世界烹饪的最高水准,但是在
荷加斯的时代,法国饮食却是英国人讥诮嘲讽的对象。在那时,法国饮食寡淡无味,缺少油水。在法国治下,加莱人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而教士等权贵阶层却脑满肠肥。借此,荷加斯传达了基于英格兰物质条件优越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的不仅是法国人,还有苏格兰人。在这幅画的右下角,一个支持斯图亚特王朝、流亡欧洲大陆的苏格兰人惨兮兮地躺在地上,似乎命不久矣。对于这幅画,肯尼思·本迪纳(KennthBendiner)在《绘画中的食物》(FoodinPainting)中指出,荷加斯的画表现的是英国人对欧陆吃食的鄙弃之意,反应了当时普遍的民族情绪。在这幅画中,食物和爱国密不可分,“营养学与民族主义走在了一起”。
对于英国人吃得好这一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也颇为自豪。在对英国历史的叙述中。他不惜笔墨,凸显(炫耀)了英国人吃的历史。如果荷加斯的画反映的是18世纪的状况,那么麦克法兰则将这种优越感追溯到了16世纪,由此再现了深植于英国民族意识中的“营养化”传统。他的论述逻辑清晰明了:吃得好说明经济景气,发展超前;吃得好才会有好体格,才能更好地建设民族国家。他分别引用了当时来英的法国人、德国人以及荷兰人的话来描述16世纪的英国食物:“和法国的同等人相比,英格兰居民消费面包较少,消费肉食更多,而且喜欢‘在饮料中加很多糖’”;“英格兰劳工比法国劳工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却工作得更轻松”;“……英格兰农人的工资更高,饮食更丰,因此更有力气和积极性完成自己的工作”。这种对于食物的观察、描述与评论沾染了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一本出版于1559年的书中,一位旅欧的英国人细致比较了欧洲各国的饮食标准。法国人“嶙峋骨瘦”,“从不曾鬻一物于市,倘有鬻出,所得者近半数须缴税纳赋。虽不食猪鹅鸡禽,然须为此纳贡,以备万一购用之”。此类居高临下的,掺杂了鄙弃与怜悯之意的描述并不仅仅针对法国。“意大利亦不甚佳,彼国农人所谓富裕,不过以麻衣为华服,以皮肉为长绔而已;饮食所费无
几,因其赶集之时,无非左手持鸡禽一二,右手持鸡蛋一兜数枚,鬻出货物、收得银钱之后,再无力购买牛羊鱼肉……其携归之物不过一夸特食油,用以调制野菜沙拉,维持一周食用。”对于德国,他则写道:“虽比别国略佳,然其国民食用根块多于食用肉类。”总而言之,只有英国人吃得营养均衡。为此,他大发了一番议论,告诫国民:“推己及人,汝当自知幸甚。彼等啖野草,汝等食牛羊。彼等啖根块,汝等得享黄油、奶酪及禽蛋。彼等饮普通白水,汝等畅饮上好麦芽酒或啤酒。彼等携沙拉归于市,汝等囊中满载精美肉食。彼等何尝得见海鲜,汝等尽可以大快朵颐。横征暴敛令彼等羸瘦如柴,汝等尽可以为儿孙后代积蓄存储。汝等奉召报国,一生仅三四次,况有军饷津贴;彼等日日纳税,无止弗休。汝之一生如同贵胄,彼之一生犹若彘犬。”
在他看来,“天堂为英格兰是也。”也难怪这本书的书名是《忠实臣民之安全港》(AnHarboroweforFaithfullandTreweSubjectes)。麦克法兰专门指出,作者为这段文字加了条旁注:“上帝乃英格兰人。”他认
为,这本书说明了“在16世纪中叶将英格兰和欧洲其余地区做一番比较,可以立现生活水平、国民自由程度和社会流动性方面的根本差别”。换言之,一部英国史,就是一部吃得好、营养化的历史。对于食物的评判指向了更深层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英国人丰富的饮食说明了英国当时整个社会超前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能力。从上述引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英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由此产生的种种情绪增进了英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同仇敌忾的意识。种种迹象都指向了这一点。《民族》一书的引言部分便分析了16世纪以来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简述了这一过程如何体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如果从当下的角度来看,未免觉得有些反讽。众所周知,英国向来被讥为美食的荒原(不管这一偏见是否站得住脚),而法国则以考究的餐食著称,法餐甚至被上升为“美食”的代名词。这种反差强烈的对比说明:标识一个族群的特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正是霍布斯鲍姆主编的《传统的发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一书关注的主题。《民族》一书谈论传统、怀旧的章节多次引用了这本书中的观点,包括以下这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
我们不应被一个奇怪但又可以理解的悖论所误导:现代民族和它们的所有障碍一般都宣称自己是与新相对的,是植根于最遥远的古代而与建构相对的,是如此“自然的”人类共同体,以至无需任何界定和自我断言。无论现代概念中的“法国”与“法国人”中包含有怎样的历史性或是其他连续性——这是没有人想否认的,这些概念本身必须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
三
日常语言中有哪些看似自然而然的事物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使用“爱尔兰性”“苏格兰性”“犹太性”一类词时,要予以怎样的审慎?这其中有多少本质化的嫌疑?所谓的“国民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如何既施以理性的批判,又报以“理解之同情”。这样的思考让我
们重新审视那些习焉不察的词。
2014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在利比里亚待过一段时间,当时该国刚刚结束战乱,多国维和部队尚未撤离,因此整个国家像是一个微型联合国,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当地的民众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我们常被问及一个问题:“Liberiahas 16tribes. HowmanytribesdoesChinahave?”显然,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当地普通民众的词汇里,nation、ethnicity之类的词是缺失的;而在中文中,“部族”之类的词虽然存在,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很难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部族”属于某种原始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我们的“民族”相去甚远。对于这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语言表达实际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一些部族的方言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普及不彻底等客观原因,很多民众并未掌握英语这门语言,他们无法理解一些词汇。对于这些利比里亚人而言,他们处于一种失语与发声之间的状态,这自然造成了一种“洋泾浜”化的现象。在现代民族的建构中,语言问题至关重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霍布斯鲍姆等都对此作了详尽的探讨,《民族》一书也有两个小节专门谈论了这一问题。在这里,利比里亚的语言现象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当我们谈论民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民族、部族、族群这些词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中会勾起不同的想象和情感。这一发现起到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让我更直观地看到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如何因脱离语境而变得面目全非。“民族”这一习焉不察的词或许并非大多数人认知中一个始终存在,指意明确、稳定的词。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民族”,尤其是“民族主义”是一个被诋毁的词,属于未开蒙的世界,代表某种落后和反动。叶礼庭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此生中一直居住在餍足的民族国家,在这里没有严重的边界争端,不再被外国人或压迫者统治,做我们自己房子的主人。餍足的民族有资本去做世界主义者,餍足的民族可以承担向饥饿民族的激情屈尊俯就的奢侈。”对于不同立场的人们,“民族”一词将继续激发不同的反应。民族认同是建构甚至是虚构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存在,或者将其打上“虚假意识”的标签。它至少是一种有意义的虚构,能够构筑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有助于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民族》一书中也写道:“民族认同并不是一种本质上虚假的想象,而是有着强大的实质性的力量。”如史密斯所说:“这使得民族既成为情感和意志的群体,也成为想象和认识的群体。”
四
人们通过包括食物在内的事物来表达民族主义的情绪。这种“食物民族主义”并未随着英国烹饪在全世界饱受讥讽而消失,反而以另一幅面孔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去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唐顿庄园〉与英国童话的背后》的文章,从电影中的食物叙事与奥威尔等作家对英国食物的书写角度探讨了脱欧后的英国民族主义。文中写道:
奥威尔慨叹“现在很难找到能吃一顿英国风味的地道好菜的饭馆了”,也不讳言“不是自然法规定英国的饭馆家家都必须是外国的,否则就糟糕。改进的第一步将是英国公众自己不再采取那种长期忍让的态度。”面对外国菜的入侵,英国人应该雄起,至少首先在精神上采取攻势。英国菜为英国专属,是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本土、地道的英国味儿,借用奥威尔之言,“它们是我们的特产”,好吃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乃至政治寓意。
以吃谈英国之独特性,并由此勾连文化认同,指向民族自豪感的做法显然早在荷加斯那里就已存在。这种以饮食标识民族认同的传
统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它亦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让一个民族抱残守缺,难以进取。鲁迅先生曾以食物取譬写道:“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越是积贫积弱,越是强调国粹,强调专有的属性,对外来事物保持警惕,排外而封闭。这正是鲁迅所说的:“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这不禁让人想起当下的英美:以往日鼎盛时期的荣耀来补偿今日的失落与匮乏。
《民族》第四章探讨爱尔兰的民族问题时提到:“关于民族的一切总是及物的,总会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场景与自然景观之中。”现在看来,我们也可以用食物等日常的存在来探索这个问题。文学艺术对于某一事物的再现,可能因标识了特定的生活方式或地方风物而成为一种关于民族的修辞。也即是说,“民族”具化为某一人群的生活方式,食物自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尤利西斯》中,布鲁姆最爱吃带尿骚味的烤猪腰子,这在个体层面似乎表征了他极其接地气儿的性格,与斯蒂芬高高在上的精神性形成了对比。而在集体层面,这一偏好则另有深意。书中有一段关于他到另一个犹太人开的肉铺买猪腰子的描述,这里面有很多反讽。表面上看,考虑到犹太人的身份,卖肉的与买肉的似乎都有违常理——对于犹太民族而言,猪肉是被禁止的。大啖猪腰子的布鲁姆显然比售卖猪肉的肉贩又激进了一步。乔伊斯就是要塑造这么一个在各个方面打破禁忌的人物,可以说是以此做了一个实验:将一个人所谓的民族属性剥离之后,能得到什么?因此,我们读到了小酒馆里的一段经典对话:
“民族?”布卢姆说,“民族指的就是同一批人住在同一个地方。”
“天哪,那么,”内德笑道,“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是一个民族了。因为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这样,大家当然嘲笑了布卢姆一通。他试图摆脱困境,就说:
“另外也指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我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乔说。“请问你是哪个民族的?”“市民”问。
“爱尔兰,”布卢姆说,“我是生在这儿的。爱尔兰。”
“市民”什么也没说,只从喉咙里清出一口痰;而且,好家伙,嗖的一下吐到屋角去的竟是一只红沙洲餐厅的牡蛎。
从猪腰子到牡蛎,食物被卷入到乔伊斯关于何谓民族的思考之中。吃腰子的布鲁姆和粗俗不堪地吐出牡蛎状浓痰的“市民”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于民族的理解。一种是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另一种则是偏狭的种族民族主义。通过对两者的描述,乔伊斯旗帜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立场,并为民族想象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五
如果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又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如何构建一种包容性的共同体,一种不以文化属性、血缘关系定义的共存的方式?众多文学家、思想家关于共同体的思考都在围绕这几点进行。《民族》的理论概述部分便尽力再现了各个领域之中围绕这一主题的讨论。这也是书的前言部分所说明的方法论:“既按图索骥地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中发掘梳理了关于民族的讨论,又有一定的旁逸斜出,探索了民族主题在哲学思想、文化历史、文学批评等相关领域的辐射与延伸……”通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对民族的专门研究多是社会学领域的书籍,这类著作自然秉持的是价值无涉的理路,将民族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加以条分缕析。也即是说,它们
所提供的洞见基本上属于理性、冷静的观察、揭露与剖析,尽量将民族从情感认同中剥离出来。这是一种冷冰冰的处理方式,而文学中的民族书写或民族构建却恰恰是带有温度的。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我想要实现的写作目标:“在以民族为视角的文学阅读与批评之中,我们显然要综合这两种看似矛盾对立的态度:一方面要审慎冷静地辨识文学想象之中狂热、危险、排外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又要对真实的民族认同,特别是弱小民族坚定的民族情感和反抗精神予以理解。这种阅读与批评既关涉不偏不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判断,又关涉纷繁交织的审美、诗学和情感的评定。”
上述平衡的、对位的方式也暗示了《民族》开放的结构,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不偏不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寻绎的过程。“面对各类抽象的思想资源和种种具体的文学文本,本书试图以民族与文学的关系为线索来编织一张经纬分明的渔网,以在浩瀚如海的著述与言论中捕捞吉光片羽。”自然,这种捕捞难免有所疏漏,它只能“呈现一幅导引性的蓝图,为更为深广的研究抛砖引玉”。它试图为以民族的角度阅读与思考文学标示种种出口,指向不同的可能性。如果允许的话,我当然想进一步对本书加以补缀。譬如,《民族》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梁启超、鲁迅和林纾三大人物谈外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主题,这部分现在看来写得有些仓促、简略,当时是为了尽快进入主题,而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另辟一个章节,甚至好几个章节,从民族的角度谈近代以来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再者,以民族的视角阅读文学又何尝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研究的一种修正?由此,可以更多地转向弱小民族的文学创作,转向群体、公共的维度,更多地考察文学与社会、民众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囿于学院的象牙塔之中。关于文学研究的功用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都会遭遇这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来到这个十字街头。对此,《民族》一书尚有未发之覆。还是以鲁迅先生为例:他译介、讨论了那么多冷僻的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甚至引起同时代人的误解,深意何在?如果将他的“小民族”思想和卡夫卡关于“小民族”的思考进行比较,也非常有意义。《民族》第三章主要是谈卡夫卡,特别是德勒兹与卡萨诺瓦视域中的卡夫卡的“小民族”思想:一个是哲学化的,上升到了生存论的高度;一个则是具体化的,落实到了历史中。书中对上述话题只是一笔带过,现在看来可以继续展开。
《民族》引用了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ndDarwish,1941—2008)的诗歌来说明巴勒斯坦的民族困境。这里引用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Amichai)的诗句作为一种补充——这种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正是一生对巴勒斯坦的民族事业孜孜不倦的萨义德所秉持的方法。阿米亥写道:
我们是阳性也是阴性,是复数也是单数,
一边吃着烤杏仁,一边啜饮着阿拉伯茶,
两种本不相识的滋味,在口中糅合一处。
阿拉伯茶和烤杏仁两种口味的融合隐喻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解构了对于民族认同的本质主义的观点。诗人以这种和合共通的状态譬喻巴以之间可能的未来。纪录片《风味人间》以一种相似的口感、味道、食材、烹调方式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串联起来,其实也说明了这种“殊域同嗜”的现象。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群体之间,对美味的共同追求或许可以成为沟通的路径。袁子才在《随园食单》的序中写道:“吾虽不能强天下之口与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这也是食物民族主义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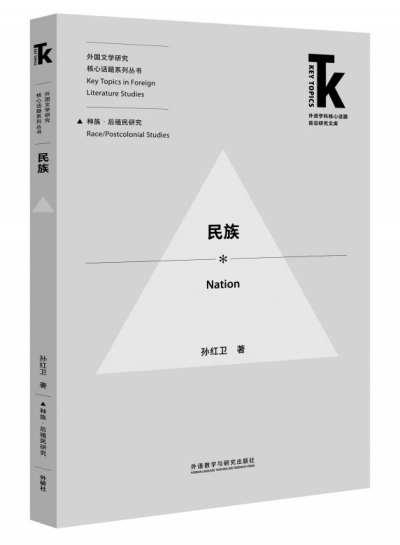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