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道体学引论》的出版似吹皱一池春水,给学界造成很大的冲击,其余波漾及中哲史外更广大的文史学科。不过,此间自来的传统是视文史哲为一体,而这三者在根底处确实面对相同的问题,做着殊途同归的探索,所以,本书能引动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自己产生一探究竟的冲动,殊属自然。
粗粗看过全书,感觉它大体以贯通性的阐释论证为基本方法,以“生生”这个第一性问题为中心,通过对《易》《庸》《庄》这些道体学经典的疏解,提出并论证道体的大意,即所谓“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同时通过确立“太一”为其中最高的主题,由努力统合宋明心、理、气诸宗,超越前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种种纷争。进而,对道学与西学各自的问题传统与义理传统的关系,作出初步的论定。书中除了见出作者扎实的西学功夫外,更多可见牟宗三和熊十力的影响。但饶是如此,它仍有自己的判断和发明,如在牟氏“四因说”基础上增益出“即虚静”即如此。这些判断与发明散见于全书各处,以致让人虽感不易看入,终究欲罢不能。
想特别指出的是,这本书无意宣示一种论证甚至主张的完成。相反,它像一个有意味的空框,以较为自由舒张的结构,向多种可能与质疑敞开。个人正是由此感觉到作者除了自信,还有难得的诚悃,并进而觉得,即使本书没有提供现成的结论,而只是专注于讨论,仍较时下那些颇有小慧、了无根底的肤浅之作要好许多。后者常常没读几本书,更不懂得思考,就敢挟几个舶来的新名词,宣布真理在我,真是轻率! 还想指出的是,学问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并应该这样做的。盖所谓学问,其实就是学加上问。学由勤得,问从思出,此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我还想更进言之,以为其义不仅仅限于勤学加好问,毋宁说就是要人学会问。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能提出问题的人比能解决问题的人要重要得多。解决问题有时候需守先待后,提出问题者是但开风气,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恰恰最缺开风气者。很高兴作者是有这个意识的,更何况许多问题由他提出来,未来未必不能由他自己来解决,他是完全有可能把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好的。当然,看本书对此问题的初步论述已有33万字,有点替他担心,接着要怎么写下去呢? 但我相信,作者将来的工作肯定会更加细致深入,更加有说服力。记得梁任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结果收拢不住,字数与规模几乎赶上原著,只得另成一书,单独出版,是为《清代学术概论》。梁任公为学生作的引论犹精彩如此,作者为自己的宏论有此铺垫,未来自然大大可期。
至于面对本书特殊的写法,以及许多人看不懂,我的感觉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自己,让自己能体认学术研究本就该指向一个更宏大超迈的境界,有不知道归路在何方的更决绝一些的出发。前者可以提升学问的准入门槛,让一切浮光掠影的浅学之辈不能随随便便以国学大师自居。说起来,现在的大师太多,鱼龙混杂,有的穿一件中装就敢端大师的架子,摆专家的谱了,这病得治。后者可以接引后来无穷的可能,从观念的阐发到文字的表达,以求得更多尖锐的质疑与指正及更多高明的增补与完善。当然,也包括来自作者自己的提升与发展。总之,为这样的自己没结论与别人看不懂,我要向作者表示敬意。他不愿匍匐在前人的陈说下,而是自立权衡,自出手眼,以“接续旧学,接引西学,广立一本”岸然自命,这是一种自信,更是难得的勇敢。此前,我读到过他的访谈,对他从来要求自己“读超一流的书,想最大的问题”很是佩服,觉得提气;又对他说倘不能思考古今中西大本大源的问题,只能成就学者而不能成就思想者,也非常同意。什么是“最大的问题”,何谓“大本大源”? 无非是要人摒弃世俗化的鸡零狗碎和学院化的功利算计,进而从现世与浮生的庸碌匆忙中超拔出来,抬头看天,在实践层面上能关心整个人类的精神出路,在义理层面上能探究符合主体创造热情与终极追求的真理。
当然,因为多原创性探索,本书有些论述难免不够周延,逻辑的衔接也间存罅隙。最直接的感觉是,书中常有出幽入冥的观察与直凑单微的判断,但有时难免忽视了例外,遗落了完整。仅就“道体”一词而言,诚如作者所说,自程朱以下,儒门古籍中多有之。由此展开的论述,则不仅限于儒学,更不限于理学或心学。但实际是,书中对别家别派道体论的关注是不够的。如唐通玄先生著有《道体论》一卷,《崇文总目》与《通志·艺文略》均有著录,作者本“道体本寂,始终常无”之旨,在《论老子道经》《问道论》《道体义》三篇中,以自设问答的形式,对道体的本意作了充分精详的论述。既认为“道体广周,义无不在,无不在故,则妙绝形名,体周万物”,又指出道之与物“常同常异”,“物以道为体,道还以物为体”,“就物差而辨,道物常异;就体实而言,物即是道”,故万物与道是二位一体、即一不二的关系,由此分别就“义用”所立之名,更注重据“体实”而彰之称。在此基础上,再本着“道始虽一,终有万数”的认识,讨论道体与教化、是非、现象、修持等关系,以“兼忘二边,双泯有无”为悟得道体的终极玄旨。这些与本书讨论的问题不仅相同,着眼点与展开方式也相近甚至一致,可以说是不能绕过和无视的道体学原典。但遗憾,书中无一处论及之,书后参考文献也不见其踪影,更不要说援用为讨论的佐助与参考了。此书后来被收入《正统道藏》太玄部。我想问的其实是,除了本书重点论及的《庄子》外,传统道体论的展开能与道教无关吗?进而,“道体”与自《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一直到《洞玄灵宝相连度劫期经》所讲的“道性”又是什么关系?
再如,宋人释元照为唐道宣《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作注,著《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卷,里面特别讲到了道体,以为“言道体者,道无别体,即本净心”。作为律宗中兴时期的大师,他不满“见学律者以为小乘,见持戒者斥为执相”的当世“偏学”,力主专志奉持净戒,以为入道以观心为主,往生以观佛为要,主张“归心净土,决誓往生”,故将“净心”统一于所主的律、教、禅三者当中,告诫人非学无以自明、自辨与自悟。他留存于今世的诗,也常阐发同样的道理,道说的是自己“静爱山头云”(《白云庵》)、“百计坦平心地静”(《咏宁国院》)的志向和情趣。其说在当时及后世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苏轼就凛遵其教诲。本书后来收录于《续藏经》。联系释延寿《宗镜录》所谓“夫修道之体,自识常身,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我再想问,道体的问题与佛教有没有关系? 考虑到佛教有般若一支,其重视体证本体,从来主张神与道合,道体说也与气本原说一起,对佛教本体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汉唐以降,受黄老思想和庄子的影响,自牟子《理惑论》和孙绰《喻道论》以下,佛教于道一途多有论述,如《本际经》就以“无相”之“道体”作为万物滋生的始基,那么,讨论道体显然不能缺少佛学这个维度。而有鉴于佛教心性论对道教道体论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以后两者更多交互,彼此渗透,其间的种种是否更有待作进一步的厘请?
又如,本书对儒门古籍中的相关讨论也有遗漏,譬如没能注意到明人王廷相的《雅述》就是一显例。王氏以“元气”为天地万物之“总统”,太极与太虚皆气。故反对程朱“有理而后有气”的理本论,以及陆王“万事万物皆出于心”的心本论,而力主气本论。用今天的说法,颇具唯物色彩。《雅述》首篇即《道体篇》,开宗明义讲“道体不可言无”,“不可以为象”,“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气者造化之本,有浑浑者,有生生者,皆道之体也。生则有灭,故有始有终,浑然者充塞宇宙,无迹无轨。不见其始,安知其终。世儒止知气化,而不只气本,皆于道远”。在他看来,“气本”与“气化”皆是道之体,其中“浑浑”即元气与“生生”即生气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其他诸篇于此义也间有发明,如《五行篇》所谓“有元气则生,有生则道显。故气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气之具也。以道能生气者,虚实颠越,老庄之谬谈也。儒者袭其故智而不察,非昏罔则固蔽,乌足以识道”。总之是认定“离气无道,离造化无道,离性情无道”。由于其思想一贯,论析清晰,很受中哲史研究者的推重,以致引来域外汉学家的关注,日人松川健二著有《王廷相的思想》,德国汉学家Wolfgang Ommerborn和Michael Leibold也有《徒手世界:王廷相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王廷相的实用主义儒学》等专著。这里我想问的是,道体论是不是仅在理学、心学的范围内就可以解说清楚? 它与儒门中唯物一派又是什么关系?
综合上述所说,在儒释道三家里面,道体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其同异交互究竟体现出什么特点,《引论》都没有涉及。我相信这些部分,许多应属作者的考虑范围,只是未及展开;有的一时没想清楚,以后应会引入。如果是前者,请告诉我们具体的内容;如果是后者,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将它们完满地实现出来。
最后再说说包括文体在内的其他枝节问题。我们说,哲学是人类经验最完整最深刻的追究和展开。可再怎么完整深刻,它终究基于人类的经验,所以还应该让更多的人看懂才好,不仅包括各种专业的学人,甚至包括普通人。我在想,如果连我们好问学的人都无法把问题说清楚,总和自己没有想清楚有关系。当我们真的把一个问题彻底想清楚了,一定是找得到说清楚的方法的。是谓深入浅出。当然,这是一个高境界。至于选用什么样的语体不是问题,用文言可以,半文半白也行。在这方面,民国诸前辈做得就很好,像钱穆、劳思光等先生,学问各家评说不同,但其用语雅驯是人所公认的。本书在这方面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盖中国人致思忌落实,议论尚灵透,不着意追求指谓与判断的分明,也不太讲究逻辑边际的周延。究其初心,是因为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基于封始而道亡的认识,他们进而认为既然事物是处在关系与联系中的,就不宜别处,要当通观,所以喜欢采用“不释之释”的策略,并努力促使言近意远、词约旨丰的高上境界的实现。宋人论心性理气等问题尤其如此,如朱熹集注《论语》,就认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以后于《语类》中,又强调“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故他们的议论与西人的逻辑周延、指谓分明不同,他们创设和沿用的名言,也远非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或“概念上的纯净体”,而呈现出一种更阔大圆融的气象。但今人看来,意旨不免有些浑涵,理路不免显得有些淆乱。凡此,都需要研究者特别小心,作认真的梳理和诠解。又需要基于真的解会,作恰如其分的意义开显与转换。但本书解释道体,这么重要的问题,其选用的表达方式仍是“据三演二,义理之分也;三即一贯,道体之全也”,这恐怕不是将道体说清楚的最好的攻略。以后,作者又提出“一统三宗”说,化用自柳宗元的“合焉者三,一以统同”,但注释只列出《柳宗元集》,既不出卷数,也不出《天对》这一篇名,更关键的是,柳氏此说的本义在说明“阴”“阳”“元气”三者合而生物,皆统一于“元气”,它与本书所认知和主张的语境是否一致,也全无说明,这不能不说是欠斟酌的。至于《柳宗元集》用的是1979年的旧本,而不采用更详尽权威的新校注本,也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够与时俱进。
本书还有一些地方也显得有些随意,比如上篇有小结,下面没有。有的章节有结语,有的则没有。这些问题或起因于单篇合成的缘故,但完全可以处理得更好一点。总之,是希望这样一些缺失不在本书作者身上出现为好。因为道体研究的将来,正期待他作出更精彩的贡献。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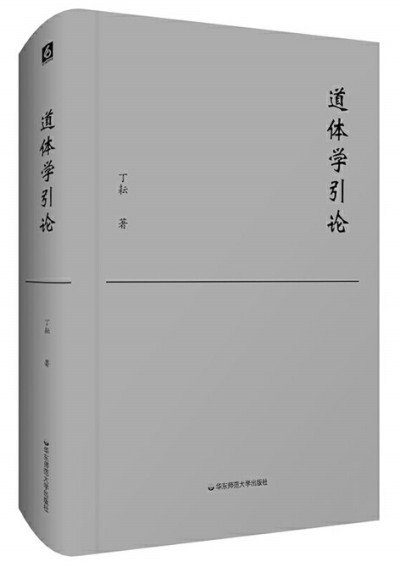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