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是一位具有宏阔学术视野和透辟学术眼光的通人。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本土学术问题考察和研究的同时,他将视野时时投向海外,通过广泛的跨域对话,深度参与最前沿的学术争鸣,别求新声于异域,诚望杰构于来者,进而生发出新知,碰撞出火花。由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一书,就是他这一长期努力的展现。
诚如葛兆光先生多次引用歌德的名言所强调的,“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晚近以降,“中国问题”不再简单。这里的中国问题,也许是古人不曾思索过的,也许是古人思索过而无从解答的,却是近代以至今天的中国人所必须直面和回答的。在撰写完成三卷本《中国思想史》后,先生在后记中写到:
我们面对的世界太复杂,个人经验都并不能够圆满解释一切,现在的人已经不像古代中国的哲人那样可以执一御万了,因为那个时候,人也简单,心也简单,每个人都充满了完整解释世界的信心。可是,现在我们向前看的未来和我们回头看的历史,似乎都太幽深暗昧。这种幽深暗昧是一种不确定性,它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也始终提醒我们不要太轻率的自信。
正是有见于这种幽深暗昧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葛兆光先生不断地开拓研究的新视野:从周边看中国、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理解中国、从异域之眼中发现中国。文献的版图不断延伸、学术的对话场不断扩大、学科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一种强烈的通人意识贯穿于先生大多数的论述之中。《侧看成峰》正鲜明体现了这一点。
从第一篇对卜正民主编的“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中译本的评述开始,葛兆光先生首先揭橥其一贯秉承的“站在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延长线上”的四个研究角度,即“时间缩短、空间扩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这也奠定了整本书全部论述的基调。正是沿着这条延长线,很多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很多很成问题的问题不成问题,并且进而,很多文献资源重新进入了学术视野,各研究领域的学科畛域被模糊化并趋近于消弭,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外交史甚至艺术史、图像史等等,都可以而且应该熔为一炉,于是,问题被高度复杂、同时也被高度充实了。《帝制中国史》和许倬云的华夏论述考察了“中国”这一概念和实体的动态发展过程,于是,本来似乎不是问题的“谁是中国”的问题成了问题,是乃为“问题复杂”。而这种“问题复杂”显然具有更高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体现在:一切为揭示复杂的历史场景和思想世界的复杂样态而服务。于是我们看到,原本游离于传统阐释场域之外的所谓“边缘文献”,被赋予了独立而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寒冷气候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卜正民所写的《元明》一卷,却用“小冰川时代”这一因素,贯串了整个13世纪至16世纪的中国历史。尽管这套通史中所谓“小冰川时期”与竺可桢的说法有些差异,元明部分关于“小冰川时代”(13世纪到15世纪)与宋代部分对于“小冰川时代”(10世纪末到12世纪)界定也有些冲突,有的证据(如用明代绘画中的《雪景图》证明气候变化)也多少有些疑问,但是,把这一点真正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并作为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确实是令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历史都变得复杂化了。
一种全新的却是鲜活的中国史的考察和写作范式从一开始便呈现在读者眼前。
《置思想史于政治史背景中》纵论《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典范意义:从《传灯录》《道命录》《学案》到晚近以来受西方哲学史及斗争哲学理念影响的一系列思想史著作,大都深受宋人建构的道学谱系的影响,从而,丰满的历史躯体弱化为骨感的概念修辞,复杂鲜活的历史现场简化成黑白分明的路线斗争。对此,葛兆光先生在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文中有一妙喻:
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里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
思想史在主题凸出或框架优先的写作模式下,变得干净、纯粹却贫血。于是葛兆光先生追问:是遵从和将就那个来自西洋哲学的概念工具“哲学”来“脉络化”宋代思想,还是应该根据历史和文献“去脉络化”,重新写一个宋代思想史?这是一个事关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大问题。因此,寻绎系谱的生成,进而“去系谱化”,再依赖更充分的来自历史现场的文献依据和多元的观察视角“重建系谱”,就成了摆在当代研究者面前的使命。《朱熹的历史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树立了典范意义。于是,作者在结语中问道:如何建构贯通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史的“新思想史”?
正是出于对长久以来单一角度审查思想世界写作路数的反动,葛兆光先生对建构新的论述框架的努力总是赞赏多于质疑。如对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从文学史角度出发考察思想世界即是如此。
在对传统中国及四裔关系问题的考察上,如夫马进的东亚外交史研究、吉开将人的苗族史研究、约瑟夫·洛克的云南纳西族研究,不管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论述理路上,都印证了葛兆光先生“空间扩大”“文献增多”的理论。文化史是最接近复杂历史现场的书写领域,也是最需要“打通”意识的写作领域,葛兆光先生在阅读《法国文化史》后撰写的笔记,及对常盘大定等的中国文化史迹考察的述评中,提出了文化史与思想史互即互入的观点。附录中的读书笔记及史料解读同样是精彩的、充满问题意识的,展现了葛兆光先生自由游弋于东西洋文献的能力和左右采获、触类旁通的余暇和快乐。
读完本书,如果说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的话,那么,“强烈的预流意识”“清晰的求真意识”“自觉的通人意识”无疑是应被注意到的三点。这三种意识统一于葛兆光先生的评论文字之中,而最终归结于“通人之学”。
因为强烈的预流意识,所以对海外的汉学研究始终报以热烈的观照,施以敏锐的观察,加以热诚的绍介,当然,也不乏冷静的质疑和批评。因为清晰的求真意识,故就治学之体言,须首先承认问题之复杂(不受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古已有之的或舶来的框架影响),就治学之用言,欲解决此复杂之问题,则不妨亦理应广泛运用各类研究方法、占有更多的史料文献,在更广大的空间上考察问题。先生一贯标举的“本无畛域”“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正为此下一注脚。又因为自觉的通人意识,才能超迈于各类既定的研究框架之上,将各种主观上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解除,以一种“举头天外望”的学术魄力和“活泼泼”的学术生命的活力,重新确立主轴和路标、边界和轮廓。在这个人文科学讳言“打通”,沉稳以至于沉闷的朴学风气劘切一世、通人之学似乎夐焉绝响的时代,人文科学更需要深沉、温情的学术关怀,更需要目光锐利,足以照映一世的学术眼光,更需要关注大历史、提出大判断、解决大问题的气魄和勇气。葛兆光先生,显然是一位真正的通人,其学亦堪称通人之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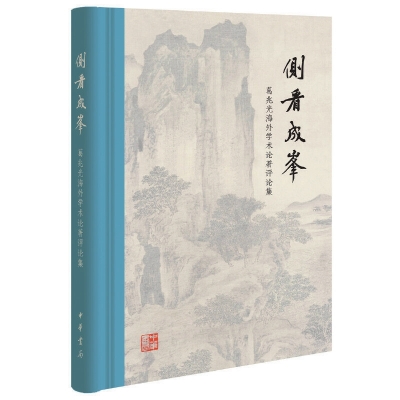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