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时,绝大部分教科书这样描述两者关系:基础研究成果是整个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对应用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起指导作用。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基础科学是应用技术之父。在我们熟悉的语境中,这个结论经常作为无需论证的知识被广泛传播和灌输。然而Science杂志前资深科学新闻记者格林伯格在《纯科学的政治》一书中,描述了另一幅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关系的图景。
基础科学从头补习“政治课”
对大部分读者来说,《纯科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Pure Science)这样的书名几近学术黑话,所以格林伯格需要在书前序言中专门做界定:“纯科学”指的就是基础科学,以示和“非纯科学”,既应用科学和技术相区分。
格林伯格这样解释:科学政治本质上与其他政治并没有什么不同,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基础大科学工程,预算很庞大,像其他需要大型预算的项目一样,也涉及既得利益、相互游说、政治恩惠、公关活动,甚至还涉及“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想从国家的腰包里掏钱,基础科学的“思想家们”必须像其他所有特殊利益集团一样,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身负特别的任务:要向公众说明一种常常被宣传为无用的研究,实际上是够格去花费纳税人钱的。
如果沿用格林伯格的说法,基础科学的“政治”,指的是怎样从“从国家的腰包里掏钱”,那大概可以判定,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础科学都未曾开设过这门“政治课”。人们熟知的科学史上那些被供奉到神殿中的人物,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到爱因斯坦,他们那些广为人知的成就,从地静说、日心说、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到相对论,都是单凭个人超凡智力和洞见,借助纸笔就搞出来的成果,完全没有花费过国家的资助。
至于少数需要资助才能开展的研究,则取决于科学家本人施展的学术魅力,能否吸引高级赞助人愿意主动埋单。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非第谷·布拉赫莫属,他先后让丹麦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伏在他的学问之下,愿意拨款、赐岛、赐城堡、建设天文台供他进行天文观测。
总体来看,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基础科学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冷淡,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而科学家也完全安之若素,他们对政府的冷落和漠视,不仅没有丝毫不满,甚至还隐隐感到骄傲——在他们看来,受到政府重视未必是好事,这会有损科学的清誉和操守。
事情的转折是二战时的曼哈顿工程,美国政府和基础科学展开深度合作。科学学创始人普赖斯对此表达了他的著名观点:这次合作标志着基础科学从单打独斗的“小科学”时代,正式迈入由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科学家群体参与的“大科学”时代。美国政府通过这次合作,深刻见证了基础科学能够发挥的威力,二战一结束就正式“招安”——标志性事件就是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这同时也宣告基础科学从此告别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云端生涯”,需要通过从头补习新的“政治课”,学会另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
基础科学打造“话语高地”
不夸张的说,二战之前的科学史,几乎就是基础科学独领风骚的历史,当我们谈论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主要谈论的是“基础科学成就”。曼哈顿工程之后,随着基础科学进入需要“从国家的腰包里掏钱”才能养活自己的时代,这种现状很快被打破——它得面对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应用科学表现超强谋生能力,成为新“政治课堂”上的优等生。
其实这样的情形早在二战前就已经很明显。当基础科学研究在美国成为没爹养没娘要的孤儿时,应用科学及技术研究早已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曾估计,在二战爆发前12年,国家每年在应用科学上的总投入达2亿美元,而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只有1000万美元,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30000人之多,而从事基础科学的只有不足4000人。无论经费还是人员,应用科学都远远超过基础科学。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后,基础科学领域的人士很快发现,曼哈顿工程的昔日荣光如昙花一现,要从政府的口袋里搞到钱花,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曾几何时,基础科学家认为“无用”根本不是短板,追求实用是“工匠”才做的事情,知识的获取远远高于知识的应用。可现实是,基础科学缺乏“变现”能力,一般政府官员也很难理解深奥理论,而应用科学往往自带“变现”属性,很容易获得政府资助。
基础科学家当然心有不甘,希望通过有效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地位,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利用累积下来的丰厚历史资源,打造自身话语“高地”——比如出现在教科书里的那些广为流传的结论,格林伯格认为就是这种有意“打造”的结果。书中还引用其它充满强烈修辞意味的表达,例如:
基础研究之于现代文明,与希腊伟大的艺术创作和哲学创作之于希腊文明,或者大教堂之于中世纪欧洲相类似。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目标,它就是我们的社会目标之一。
除了积极打造“话语高地”,基础科学家还通过某些事件来表达对应用科学的“轻视”。典型例证是小儿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在普通人看来索尔克当然属于科学家,但基础科学家把索尔克归为技术派,理由是他发明的疫苗来自失活病毒,源于组织培养技术。尽管索尔克获得国家科学院院士提名,却始终没能成为院士,科学院院士托马斯·里弗斯对此的解释是: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原创性工作”,索尔克“并非不够优秀,但类似疫苗以前已经有过很多很多”。
格林伯格揭露说,索尔克的不公遭遇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历史上绝非孤例,多年来该机构一直刻意限制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入,这直接导致1965年工程师们建立了自己的荣誉机构——国家工程院。
应用科学的反击
对基础科学努力打造“话语高地”的做法,应用科学家的回应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声称,要从一项技术成果中划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点类似“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典型如蒸汽机和热力学的关系,这当中谁先谁后?哪个更重要?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问题无解。换言之,从知识到应用的过程并非线性关系,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以从任何人造设备或技术中筛离出单纯科学的部分都几乎不可能。
另一种则带有釜底抽薪的意味,试图从根本上否认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之父”的合法身份。碰巧的是,1963年美国国防部一项名为“回顾计划”的研究,为这种反击提供了有利的论据支持。
美国国防部对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始于1945年,在对大学基础研究持续近20年,总共几十亿美元投资之后,国防部选择了20种1945年之后出现的代表美国国家军事安全领域的尖端技术武器,包括核弹头、火箭弹、雷达设备、导航卫星以及海军水雷,试图对这些武器进行仔细分析,确定造就这些武器系统的科学技术来源。让基础科学界大为懊恼的是,“回顾计划”最终总结:通过对这些尖端武器的分析,基础科学研究在其中的贡献非常小。20种武器总共涉及556个事件,其中92%来自技术领域,而剩下的几乎全部属于应用研究类别,只有2个属于基础科学研究范畴。
另一组对基础科学不利的数据来自日本,1945年到1960年日本的经济以每年10%的惊人速度增长,然而直到1960年代末,日本基础科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依然可忽略不计。所以难怪,这时期有学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科学产生财富,相反是财富在支持科学。
中国古代技术成就提供旁证
和今天大部分教科书教授的内容不同,格林伯格在《纯科学的政治》一书中描绘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并不融洽,基础科学不遗余力努力构建“技术之父”的虚幻形象,应用科学激烈反击,甚至到了“精神弑父”(在基础科学看来)的地步。结合全书十二章内容来看,这并非格林伯格要论述的重点,仅在一、二两章中作为背景知识呈现,从第三章起他很快转到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上:1960年代基础科学研究在新的基金申请体制下遭遇的新挑战。
此书初版于1967年,从作序的两位大牌人物的反应来看——无论是已故Nature总编麦多克斯,还是著名科学史家史蒂芬·夏平,在序言中都绝口没有提到这个内容,可以推想,格林伯格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的论述,应该并未引起学界太大关注。
不过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格林伯格书中这个貌似小众的观点,居然可以从中国古代技术成就中找到有力旁证。江晓原在他《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的导言中明确指出:
比如都江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千多年过去,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巨大效益。都江堰这样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人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人们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的猜想是,李冰父子熟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都江堰并非孤例,江晓原在书中谈到的其他若干中国古代技术成就——造纸、印刷、火药、钓鱼城,都是独立于基础科学理论出现的技术成就。
《纯科学的政治》和《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两书提供的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新图景,可以启发我们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一些事物。
按照长久以来流行的看法,基础科学决定应用技术发展的上限,而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理论都是西方人提出的,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将在技术上始终处于领跑位置,而其他国家只能永远处于落后追赶状态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就是因为过份偏重“实用”,才导致基础科学理论的落后,言下之意,偏重“实用”成了某种严重的短板和缺陷。
但是,如果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关系事实上是开放的,那事情就可能出现另一种不同的走向。这意味着基础理论不发达的国家,在合适的情形下,也可能独辟蹊径产生先进的技术。何况,对那些曾经取得过辉煌技术成就的国家,难道没有理由推想,未来完全有可能迎来技术文明的二次伟大复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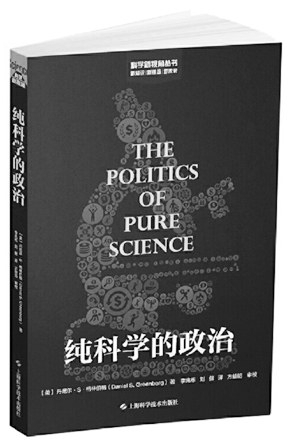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