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命题和阅卷,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多年来媒体向我邀约这方面的采访时,我都直言谢绝了。每年高考过后,浏览着汹涌的各路专家评论和网民吐槽,我只有哭笑不得的沉默而已。还不如看看那些造谣我叛逃美国朝鲜、加州豪宅曝光或者到天门山出家之类的新闻爆料,更能解颐。
今年高考结束,我在北大计算中心偶遇已经退休的前招办领导史明老师,从当下的疫情,聊到了2003年的非典,聊到了我们将近二十年间合作阅卷的一幕幕往事,这不禁令我想写一写早已过了保密期的——17年前的非典阅卷花絮了。
高考是“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按理说应由高校教师阅卷,即“谁招人谁把关”。但高校教师大多不了解基础教育详情,单凭一纸评分标准,很难单独胜任。而中学教师虽然了解一线教学,可各区县各学校的学生水平、教学风格、应试套路,都存在较大差异,阅卷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顽强的本位主义。例如发现一篇作文很像自己学生所写,随后的一系列相关影响,是颇难把控的。而我恰好在北京二中和首都师大附中,当过三年语文老师,后来虽留北大任教,也一直参与各层面的语文改革,不仅编过语文教材,而且与中学界、写作界长年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自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打酱油参加阅卷后,便再也不能脱身,成为语文阅卷乃至命题团队里,沟通高校和中学、打通学术和教学的达摩堂长老了。
现在语文科目已经习以为常的网上阅卷,是从2008年开始的。相比之下,此前的纸笔阅卷,是“高耗型重脑力劳动”加“繁琐型轻体力劳动”。特别是2003年以前,高考都在暑热的7月,阅卷场地既没空调,也无冷饮。各大题的组长把进度等各种数据写在黑板上,不断更新。小组长则逐本检查试卷,挨个叮嘱问题。连续几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又热又累,几乎每年都有阅卷员晕倒病倒。那个时候,老师们的收入普遍较低,阅卷报酬更是低得令人羞耻。阿忆曾在网上晒他4千元的北大月薪,遭到一片围攻,是我出来力挺阿忆,说我的月薪还不到4千呢。幸好在史明老师等领导的支持下,北大的食堂,每天都提供了高质量的午饭,用三轮车送到现场,不是有红烧鱼,就是有扒肘条。一位远郊县的老师首次参加阅卷,第一天午饭时说:“呀,今天咱们吃这么好哇!”第二天午饭时说:“咦?今天还吃这么好哇?”第三天午饭时说:“哦,咱们天天吃这么好哇!”我在旁边听了,不禁微微心酸。
要在条件苦、待遇低、限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调节好这样一支队伍,一是依靠从市委到北大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二是依靠北京语文界的一批重量级专家。当年编过一个口诀,我记不全了:东城有个东——薛川东,西城有个西——顾德希,宣武有个文——柯素文,海淀有个山——方晓山……在这些前辈的鼎力襄赞下,逐渐磨练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阅卷骨干队伍。假如没有这样一支精诚团结的队伍,那么每年不知道要出多少矛盾乃至事故。每年阅卷结束,赠给每位阅卷员和后勤安保人员一本我的新书,史明老师组织几百人分别排队,让我签名,那种温馨而热闹的场面,激起的是战友般的亲情。
而到了2003年,国家采纳各方建议,高考改到6月。本来这是个载入高考历史的“典型标志”,但谁也没有想到,年初爆发的SARS,春天达到了高潮,直到5月底,北京的新增病例才开始为零。于是留在我们阅卷人员脑海中的那一年,就成为“非典之年”。
由于北大被定为特殊隔离单位,因此那一年另选了保密阅卷场地,几百人的后勤,压力甚重。北大特派一辆专车每天接送我——这是我唯一连续十天享受校领导待遇的“特权时光”。往年阅卷的首要任务是信息安全,而2003年的首要任务是人员安全——不能让一个人感染SARS。假如一人感染,可能一组人都要隔离,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战略预备队,以防不测。每天场地要消毒、人员要消毒、试卷要消毒,仿佛一支生化部队在作战。头一个相对凉爽的阅卷季节,由于对病毒的恐惧,被强行升温了。
于是仿佛仍然在炎热的7月,参加阅卷的高校和中学老师们,一早就从小组长手里领到一本一本的试卷,签名登记,左手翻着卷纸,右手在答案上比量着,远看颇似一个服装车间里,工人们在缝纫机上进行裁剪。圆珠笔一根一根地用废了,试卷一本一本地堆积起来了,场地里回响着哗哗的翻纸声和低低切切的叮嘱声。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双评”制度,从填空到作文,都是一支笔给分。小组长的复查任务非常繁重,大题组长的审核任务也相应加重,而最后推到我这里来的终审工作量,也明显高于往年。如此劳累阅卷之后,再聪明的人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脑子几乎拒绝运转了,合分工作难免出错,于是就单请了一批学生,专门进行分数加减。史明老师他们紧张地搬运、打包、分类。要把各区县各学校的试卷打乱、混编,阅卷之后还要再归队、合编。既要管物资,又要管人员。既要管交通,又要管吃饭。既要保人员安全,又要防无良记者,所有的阅卷员和后勤安保人员,都感觉自己跟非典前线的医生一样,身处一种战时状态也。于是脑海中保存了很多鲜明的画面,却连那一年的饭菜是什么滋味,都记忆模糊了。
2003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转折”,文体不限,这是符合非典背景之下,降低命题难度的上级指示精神的,意思就是尽量不用动脑,不设限制,让所有考生都“有话可说”,另外也有利于引导积极向上的健康情绪。但是从阅卷的学术性来看,命题越放水,就导致阅卷越艰难。假如把所谓“快乐教育”的原则推到极端,高考就出几道四则运算水平的题,作文怎么写都以各种理由给高分,甚至很多省市涌现出大批真真假假的“满分作文”,那区分度怎么体现?教学成果怎么体现?考生实际水平怎么体现?择优录取的国家战略怎么体现?……就从这个“人人有话说”的“转折”来看,许多考生都简单地把抗击非典取得胜利说成是“转折”,而实际上既没有写出“转”,也看不出有什么“折”。还有大量考生把平时准备好的某篇文章,硬贴上转折的标签。于是得了非典坚持上学,也是转折;亲人去世了,发现遗物中有张照片,也是转折;李白看见老奶奶磨铁杵,也是转折;爱因斯坦煮手表发明了蒸汽机,也是转折……本来每年的作文中,那些经过“悲情训练”的学子们,都要写死一大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这特殊的非典之年,就更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了。而站在阅卷立场,既要理解和同情在非典背景之下的教学滑坡,又要坚持为国选材的客观标准,既要防止分数趋中形成的难解难分的“大肚子”,还要注意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另类思想情绪……这些标准如何细化为阅卷员的操作指南,真是令人煞费苦心也。
阅卷进入尾声,突然开来一辆密闭武装押运车,运来的是罹患SARS考生的试卷。由于我掌握每一道题的评分标准,所以我穿上防护服,进入专设的消毒阅卷室,亲自评阅这批试卷。因为数量不多,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印象中整体的成绩还不错,我心想这些考生身患非典还能镇定答题,真是应该嘉勉。不知道17年后,那些我亲自给了全部语文分数的学子,都在何处,其中会不会有人参加了今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呢?
今年的高考时间,遇新冠特殊时期,由延续了17年的6月,又一次改到了7月,这到底算是“典型”还是“非典型”呢?现在的阅卷,早已是“无纸化”操作,严密的安检使得阅卷现场片纸不得出入。所有的题目都是双评,所有的阅卷细节都可以即时监测和调控。搬运分发试卷等机械的体力劳作大规模减少了,但是阅卷员的劳累强度并未相应减轻,而今年的防疫,也比当年更紧张了。所以今年,仍然属于“非典型”的高考年。当我提着从食堂买来的套餐,行走在未名湖东岸,环视四围悠悠垂柳,寥寥行人,我在心底默默念道:
2003年出生的孩子们,你们明年就要高考了。祝今年的考生,和明年的考生,闱场如愿,一生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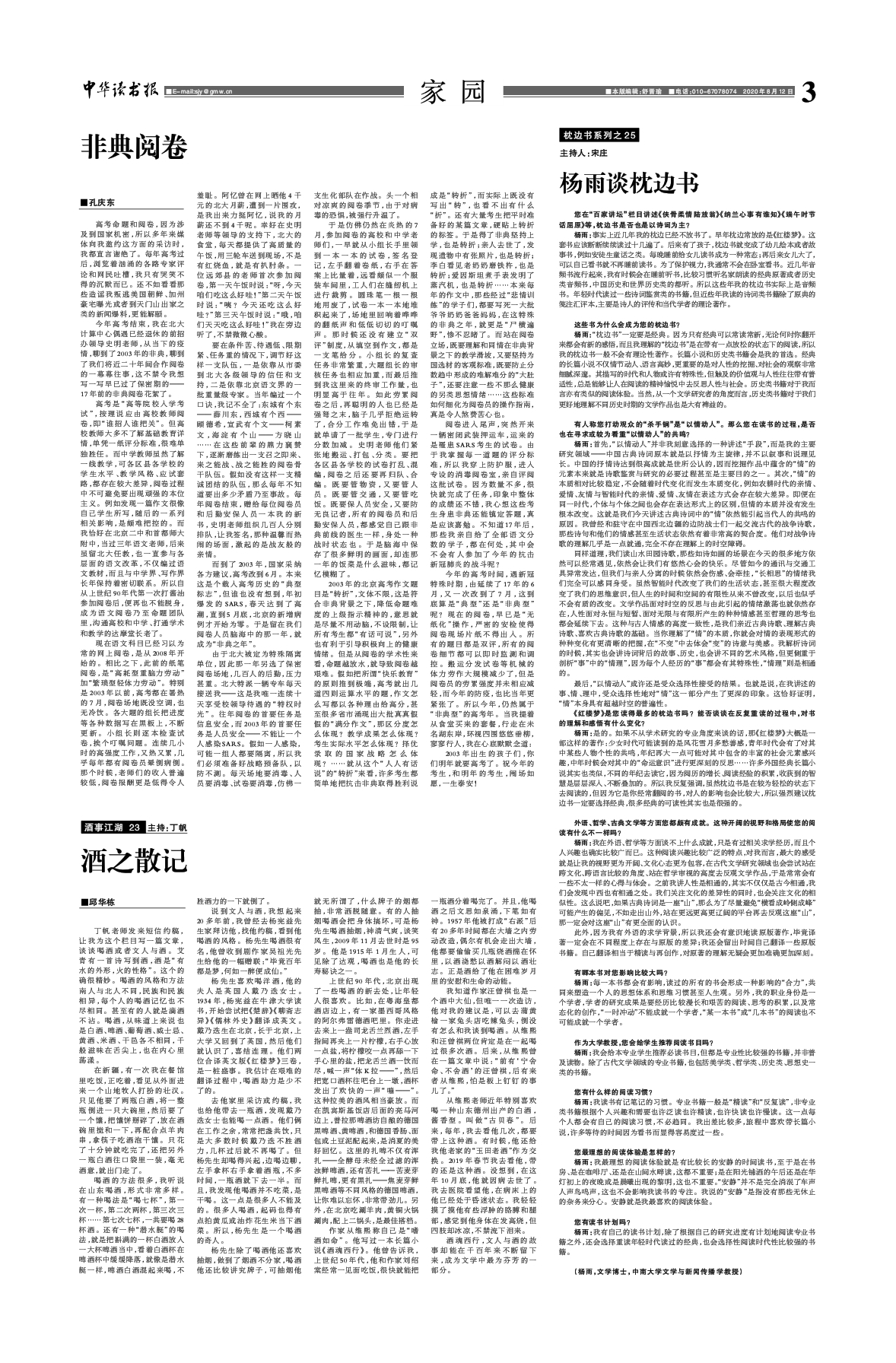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