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汤因比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部巨著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但也曾引发争议,甚至使汤因比“跌落神坛”。要理解这一切,自然需要去了解这本著作诞生的来龙去脉。完整的《历史研究》一共12卷,其出版历程跨越27年(1934—1961)。若从汤因比开始酝酿这部作品的1920年算起,则是41年,基本上囊括了汤因比的大半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完成的作品,不能不受到作者人生际遇变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结合其人生来阅读《历史研究》。
威廉·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追索汤因比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这本传记详细考证了《历史研究》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并对如何评价、理解这部作品乃至汤因比本人发表了看法。
青年锐气:《历史研究》的酝酿
在麦克尼尔眼里,《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应在于,开启了一种宏观、平等地囊括所有人类文明的系统研究,这与他自己所坚持的全球史研究是相通的。麦克尼尔通过大量史料,追溯了汤因比这种世界性视野的形成经过。
汤因比的母亲曾担任历史教师,叔叔阿诺德是以研究工业革命知名的史学家,哈利叔公曾是远洋商船的船长,这样的家庭环境给汤因比提供了关注历史和开阔视野的启蒙教育。英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则给汤因比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从温彻斯特公学到牛津巴利奥尔学院,成绩优异的汤因比已经展现出成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他不受牛津大学当时排斥宏观思考的课程和氛围影响,坚持从宏观视角思考历史。1910年的汤因比立下了远大志向:“我希望成为一名史学巨擘——这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并且我渴望自己在其中承担尽可能多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汤因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战爆发后,他辞去在巴利奥尔学院的教职,走出象牙塔,积极参与政府情报工作。耳闻目睹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汤因比感受到似乎历史在重演,他想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于是开始思考历史循环的模式与可能性。
向宏观文明体系研究的转变发生在1920年。麦克尼尔对汤因比这一学术路径转变的分析堪称精彩。他详细分析了两位学者给汤因比带来的智慧启迪。首先是斯宾格勒。汤因比阅读《西方的没落》后,大受启发,甚至怀疑自己的课题已经被斯宾格勒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再加上1920—1922年在前线报道希土战争期间,汤因比目睹希腊和土耳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而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灾难,汤因比更加接受斯宾格勒的悲观主张,即不同文明的融合是人类历史走向衰退的标志。其次是美国历史学家特加特。特加特像生物学家研究生命形态的发展史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汤因比由此意识到,分析式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人类族群具体历史的比较之上。
1921年,在从伊斯坦布尔返回伦敦的火车上,汤因比在一张草稿纸上拟订了写作提纲。提纲的要点是,以文明为独立的历史研究单位,所有文明的历史是平行可比较的,一视同仁地看待所有文明,文明像生物一样会经历诞生、分化、扩张、解体等过程。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汤因比广泛阅读欧洲地区以外的材料,为这个框架填充内容。30岁出头的汤因比,已经走在这项毕生事业的正轨上。
功成名就:《历史研究》的诞生
《历史研究》是从业余写作中诞生的。因为在第二次希土战争中为土耳其发声,汤因比失去了伦敦大学的教职。但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工作。为了履行这一工作的职责,汤因比必须每年从海量材料中整理编纂出一部国际事务调查报告,然后才有时间为自己的研究做准备。
汤因比的勤奋、野心勃勃、良好的时间管理,使得他能够充分平衡职务工作与个人研究的关系,甚至让二者相互促进。在几个年度的报告里,他将时事政治的分析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同时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关注当地局势,等于是在给自己的研究收集材料。比如在1926年报告中,他用了一半篇幅叙述远东与太平洋地区事务;1929年前往日本京都参加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会议时,他不断在沿途见闻中思考亚洲文明同西方文明的接触问题。
《历史研究》的写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1927年至1929年夏,汤因比利用闲暇,将1921年的提纲扩充得更为详细,最终写成750页手稿,结构已经与最后出版的《历史研究》基本吻合。1930年夏,汤因比开始了正式撰稿。他在每年的前半年集中精力完成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随后前往甘索普忘我地写《历史研究》。
终于,1931年,汤因比完成了这本著作的前三卷。同年12月,汤因比投稿给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人汉弗莱·米尔福德。四周之后得到米尔福德的答复:“我无法拒绝您的《历史研究》,尽管它篇幅巨大。”1934年,《历史研究》前三卷出版。随后在英国大受好评。前三卷还取得了不俗的销量,仅6个月后,第一版就已经脱销。1939年出版的第4-6卷也赢得不少赞誉。
然而,是1940年代索默维尔节编本的出版,才进一步让汤因比在英国之外名利双收。1943年,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索默维尔致信汤因比,告知自己完成了前六卷的节编本。汤因比一开始并不乐意,但在阅读索默维尔的文稿后改变了主意。节编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在伦敦出版,1947年3月在美国纽约出版。这个版本在美国大获成功,首印13000册很快售罄,到1947年9月已经卖出10万册。再加上《时代》杂志的鼓吹,汤因比风头一时无两。节编本的成功还不止于此,后来陆续传播至欧美之外,比如当今中国读者读到的《历史研究》中译本,正是译自节编本。
总之,《历史研究》成就了汤因比的世界声誉。麦克尼尔总结其原因是,《历史研究》前三卷的出版时机恰逢其时。1934年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节点,一战的阴影还未散去,西方文明究竟是崩溃,还是通过建立国际秩序来应对挑战,局势还不明朗,当时的局势使得《历史研究》当中的事例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应和了公众焦虑情绪。而节编本省略了大部分可有可无的例证和借题发挥,从而更容易阅读,所以特受读者欢迎。麦克尼尔也对汤因比的写作能力发出由衷赞叹,认为能够将对现实事件的叙述同跨越全球辽阔时空的历史比较结合起来的,仅汤因比一人而已。
毁誉参半:《历史研究》的争议
1954年,《历史研究》第7-10卷出版,此时距前六卷出版已经过去了15年时间。这四卷的出版标志着汤因比宏大体系构建的基本完成,然而却遭受了与15年前截然不同的待遇。第7-10卷受到了猛烈的质疑与批评,甚至导致整部《历史研究》被否定。批评者包括彼得·盖尔、特雷弗—罗珀等。尤其以罗珀的批评最为激烈,他讽刺汤因比是一个自我认定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他的批评对汤因比在西方学界的声誉带来了最严重的伤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15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在汤因比事业大获成功的同时,私人生活的悲剧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汤因比的思想因周边环境刺激而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了《历史研究》的走向。正如麦克尼尔总结的那样,第7-10卷与前六卷在精神内核上已截然不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大杂烩,夹杂了许多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的新观点,否定了前六卷相关探讨中大部分内容的价值。
麦克尼尔使用大量书信、档案、访谈等材料,向读者还原了汤因比在这段时期所遭遇的变故。在《历史研究》前三卷出版后,母亲去世、长子自杀、其他两个儿子的叛逆,以及长期挑战极限的工作方式影响了健康,一系列变故让汤因比开始失眠、焦虑。汤因比从未让家庭事务干扰他的写作,他甚至将写作放在第一位,正是这种过度沉迷工作的态度,导致了汤因比家庭生活的不幸。
最大的打击是与妻子罗萨琳娜的离异。罗萨琳德与汤因比的嫌隙早已有之,这位业余的小说家从不曾欣赏汤因比的事业,《历史研究》在她眼里不过是本“胡说八道的书”。两人的关系在1930年代后半期日趋恶化,当罗萨琳德有了新的爱恋对象后,两人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经过长时期的挣扎,他们终于在1946年离婚。在此期间,汤因比陷入深深自责与精神困境,为了摆脱这种负面影响,他开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甚至逼迫自己像妻子那样信仰天主教。虽然没有完全接受天主教,但是他已经与宗教信仰建立起密切联系,给自己的写作带来了巨大副作用。
二战中德国胜利、法国战败等政治局势的恶化,令汤因比转变了对文明与宗教关系的看法。在此之前,他认为宗教是孕育文明的蚕茧。此时,他转而认为文明是为宗教服务的,文明的烟花是周期性的,而宗教的发展是线性上升的,世俗文明或许会灭亡,但宗教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就这样,宗教成为《历史研究》乃至其他后期著作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主题。
在《历史研究》第4-6卷中,这样的变化已经有所体现,不过二战的爆发转移了人们对此的注意力,这使得对《历史研究》及汤因比的猛烈批评还没有那么快出现。而在第7-10卷中,这种变化展露无遗,汤因比转而关注一种更加普遍的宗教,把接近上帝、探寻历史背后的真实意义,作为人生终极目标和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他要向世人揭示上帝的存在,扮演先知的角色。——也许,更理智的做法,是干脆就新的主题另外写一本书,但是汤因比没有这么做。
汤因比不得不以部分妥协来为《历史研究》画上句号。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反思》中,他部分承认自己关于文明停滞的观点是错误的,以此与学界达成部分和解——他毕竟已经老了。汤因比精心构建了一个体系,又亲手破坏了它。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荣耀,又倔强地遵循真实意愿去作出改变。
此后他依旧笔耕不辍,直至1975年去世。留在身后的,是《历史研究》曾经获得的赞誉与质疑。
总之,麦克尼尔以客观的态度剖析了《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在学术志业上,尽管他曾经受到汤因比的积极影响。但是,他并不讳言《历史研究》的缺陷,认为与其说《历史研究》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还不如说是历史类比与相似性研究的汇编,汤因比像是一位不断受到环境变化刺激而作出即时反应的诗人,虽然史学写作永远具有诗性,但他的诗性超出了书斋式史学著作的规范,因而造成不幸。
实际上,麦克尼尔在传记里对《历史研究》的“解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变相的辩护。他让我们看清了汤因比是如何雄心勃勃地实现个人的学术目标,个体又是如何被时代、环境的巨大洪流所席卷。这部传记的作用应该在于,让人对汤因比产生“同情”,至少避免单纯地追捧或抨击《历史研究》。毕竟作品都是“人”写出来的,阅读作品的同时,总是离不开阅读写作的“人”及其世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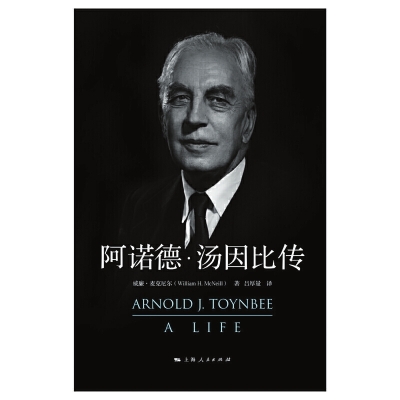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