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2020年推出中译第三版精装修订本。在2011年初版“代译后记”《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我已经叙述了此书基本情况。十年过去,对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又出现了一些与此书相关的新情况,故有必要再作说明。
我在翻译此书时,除了被洪业独到的论述角度、纷出的原创观点所吸引,也为其中流寓异域的故国之思触动,形诸译笔。所幸读者乐于认同洪业对杜甫的阐释,也就附带接受笔端常带感情的译文,并认可某些不合常规的做法(例如以文言翻译《自叙》、在脚注中以“译者按”加入讨论等),真是幸何如之。现在回想,就学理逻辑而言,在不违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对同等的材料做出更大胆的想象与推测,这种对材料的理解不但能够反映被研究对象的性质,还能够映射出研究者的心灵世界与历史语境,从而增加了读解的丰富性。历史的意义常在于求得一种文化价值之追忆与认同。史学研究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尽可能地去揣度一段“合情理”的史迹,作一种“有意义”的假说,藉以发明古人及今人孤怀隐衷之深切著明,恰恰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意义。
洪业及其《杜甫》尽管有过一时沉寂,然而潜德幽光,必不磨灭。2020年BBC播出的同名纪录片正是以洪业此书为最重要的参考底本撰写脚本,故能在交流沟通尚存在障碍与壁垒的时代,通过洪业著述的桥梁达到对杜甫真挚有诚意的理解。在各种机缘促进之下,洪业《杜甫》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各个阶层的读者认识。借用哲学家理罗蒂的观念来理解,杜甫“追根究底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原因,其唯一方式是用新的语言诉说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原因的故事”(查德·罗蒂《偶然、团结与反讽》)。洪业亦然,他用关于杜甫的语言诉说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原因与结局的故事。这样的关于人性的故事一定会在我们的时代,以及今后的时代流传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且不论杜甫在集大成基础上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探究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从而接近了古典诗歌写作的极限,即使从人性的角度看,所谓“最伟大”之争的结果也不言而喻,还是借用罗蒂的话,“希望在尚未结束利用旧字眼来表达新意义之前,人们就不再继续问那些利用旧字眼说出来的问题了”。
在个人境遇情性之外,洪业的杜甫研究在纯粹学术领域中的开创性意义,仍有待彰明。译事既毕,我常反思洪业为何能在千百年来为无数人阅读、研究的杜诗中发掘出大量原创观点?我的答案是:清代以来迄今的杜甫研究的隐含前提是以清代“集大成”杜集注本为起点,洪业以史学家的职业素养,加上早年编纂《杜诗引得》对杜集文献流变的了解,研究杜甫必以源头性的杜集宋注、宋谱作为起点,不盲从约定俗成、后出而缺乏源头性文献依据的意见,从而摆脱了以清人注本为起点的前提束缚。这是《杜甫》一书虽出版于1952年,不但迄今仍被公认为西语世界中杜甫研究最重要作品,而且大量观点置于今日国内学界仍具有原创性的原因。受此启发,我提出“杜甫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这一观念,这是洪业虽未明言、却付诸实际的做法。当然,杜集宋注本体系复杂,迄今尚未得到过全面系统的梳理,洪业当时也仅能目睹、利用其中一部分,如今的研究条件要好得多。过去十年我通过《杜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与《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完成了杜集宋注本的基本梳理工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此书既是宋代晚出的总结性注本,又是杜集宋注本中成书情况最复杂、版本源流最混乱、整理难度最大的一种,《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确定、补齐善本为底本后,以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为基础对注文进行比对考辨,还原了至少95%以上的注文源流,可以视为一部全面的“杜集宋注考辨汇编”。全书预估达120万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即将问世。
上述工作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杜甫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我目前正在进行的《钱注杜诗疏证》研究,将回答问题的另一半:为什么杜甫研究“不能以清代注本为起点”?《钱注杜诗》向来号称以吴若本为底本,又是最具原创性的清代杜注,为后来仇、浦、杨等注本遵从。我已从编次角度证明了钱谦益擅自改动吴若本且刻意隐瞒的事实(近来钱曾、季振宜刊印《钱注杜诗》依据的稿本在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被发现,接下来还将比对刊本与稿本,核实稿本中有无更接近吴若本的可能性)。在注文层面,钱注在观点原创性上没有超出宋注的范围。钱注受到文献搜集的限制(此点通过《绛云楼书目》记载以及比对钱注与宋注可以发现),对宋注尚未能全面掌握,且颇多误解。钱注的主要贡献只是在宋注提供的观点基础上更规范地征引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形成注文,最明显地表现在地理、史实方面。《钱注杜诗疏证》将重新评估《钱注杜诗》的价值与地位,此书刊行也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以上种种,追溯源头,都应感谢煨莲先生及其予人启发的著述,爝火微光,踵武前贤,中心藏之,何日敢忘。
读者如果结合性情、学术两个维度阅读《杜甫》此书,或许能获得更丰富深邃的体会。
我在日常使用此书时,陆续记下译文及排印错误,此次新版都据以修订。对于手中持有旧版的读者,我把据2011年初版所作的修订列出供参考:
(1)50页注1,“李林甫”改为“王鉷”。
(2)56页倒数第10行,“自注”改为“几句”。
(3)62页倒数第4行,“研”改为“砚”。(4)110页第3行,“二十世纪的注家”应改为“十二世纪的注家”。
(5)142页第12页,“来到成州”一句之后加入“再往东南60英里,到达同谷;”。
(6)158页倒数第5行,“骄儿”改为“娇儿”。
(7)164页第4-5行,“后来被李若幽接替”,改为“他接替的是李若幽”。
(8)185页注1,“IXXIX”改为“LXXIX”。
(9)196页第12行,“后者”改为“前者”;第14行,“前者”改为“后者”。
(10)211页注第5行,“CCX-CLX”改为“CCXCIX”。
(11)216页第1行,删去序号“三”。(12)219页注第3行,“鲁訔”改为“卢元昌”;第13行,“《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改为“吕大防”。
(13)225页,引《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题宜加“并序”二字,下引诗序与诗之正文应分别成段,以作区分。
(14)254页第3行,“760”改为“770”。(15)309页第14行,“校蔡梦弼《草堂》,本荟粹群书”,改为“校蔡梦弼《草堂》本,会粹群书”。
(16)311页第1行,“于是常熟吴江各刻其书”,改为“于是常熟、吴江各刻其书”。
(17)311页第12、13、14、16行,“书中所指遵王,谦益族孙曾也”、“又书曰”、“钱谦益与钱曾书曰”,皆改为宋体正文。
(18)312页第2、10、13、17行,“又书曰”、“又书曰”、“又书曰”、“钱谦益与潘柽章书曰”,皆改为宋体正文。
(19)315页第1、23行,“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曰”、“朱氏《辑注杜工部集序》曰”,皆改为宋体正文。
(20)382页倒数第6行,“戎州”、“戎县”凡三处“戎”字,皆改为“忠”,“宜宾郡”后加括注“(译者按:当为“南宾郡”)”。
(21)440页倒数第4行,medota改为mendota。
其中第14条至第19条是对附录《杜诗引得序》的修改。新版虽然删去这一附录,但我仍想提醒读者,若不满足于传记叙述,要探骊得珠,进一步深入杜诗文本世界,必须经由被视为第一部杜集文献版本源流简史的《杜诗引得序》入手(除参《杜诗引得》外,亦载于《洪业论学集》等)。我开设的杜诗课程至少有一半时间用来细读这篇序言,尽管这每每使得乘着传记叙述之兴而来的同学怨望而归。
在第三版修订过程中,责编刘赛兄除吸收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外,还提出了更多意见,商量讨论中旋生旋改,故未及尽数列入上表,我记得其中涉及杜甫诗句“稠花乱蕊畏江滨”中的“畏”字,当依洪业所据的《九家集注杜诗》作“裹”,以及杜甫登严武之床是否为“胡床”,闻一多、冯至著述版本等问题。尽管如此,新版一定仍有目力不及的舛讹,也请读者继续指瑕。近日有读者指出,新版第六章《东胡反未已》第124页第1行,“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马元帅”一句,“享”是“亨”之误。只能请读者谅解,留待重印再改。好在“文章千古事”,得失一时难尽觑,且待从容安排。正如洪业先生所说:“杜甫题诗于岳麓山寺壁时,感谢宋之问未把风景都写完尽。很多的问题,我也分留与将来贤哲。”他总是这样暗暗地幽默,参透世情而又不失自信,令人忍俊不禁,向往其风采仪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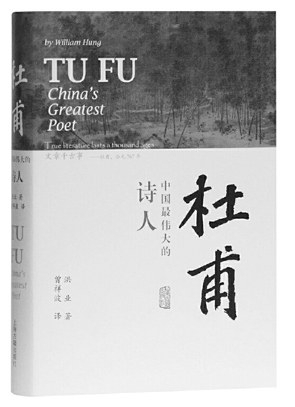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