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31年法拉第从运动的磁铁为线圈赋予电流的现象中发现电磁感应之时起,一个属于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时代便在他的洞见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当代人的眼中,电磁感应与形而上的思考,与宗教的情感,并无瓜葛,数据与实证主义以一己之力推动着科学发现的不断拓展。但是在法拉第眼中,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此简单。他的基督教信仰曾是他所有活动的中心,包括他的科研活动。这种信仰非但没有阻碍他在科学之路上的探索,反而对他多有助益。
这种影响还发生在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威廉·哈维身上;发生在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身上;发生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的完善者罗伯特·波义耳身上……对于历史上数不清的科学家而言,研究自然的动力源于信仰,而非源于舍弃信仰。
为什么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会贯穿历史,绵延至今?作为艺术家的罗杰·瓦格纳和作为牛津大学科学家的安德鲁·布利格斯合著的《次终极追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便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在两位作者看来,人类始终热爱探索世界,始终感受着自然的魅力。从史前时代那些渔猎部落开始便是如此。11000年前位于非洲厄瓜多尔的原始渔村遗址中,就有关于月相的观察记录,而骨器上的道道刻痕,至少证明了书面记录手段自那时起便已经存在。“次终极追问”所形容的,是一种对物理世界不懈的学习,和永不满足的求索。而现代科学,正是人类长达几千年的次终极追问历程的巅峰。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位作者眼里,科学是一种次终极追问,而非终极追问。原来,许多科学研究的终极驱动力,其实是某种强烈的宗教冲动。通过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瓦格纳和布利格斯认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叙事或行动组织起来的,那就是对现象世界之外的某种存在的关注。这一宗教维度几乎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欲往往与对于宗教问题的探索欲相交叠,并且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终极来源。
瓦格纳与布利格斯将这种相互影响比作一种名叫滑流(slipstream)的流场——当某一物体在另一个物体带起的滑流中运动时,它受到的阻力更小。就像大风天气里孩子跟在大人身后行走会更省力,就像大海里鱼群跟着领头鱼游动会更舒服,就像自行车赛道上主车手跟在破风车手身后能够在同等的速度下花费更少的能量以保存体力。
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如此。最古老的人类社会都倾向于将精力花费在被我们称作宗教的东西上。例如史前艺术往往具有仪式功能,而文学作品又往往与创世神话相关。而这些终极追问又将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拖进了它们的滑流中:那些古老的岩画,尽管是为了宗教仪式而绘制,但也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动物生理结构的观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例如中国、印度、南美洲和中东地区,都能找到人们在终极追问的驱使和陪伴下探索物理现象的身影。
让我们追溯至公元前500年便已繁荣兴盛的希腊爱奥尼亚城邦,爱奥尼亚人强烈地相信某种神圣的源头规制着并掌控着宇宙。这种信念引导着阿那克萨戈拉研究太阳、月亮和天堂。当后来的希腊天文学家证明行星的运动能够被数学所预测,他们便更加坚信世界是理性设计的结果。柏拉图相信,宗教理解、道德和科学能够形成一个综合的智识体,在他的对话录《蒂迈欧篇》中,将宇宙之父和创造者描绘成一位几何学家,并对神的存在即是正道(eikoslogos)展开了辩论。
再让我们顺流而下1100年,看看伊斯兰教诸帝国。《古兰经》规定了穆斯林们每日礼拜的时间和朝向。为了让帝国各处的穆斯林都能确定麦加的方向,需要穆斯林天文学家解决复杂的几何学问题,并进行精确的天文观测。而在钟表发明之前,每日五次按时礼拜的要求,也促成了天文学和数学的进步。为了宗教信仰而研究科学的观念,在许多穆斯林科学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伊本·艾尔-海塞姆——其光学研究奠基了系统实验在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便认为“除了探索知识和真理外,没有任何(接近神的)更好方法了”。
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家也同样如此。尽管伽利略的形象一直被描述为现实理性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却相信“神圣的恩典”令他“哲思深远”,而“对神圣的设计者的爱”,则是他“工作的至高终点”。牛顿研究物理学的目的是“用上帝的造物为祂增添荣耀,并教导世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罗杰·培根、哥白尼、开普勒和麦克斯韦也都用他们的科学与信仰共同福泽世人。
瓦格纳与布利格斯相信,这些跨越文化、贯通古今的例证都证明着,人类关于心灵和世界的关怀都需要寄托,而这种需要形塑了人类经验的某种核心。为“作为整体的世界赋予意义”的热切渴望,预示了科学与信仰的纠葛将永存世间,而次终极追问也将继续畅游在终极问题的滑流之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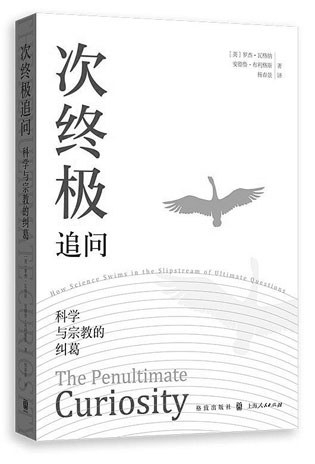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