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了。那时,我还是个少年,随着父母、哥哥、姐姐去逛故宫。票价银圆一元,是按照颐和园票价先例定的。当时的宫殿是溥仪出宫时现场的原状: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日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瓷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猎人,等等。桌上有各式大座钟和金枝、翠叶、宝石果的盆景。洋式木器和中式古代木器掺杂在一起,洋式铁床在前窗下,落地罩木炕靠着后檐墙。古铜器的旁边摆着大喇叭式的留声机,宝座左右放着男女自行车。还有一间屋内摆着一只和床差不多高的大靴子。这件东西有什么用?不知道。以上是我对于当时叫作内西路的参观印象。
中路乾清官、坤宁宫等都开着门,允许走进去,但三面拦着绳子,只能立在当中往左右看。坤宁宫,煮肉大锅是很引人注目的,西北角显得很神秘,挂着黑色幔帐。乾清宫东西庑,有几间开着门,那是陈列室,但看得出还有些原陈设家具(并非陈列品)也保留在原处。此外,还有内东路、外东路、外西路,亦都仅是参观宫殿而已。皇宫总算是全部开放了。当时,我刚十二岁,小孩子不懂什么,但也知道这里原是皇宫,过去百姓是不能进来的,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遍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几年之后,我又来过故宫一次,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的年月。我记得还买到了故宫编印的《掌故丛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能够阅读这样的期刊了。其中《圣祖谕旨》那一栏目,第一次使我知道皇帝的谕旨中也有生动的家常白话,内容都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期从漠北寄回北京的谕旨。书中还有乾隆时英吉利国王派使臣马戛尔尼来聘的档案。这些史料能够让中学生感兴趣的原因,我后来分析,可能因为当时我国在世界上居于弱国的地位,而这两部分史料所记录的都是我国强盛时期的口气和语言。尤其康熙到漠北狼居胥山,看到明代永乐皇帝立的碑,康熙表示了对前朝皇帝的敬仰。对这一节史实,印象极深。中学生的文化程度当然谈不上研究历史,但对历史上我国曾经立碑的地区已经不再属于我国版图这一点,我是很敏感的。所以发行这种期刊,不仅可供史学家研究之用,而且对于一般读者确实起到了增强爱国思想的作用。
北伐统一以后,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年之内,故宫博物院有了变化,我这个参观者的文化程度比过去也提高了一点,对于陈列的文物开始喜欢看了。故宫博物院的票价由一元降到五角,轮流开放内东路、外东路和内西路、外西路,但中路则每日都开放。钟粹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还有景阳宫瓷器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承乾宫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乾隆珍赏物陈列室以及其他一些陈列室。从这个时期开始,故宫博物院有了内部优待赠券。我的哥哥朱家济和庄尚严、傅振伦、张廷济等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我有赠券,可以常来故宫。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钟粹宫陈列的书画,那时每月更换陈列品两次。当时专门委员会每周开鉴定会,每星期一故宫博物院派人送一份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给我的父亲,这等于给我一个预习的机会。父亲每次开审查会回来,对着目录告诉我,某件真,某件假,某件真而不精,某件假但笔墨还好,某件题跋真而本幅假,某件本幅真而某人题跋假,等等。我的哥哥朱家济和杨宗荣两人是专管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每次更换陈列品,我哥哥总先告诉我,这次更换的有哪些名画。因为有这种机缘,所以故宫当时所展出的《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我都有幸观赏过。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编印发行的《故宫周刊》《故宫》(月刊),还有许多单行本影印的法书名画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读物。
“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古物南迁以后,故宫博物院内冷冷清清,我就没有再去了。一直到1943年,故宫博物院保存在贵州安顺的一部分文物,即曾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的八十三箱精品,于重庆中央图书馆临时展览时,在庄尚严的领导下,我参加了临时工作,晋唐宋元明清法书名画,又得以寓目一次。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马衡院长派我在古物馆工作。从此,我就不再是参观者了。
青年时代经历的故宫博物院院庆
故宫,在1925年10月10日成为博物院,因此,每年的10月10日是成立的纪念日。就像人的生日一样,这个纪念日称为院庆。每逢十年好比人的整寿,可以称大庆。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的那一天,我是一个刚过十二岁的儿童,随着父母兄姐,一家人来故宫参观。当时是五路开放。关于这次参观,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发表在1985年《紫禁城》的院庆特刊上,那一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六十年大庆。
每到10月院庆必有新的陈列出现,记得承乾宫专辟为“清代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专辟为“乾隆珍赏物陈列室”,都是在那几年中的“院庆”时开放的。承乾宫前后殿共陈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四百余件,真是珐琅彩的大观。现在这四百多件珐琅彩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几年每到10月,院长都要在御花园绛雪轩举办招待会。有一次曾经约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芳斋演昆剧《游园惊梦》,招待故宫的理事和专门委员以及外宾。《游园惊梦》是由明至清久演不衰的传统戏,在传统形式的四方戏台上表演,真是天造地设地合适,整个协调的美达到不能再为之增减的程度。漱芳斋庭院里飘扬的曲声,真如戏文中“摇漾春如线”的美感,清歌妙舞和画栋雕梁汇为一体,相得益彰。来宾都赞美不止,认为是故宫博物院独一份的特殊展览。
《故宫周刊》平时每周出版一张,到了10月院庆必然出版一册特刊。记得1932年10月出版了一册《故宫周刊双十号·恽王合璧》画册。1933年出版了《故宫周刊双十号·宋四家真迹》法书。出版这本特刊时还有一节小故事:当时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到我们家,向我父亲说:“将要出版一本照例的双十号特刊,这次选的是《宋四家真迹》,你给题个签。”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又是故宫的同事,当然就答应了。这位徐老伯临走时还不太放心,又特为单独嘱咐我:“这本特刊已经印制,只等封面题签了,我不好意思跟你爸爸限日期,你给我做个内应,提醒他快点写,将来出版,除去给专门委员的一本之外,我再送你一本,好不好?”我说:“行啊!我还希望徐老伯再给我一本黄山谷的《松风阁诗》,一本赵子昂的《鹊华秋色》图卷,都要高丽笺印的。”徐老伯满口答应。当时这两件,都有两种版本,普通本是宣纸印的,另一种是用故宫原藏乾隆年间朝鲜进贡的高丽纸笺印的,墨光纸色古雅可爱,但印数不多,所以我才借机提这个要求。
次日很早我就把墨磨好,请父亲写。下午就送到古物馆的中所(现在科技部临摹室)交给徐老伯,他立刻命管理刊物的冯华先生取来我要的两种刊物。
1931年9月18日,万恶的日本人侵占了沈阳,之后不断扩大侵略面积,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平津地区一旦成为战场,故宫所藏国宝就会遭到破坏,遂命故宫理事会做好古物南运的准备。到了1933年春天,山海关告警,理事会正式决定古物南迁。
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不可能为十年纪念日举办什么庆祝活动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部在重庆南岸海棠溪,马衡院长就住在院部。古物分别保存在:贵州安顺一处,由庄尚严主管;四川峨眉一处,由那志良主管;四川乐山一处,由欧阳道达主管。
1944年,日本人孤军深入,侵略到独山,已经离贵阳不远。重庆院部派车将保存在安顺华岩洞的八十三箱珍品,接运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由安顺办事处主任庄尚严先生押运,并选择一部分运至重庆展览。马院长命我和王世襄兄参加这次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临时展览,以前我只是故宫的职工家属,到这时才实地参加工作,包括装车、押车、卸车、抬箱子和开箱整理,以及写说明、写卡片等,脑力体力一齐干。这部分展品就是曾在伦敦展览过的珍品,每件文物我都过一下手,真是莫大享受。
1945年,应该是二十年院庆的日子。这一年的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天,我正在牛德明兄(故宫古物馆的科员)家吃晚饭,牛太太烙饼的手艺特好,外焦里酥,吃起来口滑,不知不觉到吃完了才觉出撑得慌,喝过茶更胀得不得了。正在难受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由远而近人声鼎沸,鼓乐鞭炮齐鸣,德明的儿子牛晨从山下跑上来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还有点不相信,又听见隔壁收音机广播,这没错了!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和牛德明就下山,在上清寺街上走着,只见人山人海,都在喊口号,唱《大刀进行曲》。我们两人也蹦起来喊着:“胜利万岁!”刚才吃多了的感觉已经消失,心里反而发空,有些发抖,从来没经受过这样使人激动的事,高兴,又有点想哭,我不知所措了。街上的人群一直在狂欢。这一天的太阳也好像落山格外晚,大概天人同感吧。
当时,我在故宫是借调的性质,编制还在粮食部。胜利的这一年,各单位都在准备复员,虽然这一年的10月是故宫博物院的二十年院庆,但是分别在三个地方保管的文物都准备先集中到重庆,应做的事千头万绪,当然顾不上院庆了。到1946年1月,巴县石油沟飞仙岩保管的八十三箱文物,由庄尚严兄押运到重庆。事先马院长在海棠溪附近向家坡借到贸易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作为临时库房。贸易委员会已经迁回南京,留下很多宽敞的空屋。院部的计划是分为三组,甲组由庄尚严为主任,管理山脚一带的库房;乙组由欧阳道达为主任,管理山腰一带库房;丙组由那志良为主任,管理山顶附近一带库房。6月里我将要随粮食部先回南京,于是到向家坡与庄尚严兄话别,共同盘桓了几天,文物箱当然不能无故开箱,所以并未看什么。白天我们登山,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可以远眺川江。山上黄桷树和竹子很多,山境很幽,晚上喝点红糟大曲聊天。大家都快回家了,心情很愉快。老庄兄并不善作诗,他给我看日记本上前几年写的诗,非常朴素真实。我最喜爱的句子“苦忆黄沙大北风”。黄沙大北风本是北方气候的缺点,因为家乡沦陷,思乡心切,就觉刮大风的滋味很让人想,我也有同感。在日记本上还钤着一方印,印文是“老庄老运好”,语意双关,又含有他八年之中无休止的装箱、装车、运输、转移。他说:“胜利了,这一回东西装运回到北平,收进延禧宫和北五所库房,不用再装再运了吧。”我们满怀信心地都这样想。谁知后来事与愿违。胜利后,国家的统一反而成为久未解决的问题,是始料未及的。
我在向家坡时,正值那志良兄押着乐山文物的第一车也来到了。这次话别之后,那志良兄于1948年曾回北平一次,庄尚严兄却一直没能再尝到“黄沙大北风”的滋味。我回到北平后,从那志良兄的信中得知,我走后,9月份峨眉办事处的文物已全部集中到向家坡,到1947年的春天,乐山办事处的文物也完全到了向家坡。最后,除石鼓用十辆汽车走川湘公路运到南京以外,全部文物都装船顺流而下回到南京。
从1946年起,我在北平故宫古物馆上班,每日在库房编目和向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补充陈列室。第二年接收古物陈列所的清点工作,这一年(1947年)10月10日的新陈列,有在坤宁门东群房布置的郎世宁、艾启蒙的十幅画马,在钟粹宫书画陈列室布置的《兰亭八柱》、《法书大观》、韩滉《文苑图》、惠崇《溪山无尽意图》等。这些新补充陈列室的展品,除《文苑图》是南迁时正在照相室未赶上装箱,所以漏下了,惠崇《溪山无尽意图》是接收古物陈列所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原藏处新提集的,包括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所书的《兰亭八柱》,如果南迁以前发现这种稀世之珍也早就运走了。十幅画马是属于漏点的物品,装在很坚固的大漆匣里,原藏处因为漏雨挪动漆匣,才发现匣内装着画,所幸是漆匣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损伤。《法书大观》是在重华宫内一座木炕里面无意中发现的,也是属于点查报告时漏点的物品。
1949年以后,政府大力开展古建维修,多方征集文物,每年10月仍然必有新的展览,但并未提出院庆这个概念。一直到1985年才大举庆祝六十年,1990年又举办六十五年院庆。
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
《髹饰录解说》,精装一册,仿“黑光漆”的书衣,朱色题签,笔意厚拙凝重,朱桂辛(启钤)先生所书。这就是王世襄同志于1949年开始编写,1958年初稿完成,后又多次修改补充,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才得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专著。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工匠则限于文化水平,著书立说,确实有困难。如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
记得1949年秋,世襄刚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自此以后,古物馆的工作虽然很忙,他每天都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翻弄这本书,圈圈点点,抄抄写写。
《髹饰录》,明隆庆间名匠黄成撰,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分《乾》《坤》两集。《乾》集讲工具、原料及操作禁忌等;《坤》集讲髹饰品种、分类、技法及制作程序等。两集内容丰富,涉及漆工艺的各个方面,可能原意是为漆工而作,故认为不妨文字从简。另一方面又故作古奥,引经据典来象征比喻工具、原料。当时漆器名称和现在流行使用的名称又多有出入,所以尽管有天启时的杨明为它作注,还是很难读懂。
面对这样一本难读的古籍,世襄是如何攻读呢?由于我们都对工艺感兴趣,又不时探讨切磋,所以我是知之颇深的。世襄是先把《髹饰录》中的名词、术语摘录出来,编成索引,这样就能知道每一词语在书中出现若干次,通过综合比较来探索其意义。我国著述末附索引的为数不多,而世襄研读此书却是从编索引入手的。
他曾说过,《解说》的内容来自三个方面。(一)实物的观察研究;(二)向漆工艺人请教访问;(三)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为了观察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为了向老艺人求教,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至于文献资料,则查阅了大量古今图籍,包括国外文献。从《解说》的编写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态度和研究方法。他的态度是严谨的、不惜力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1953年世襄离开了故宫,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解说》并未因此而中辍。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这倒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加速了《解说》的编写。一年后初稿完成。朱桂老兴奋地为他撰序,并题签。世襄冒着风险,节衣缩食,把《解说》送到一家誊印社,自费刻印了二百册,署名“王畅安”。这就是1958年非正式出版的油印本。
二百册书被他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漆器厂及他认为需用此书的人,当然也有我一本。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多宝臣先生在故宫修复厂上班,见面时他也常谈到世襄又提出什么问题,并且世襄的草稿有时也给我看,所以这部书大概内容我是有印象的。这次看到写刻清楚的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更使我惊喜心折。他用了约二十倍于原著的篇幅,逐条、逐句、逐词对这部古籍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注释,把古代漆器名称、品种、出土及传世的实物,乃至现在流行的名称、品种联系起来。把古代的工具、原料、技法和当代老艺人使用的工具、原料、技法联系起来。广征博引,一以贯之,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许多制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答了许多专业性问题。实际上它已远远超出一般对古书整理诠释的程度,而卓然自成一部专门著述。《解说》油印本问世后,得到漆器生产者的赞赏。我更觉得《解说》是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进行漆器编目、陈列工作时的唯一重要参考书。1959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为了和英国大维德(SirPercivalDavid)交换资料,向世襄索取一本寄往伦敦,立即得到国外学人的重视。大维德英译《格古要论》,迦纳(SirHar⁃ryGarner)撰写《琉球漆器》《中国漆器》及有关髹漆的文章,广泛引用了《解说》中的材料。
1961年,全国大专院校重编教材,美术院校的教材由文化部在香山静宜园召集一个编写的组织,我是参加编写的成员之一。为纂写《中国髹漆工艺美术史》成立了以沈福文教授为主编的小组,按理说邀世襄参加工作是十分合适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能让他来。不过《解说》却成了教材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尤其是明、清实例的描绘,往往整段地录引。教材《后记》没有提到世襄的名字,只笼统地说一句:“参考了不少近人有关漆器方面的论著,从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后我见到世襄,告诉他上述情况。他怡然表示:“很好!只要我写的东西多少能为人们提供些材料,就是好事!”
1962年世襄摘掉了“右派”帽子,《解说》经过陈叔通、齐燕铭两位同志推荐,送到了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这时世襄感到有必要向文物局领导汇报一下。局领导认为据该书的性质还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较为合适。于是又从中华书局取回送到了文物出版社。一经辗转,已经到了1969年,从完成初稿到此时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世襄认为有必要把重要的漆器新材料补充到《解说》中,然后再正式出版。他在“四清”的间歇中对《解说》做了一次修改和增订。待修订完毕,“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稿子送到文物出版社,只能束之高阁了。
1969年,世襄是带着肺结核病来到干校的,连部分配他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我们在“四五二”高地的七、九两连毗邻,可以朝夕相见。疾病缠扰,岁月蹉跎,并不能消沉他的意志。有一天我经过菜地,看见有倒在畦边而色灿如金的一株菜花,我说:“油菜能对付活着的劲头真大!已经倒了,还能扭着脖子开花!”他说:“我还给它做了一首小诗呢。”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我说:“不要给别人看了,你现在还没解放呢!这也能招祸!”他笑了一笑。
后来我被调到丹江干校,1972年他从咸宁来信说:已经解放了,肺病也已痊愈,调到伙房工作,干校人少物资多了,湖里鸭子、圈里肥猪、窑咀的活鳜鱼,成为家常菜,营养丰富,所以身体也强壮了。又写了很多首田园杂诗,还问我有无调回工作的消息。我的回答诗里有“今年依旧系匏瓜”的句子,就是指当时的实况。
“四人帮”覆灭后,世襄的错划问题得到了改正。三中全会后,他更加起劲地工作,公余之暇,又把《解说》做了第二次修改补充。由于考古的新发现,使《解说》征引的实例由原来的一百多件增加到二百多件,还补充了不少从清代匠作则例中找到的材料,对近年国外的论著,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索引的编排,为了方便青年读者,把笔画检字改为汉语拼音。
书正式出版后,世襄又亲自送来一本,当我看到这本书时,不禁又想起当年咸宁他做的诗。我对他说:“真不易呀,现在总算一切都好了,风调雨顺,土厚肥丰,祝愿你结出更丰硕的菜籽来!”
(本文摘自《北京闻见录》,朱家溍著、杨良志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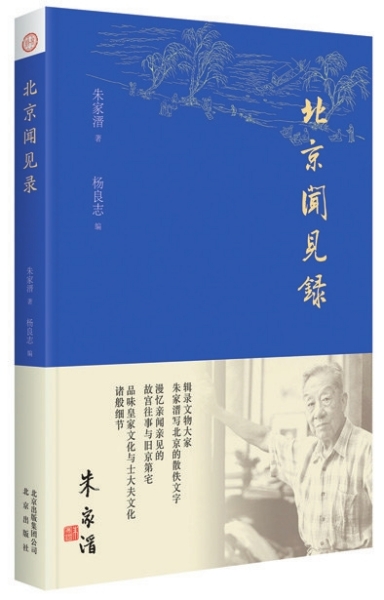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