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意大利疫情严重以来,“震中”伦巴第就成了媒体上的高频词,很多人都是通过疫情的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把米兰作为首府的那个地方。这个意大利北部与瑞士毗邻的大区处于南欧最大的一片平原上,它对于意大利就像长三角对于中国一样重要。最风光的地方往往也会遭受最大的苦难,历史上像这样大规模的瘟疫,在以米兰为核心的伦巴第已经发生过400到500场了:1447年,一场不明原因的“热病”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不到40年后(1484—1485年),一场鼠疫造成总共五万人死亡,目睹了这一惨状的达·芬奇决定设计出一个卫生安全的市政系统。然而,历史上伦巴第经历的最黑暗时刻是在1630年前后,那场被称为“米兰大瘟疫”的鼠疫从这里爆发,最终导致整个意大利28万人死亡。
但是,尽管已有这些先例,当瘟疫再一次让这里成为意大利前沿阵地的时候,大多数伦巴第人依然感到陌生和困惑,甚至一时回不过神来,并没有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直到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实,从疫情在意大利开始的那一天,一直有人在提醒人们以史为鉴,莫掉以轻心。2月26日,在米兰及其周边的学校开始停课的时候,一位名叫斯奎拉切的高中校长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他给全校学生留的家庭作业是阅读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中关于1630年瘟疫的章节,并体会和总结其中“非凡的现实意义”。
这位校长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他的这声哨音让很多人若有所悟。《约婚夫妇》这部小说在意大利文学中的地位不亚于中国文学中的《红楼梦》,但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它又像一场避之不及的噩梦:枯燥、冗长,既没意思,又不好读,若不为考试,永远也不会碰它。但斯奎拉切校长在这个时候号召学生们翻开这本小说,而且此举还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共鸣,想必有其深意。
1630年的那场瘟疫发生在《约婚夫妇》诞生的约200年以前,而如今的意大利疫情是在小说问世约200年以后,这两场时隔近400年的疫情都是以伦巴第—米兰为中心,然后逐渐蔓延开来的。时间的对称,空间的重合,危害性的相似使我们不由得不将这两场疫情相互参照和比较。当然,小说中战争和饥荒的背景,以及低下的社会公共卫生条件都已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结构也完全不同,然而当我们重读小说,尤其是重点描述瘟疫流行状况的章节时,却犹如经历一次次潜意识的古今穿越。
作为小说家的曼佐尼有着浓重的史家情结,为了提醒读者他的小说并非凭空杜撰,他甚至在小说的前言中坚称,他讲的故事来自于一份17世纪的历史档案,是他从故纸堆里找到的,怕读者不信,他还特意在书名下面加上个副标题:《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发现并整理的17世纪米兰历史》。如今看来,这并不只是老套的叙事手法,更是小说家与史家这两种身份在作者身上不断纠缠、融合的产物,而促使两种身份融合的催化剂则是他浪漫主义的民族复兴理想。在他看来,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要比一部普通的编年史更丰富多彩,更易于流传,更深入人心,这一点他完全继承了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一脉相传的衣钵。
其实,曼佐尼写《约婚夫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含沙射影地批判他那个时代奥地利统治者对意大利的奴役。曼佐尼将小说的高潮部分设置在瘟疫的背景之中,恰恰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人类共同命运的自然灾难面前,人性和社会心理才会显露得淋漓尽致,而错综复杂的小说情节才能有峰回路转的可能。然而,让曼佐尼没有想到的是,他关于1630年伦巴第瘟疫的描述似乎在两场时隔近400年的疫情之间打开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界面,通过对个体与集体行为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对称性与相似性——小说的现实意义在近200年后仍然存在,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
曼佐尼在小说中将这场鼠疫的蔓延更多地归咎于“人祸”,而非天灾。在他看来,1630年鼠疫在意大利北部爆发绝非偶然。161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波及了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雇佣兵穿过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乡村,他们蓬头垢面,满身污垢,不但随地大小便,还到处寻衅杀人,致使尸横遍野,无人掩埋:这些都是让鼠疫迅速蔓延的理想条件。但假如人们注意卫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话,鼠疫也不会传播得这么快。但在那个时代,现代的卫生观念还没有形成,人们也不知道细菌和病毒为何物,然而这并不是导致鼠疫传播乃至失控的直接原因,曼佐尼写小说当然也不是为了传播医学知识和宣扬讲卫生习惯。
埃科曾经说过,曼佐尼想通过小说告诫我们的是,人们愚蠢的行为才是最大的祸端,蠢人做的坏事比坏人做的坏事还要多,还要可怕。在鼠疫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尽管普通百姓人心惶惶,但官方却一直否认爆发鼠疫的说法。当伦巴第出现了第一批死人的时候,官方却说那是由沼气引发的热病所致:
原来那些否认这是传染病的医生,如今仍然不愿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的东西,可是又不得不给如今这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属名,于是只好将其称作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一种可怜的权宜之计,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带来了极大的害处,因为,尽管这一做法表面看来是承认了事实,但它仍然没有使人明白,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而承认和看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吕同六译,后同)
当爆发鼠疫的证据更加充分的时候,米兰的统治者心里想的只是关系到他们统治利益和个人前途的战争与政治,根本不关注这些小小的热病,有关部门也无意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而是互相推诿扯皮,致使关于防治疫情的公告足足拖了一个月才正式发布。而此时,瘟疫已经从伦巴第的农村蔓延到了米兰城。然而当有人首次发现了出现在腋下的蓝紫色鼠疫赘瘤时,惶恐的官员们居然号召市民举行一次大游行,“团结一心”共同祈求上帝的助佑。这个愚蠢的行为让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一起,摩肩接踵,正好为鼠疫提供了绝佳的传播途径。从今天来看,这种帮倒忙的行为一直未被杜绝。
终于,鼠疫的存在昭然若揭,倒毙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整个伦巴第地区就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当人们再也无法回避这个可怕的现实时,却突然有人开始提出了一个既不合时宜又极其愚蠢的问题——这到底是谁的错?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我们大家的错,应归咎于那些没有认识到事态严重性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及时采取预防、隔离、诊治、消毒措施的人。但是对于愚蠢的人而言,推卸责任要比承认错误容易得多。于是,关于鼠疫传播者的猜测和谣言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了。官方派遣调查疫情的两位“专家”,在既没弄清导致大量死亡的原因,也没确定具体死亡人数之前,把精力都花在了追查米兰的“零号病人”上,难怪曼佐尼在小说里调侃他们说,似乎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追查,就能使他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位专家终于找到了米兰地区疫情的罪魁祸首——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意大利士兵,然而对于这个士兵的姓名和进入米兰的具体日期,两位专家却各执己见。可不久之后,他们的结论就又被推翻了,因为人们总能发现在那两个士兵之前进入米兰的疑似病例。正像前不久很多人怀疑的那样,相对无数正在患病和已经死去的人,找出这个“零”就这么重要吗?但小说里这两位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查明这位士兵在西班牙服役之后,因为这可以为米兰统治者成功“甩锅”找到充分的证据,甚至可以干脆将这种恶性传染病命名为“西班牙黑死病”。看来这种“甩锅”行为古往今来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恐怕就是从15世纪末开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梅毒的称呼:欧陆很多国家称之为“法国病”,而愤怒的法国人则将其命名为“那不勒斯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称之为“基督徒病”,印度人则说它是“葡萄牙病”。总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个不光彩的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看似可笑的行为至今仍在被复制粘贴,就好像给病改成别人的名字自己就可以终生免疫一样,可能在这些人的逻辑中,细菌和病毒是拥有国籍和会识别国界的。
在米兰,患鼠疫而死的人数不断上升,而可以收留鼠疫患者的医院和专门的隔离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然而还有比这些更让人一筹莫展的问题:
比如确保服务、维护纪律、按规定进行隔离等,简而言之,就是要维护或者建立卫生委员会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一开始,正是由于许多病人肆意妄为,加上部分官员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以一切才陷入了一片混乱。
大乱之中,一位天主教嘉布遣会的修士临危受命,被官方赋予“最高而且无限的”权力,代领同会的兄弟去管理这个“悲伤的王国”。他内心仁慈,具有牺牲精神,但手段却“专横严酷”,对待病人恩威并施,甚至会手执长矛巡视病房。但在小说里,曼佐尼明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社会混乱、管理无序的特殊时期,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严苛的治理是很有必要的。在如今的意大利疫情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并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人们由于价值取向、政治派别、生活条件等情况的不同,对待“封国”“封城”等政府强制性措施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尤其是在疫情刚刚出现的阶段,意大利的情况与小说中描述的17世纪米兰的情况如出一辙,市民和政府机构对事态的严重性普遍估计不足,他们怀疑、嘲笑,甚至鄙视那些为此担忧的人们,集体的轻视、懈怠和拒绝助长了疫情的蔓延。
与古人一样,当下意大利人对于积极严厉防疫措施的质疑和反对并不只是出于单纯的医学观点,而是掺杂了太多的“主义”和意识形态,比如颇具世界影响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就一直在唱反调,他认为意大利人不能为此牺牲正常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工作、友谊、情感、政治和宗教信仰,不能像《约婚夫妇》中描述的那样只把人视为潜在的传染媒介而加以隔离,没有自由生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意大利当局采取的紧急措施是“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这很代表了一部分意大利人的意见。然而当疫情骤然严峻,死亡阴云已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和心头时,阿甘本的观点遭到了众多质疑,比如他的诤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一开始就对他这种言论给予了干脆的回应:“别听他的!”
米兰的一群修士作为400年前的“逆行者”,在没有得到政府足够援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传染病医院中收留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这些明智而崇高的人在百姓心中激起了感恩之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面这场瘟疫。然而,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死亡人数的增加,又有一部分人的心里出现了新的阴影,他们不再否认瘟疫扩散的事实,而是转而怀疑它并非通过自然途径传播,因为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承认自然传播,就等于承认自己此前的误判与过失。他们根据以往的一些文件,断定这次瘟疫是别有用心的坏人实施的阴谋诡计,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入米兰,伺机在人家墙上或门上喷洒有毒物质,或使用其他巫蛊之术,传播鼠疫。愿意相信阴谋论的人们像集体着了魔一样,只要看见异国打扮的人,都会当他是传播鼠疫的坏人——这是因为人们更容易憎恨外国人,而不是自己的近邻。有一个老头遭人围攻,仅仅是因为掸去了一条长凳上的灰尘。如果有人在路上向别人打听事的时候摘下了帽子,对方马上就会大叫道:“把有毒的灰尘留在帽子里撒给死人吧!”一个家伙敲了敲大教堂的墙面,想看看石材的坚硬程度,众人便愤怒地扑向了他。曼佐尼这位总是略带忧郁的作家以冷幽默的方式描述了这些现象,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会“对号入座”。用前面提到的那位斯奎拉切校长的话说:“曼佐尼告诉我们,这类事导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毒害,以及世俗生活的野蛮化。当我们感到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威胁时,本能会让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而危险在于我们会将每一个同类都视为威胁,视为一个潜在的攻击者。”对此,曼佐尼给出的忠告是: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解与此类似的历史事件而为这段历史发表更多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小事件还是大事件,在多数情况下,通过采取早已被证实的方法,例如在发表意见之前,先仔细观察、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然后经过一番考虑后加以比较,这样可以避免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除了人性以外,曼佐尼在小说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也与今天疫情中的意大利息息相关,这就是疫情与经济的关系。那时候,对于鼠疫肆虐的米兰而言,主要问题是食物和医疗经费的短缺,以及政府如何维持大批突然失业市民的生计。因此,政府在面对巨大预算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了两种基本应对方式。一是暂缓政府的税收,为百姓缓解压力;二是通过借贷的方式募集资金,作为购买粮食和救济穷人的经费。小说中的应对措施与当今意大利政府的做法别无二致:一方面,他们制定了75亿欧元的纾困支出计划和250亿欧元的“罗马计划”,为暂时减免税收、债务,宽限房贷等项目提供资助;另一方面,意大利与欧盟和欧洲央行达成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债务协议,突破财政负债上限,将2020年赤字支出提高至200亿欧元,以弥补巨额医疗费用,挽救GDP。意大利本来衰退的经济,恐怕这次是要雪上加霜了,正如曼佐尼在小说中说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现在的某些需求。然而,严重的苦难尚未来临。”
曼佐尼,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作家,善于把瘟疫带来的苦难描绘成一面明鉴社会与人性善恶美丑的镜子:那些负责把尸体搬运到公共墓地的脚夫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们认为喝酒能抵御病菌的侵袭,这场鼠疫已经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据说他们会故意把患者的衣服丢在街上,加速疾病的蔓延;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为逝去的九岁女儿穿上洁白美丽的衣裙,像孩子睡着了一样地抱着她、亲吻她、与她告别,这种圣洁的母爱连猥琐的脚夫们都为之折服,答应不拿走孩子身上的任何东西,其实这位母亲和家里一个更小的孩子也将不久于人世。这些都是小说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场景,已进入了意大利人的共同记忆之中。虽然曼佐尼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作家,也从未回避过任何关于丑陋、悲惨、痛苦或死亡之类的话题,但他用恶衬出的善、用丑映出的美,20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曼佐尼笔下的这场瘟疫还是一把能荡涤一切污秽、还原一切清白的扫帚:它让恶人一命呜呼,让善良的人不再被搅扰,让躁动的人复归平静,让有情人劫后重逢、终成眷属。然而,人们为了这一切的皆大欢喜又付出了惨重代价——1630年的这场鼠疫使米兰三分之一的人丢掉性命。
在今年4月25日意大利独立日前后,亚平宁半岛的疫情终于出现了向好的拐点。两个月前,为了让学生们振作起来,在精神上不被病毒击垮,早日重返校园,斯奎拉切校长还恳请所有学生要笃信科学:
与14和17世纪的疫情相比,我们拥有现代化医学,请你们一定坚信科学的进步与可靠,因为她是理性思维的女儿,就让我们运用理性思维来保护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社会的结构和我们的人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真的会被瘟疫击败了。期待早日与你们在学校重逢。(意大利《信使报》2月26日)
当下疫情中的意大利人,特别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少年学生,正在教育者的引导下,在文学和历史的字里行间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答案,从而校正自己被社会和环境扭曲的生活。“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曼佐尼在《约婚夫妇》中讲的故事仿佛是对今天的预言:政客之间的推诿与争辩,对“零号病人”的追查,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恐惧,对生命的无视与尊重,荒唐的言论与行为,医院人满为患,政府财政危机,市民抢购生活物资……,400年前的那场瘟疫恍如昨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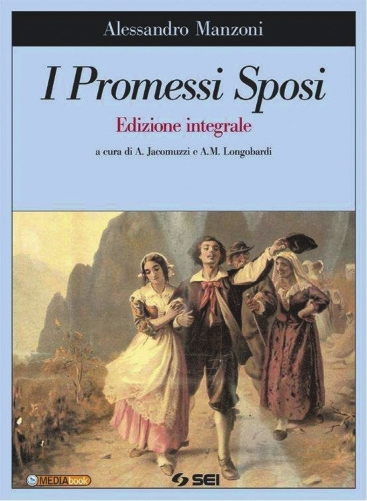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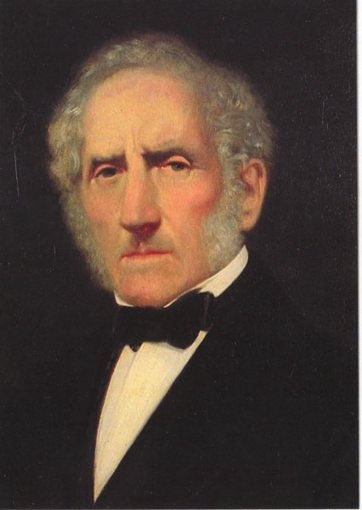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